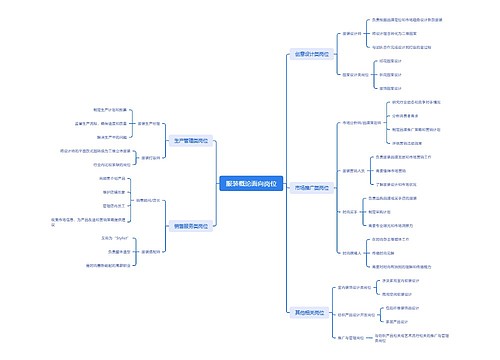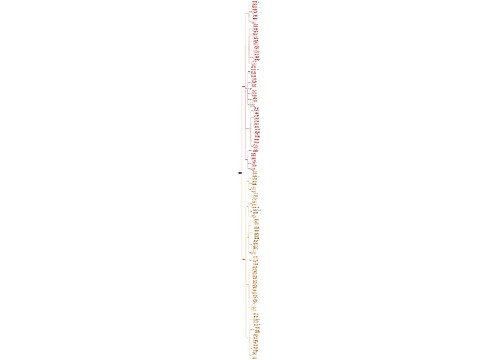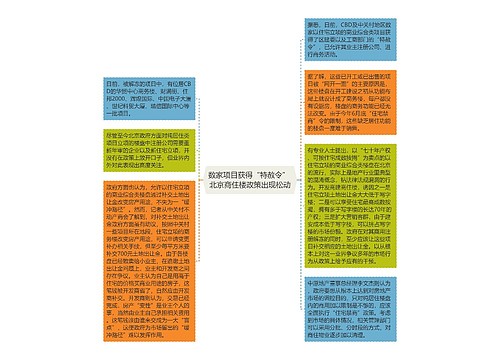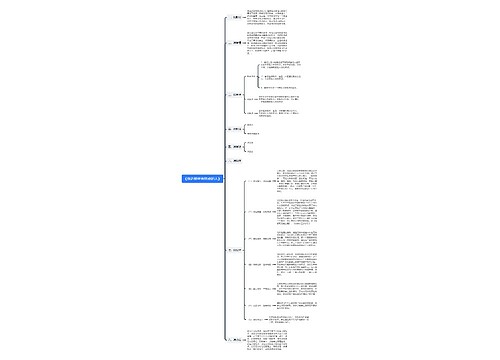分析人士指出,这是2004年“国发28号文”后,中国政府为实施新的宏观调控而出台的“最严厉的土地政策文件”;其对宏观经济和地方政府的影响非同小可,甚至可能超过“国发28号文”,成为新一轮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纲领性文件。
但是,由于该文件并未触及中国土地制度的根本缺陷,也没有撼动扭曲的政绩评价机制,“新土地调控”之成败得失。似仍在未定之天。
据记者了解,这一“31号文”系由国土资源部起草,其草稿在8月12日至14日于昆明召开的全国土地调控工作座谈会讨论后,便基本成型。后经修改于8月31日定稿——从正式定稿到全文公开只有五天时间,堪称“创纪录”,亦可见决策者借“收紧地根”调控宏观经济的决心。
中国政府“土地调控”始于2004年,但成绩并不理想。据国土资源部数据,2005年对16个城市的卫星遥感监测显示,违法用地宗数占新增建设用地宗数近60%;若论面积,则占近50%,个别地方甚至高达90%.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土地违法案件高达25153起,涉及土地面积18.36万亩,同比上升近20%.这些态势表明,“土地闸门”并未能守住。
故此,“31号文”开宗明义——当前“土地调控中出现了一些新动向、新问题,建设用地总量增长过快,低成本工业用地过度扩张,违法违规用地、滥占耕地现象屡禁不止,严把土地‘闸门'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基于上述教训,此次“31号文”可谓“重典治乱”之重演,从调整利益机制、强化行政问责、完善法律法规诸方面全面出击。
“由于目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地方以租代征等违法占地严重,中央决定,着眼于‘迅即有效',强化土地宏观调控职能,给宏观经济点刹车。”国土资源部政策法规司司长甘藏春说。
据《财经》记者了解,“31号文”的四个配套文件正在制订之中,并有望在2007年1月1日前颁布施行。其中,包括提高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增至原标准的两倍;提高城市土地使用税,增至原来的3倍;财政部会同国土资源部制定《土地出让金收支管理办法》,修订《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监察部、国土资源部制定《土地违法责任追究办法》等。
根据“31号文”的规定,“工业用地必须采用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其出让价格不得低于公布的最低价标准”。这是最引人注目的政策变化之一。
目前,中国商业用地实行“招拍挂”出让,而工业用地大多仍是“协议出让”。由于协议出让“操作空间”甚大,基层政府竞相压价“招商引资”,甚至零地价招商。今后工业用地实行“招拍挂”后,协议出让将逐渐淡出,土地出让的市场化程度将有所提高。
目前我国建设用地出让的总量中,工业用地的比例占30%左右,商业用地的比例大约占20%以上。可以料定,随着工业用地“招拍挂”,其地价将有大幅度提高。据国土资源部政策法规司司长甘藏春预测,新政策全面实施后,工业地价可能在现有基础上提高三分之一甚至50%.
毫无疑问,工业用地“招拍挂”,会提高工业用地出让的透明性和公开性,有效抑制地方政府对于经济的低水平扩张。但专家担心另一个可能的结果,即工业用地其实大多从耕地征用而来,如果工业用地今后全部实行“招拍挂”,地方政府把工业用地垄断在手,实际上就排除了农用地所有者——农民参与土地出让谈判的权力。由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可能更加得不到保障。
有专家指出,工业用地确实应该市场化出让,但是不能由地方政府或国土部门垄断后搞“招拍挂”。否则不仅会增加企业用地成本,更会进一步强化土地管理部门的行政权力,像城市房地产市场一样滋生腐败。
国土资源部是这项政策的制定者。据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司官员介绍,目前商业用地“招拍挂”已有成熟经验,推广到工业用地上“应该没有问题”。这次“31号文”规定,工业用地出让不得低于国家统一公布的“最低价标准”,并规定“最低价标准”不得低于“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前期开发成本和按规定收取的相关费用之和”。
但是,真正的难题在于如何核定“工业用地最低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刘守英对记者分析:“工业用地最低价三要素中,最难以计算的是前期开发成本。比如,‘前期开发'究竟是指’三通一平'还是‘七通一平'?是政府性公司去做,还是委托市场去做?不同的做法则成本大不相同。最低价难以准确核定,’招拍挂'又如何操作?”
事实上,有些工业用地也很难实行“招拍挂”。据国土资源部一位官员说,对于国务院确定的一些大型工业项目,像天津引资的“空中客车”项目用地,就无法实行“招拍挂”。
据记者了解,“31号文”最初只是规定“原则上”实行“招拍挂”,但在出台前夕被“必须”二字代替——而究竟如何实行,并没有具体的操作措施。
其实,广东、江苏等省近年来的实践证明,农民集体与工业企业“平等谈判”,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以出租、出让或转让等方式直接供应给企业,既降低了企业的用地成本,也保证了农民长期分享土地增值收益,政府又可获得税收及土地费,可谓“一举数得”。
“既然政府垄断工业用地出让问题多多,倒不如让农民集体建设用地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直接进入市场。”刘守英对《财经》记者说。
“31号文”的另一个核心内容是,为了“权责一致”,调整城市建设用地审批方式,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内,“由国务院分批次审批的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调整为每年由省级人民政府汇总后一次申报”。
据专家介绍,这实际上是把“城市建设用地的农用地转用审批权”由国务院下放到省级政府,同时,强化了省级政府对全省农用地转用和耕地保护的监管责任。土地专家指出,此项改革减少了建设用地指标控制的僵化性,地方政府用地的灵活性更大,具有积极意义。
中国的农用地转用审批目前分为两种,一种是“批次项目”用地的审批,一种是“单选址项目”用地的审批。批次建设项目占用的农地,一般在城市规划范围内,由各县市政府上报,由省级政府和国务院审批;而单选址项目用地,大多涉及占用基本农田,需要修改土地利用规划,必须上报国务院审批。
此次改革后,随着批次建设用地的审批权下放到省级政府,这一矛盾有望得到解决。今后,省内城市建设规划内用地,涉及农用地转用的,无论面积大小,市县政府只需上报到省政府审批,不必由省级政府逐批次呈送国务院;国土资源部今后则侧重于监控各省年度建设用地的规模和总量。
调整审批方式后,省级政府的用地审批权有所扩大,但他们的责任也相应增大。2004年的“28号文”要求“省级政府对耕地保护负总责”,“31号文”更进一步要求建立耕地保护和土地利用的“省长负责制”。
根据“31号文”,今后,各省省长“应对本行政区域内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执行情况负总责”,“实际用地超过计划的,扣减下一年度相应的计划指标”。
由于强化了耕地保护的省长负责制,考核的内容也以实际发生的新增建设用地为准,更是给省级政府套上了“紧箍咒”:一旦本省实际用地规模超过年度用地计划,省级政府及其领导人就要被“问责”。在现行政绩评价机制下,此招可谓“落到实处”。
不过,一些土地专家对记者指出,强化行政问责制固然重要,但并不能从根本上阻断地方政府的“卖地机制”;换言之,“省长负责制”能在多大程度上奏效,尚有疑问。
对于近来坊间热议的土地出让金的管理和使用,“31号文”中明确规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总价款全额纳入地方预算,缴入地方国库,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土地出让金,所称“地价”,亦即“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总价款”。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土地出让金一直作为地方政府的一项收入,没有纳入政府预算管理,其管理和使用异常混乱。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调查,土地出让金收入约占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的60%以上,属于地方投资扩张的主要驱动力。
此次“31号文”要求把土地出让金全额纳入地方预算,这无疑有利于强化监管;但由于土地出让金收支长期“体外循环”,目前要一举纳入地方预算,不能不说面临操作的困难。
据国土资源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王守智透露,《土地出让金收支管理办法》具体由财政部综合司主导起草,目前已经有了一个初稿,但他不愿透露具体的内容。同时,主责此事的财政部相关官员也讳莫如深,由此可见其“敏感”程度。
据记者了解,财政部今年年初曾计划在国库中设立“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专账”,按照国有土地出让金收入的一定比例,建立“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并规定不得作为政府当期收入安排使用,意在留给后任政府一些发展建设资金。国土资源部则倾向于建立“国有土地出让收益专项管理制度”,把土地出让金的收支纳入政府特别预算管理,在中央、省、市县分别建立“国有土地出让收益基金”。
据记者了解,国土资源部方案欲从土地出让金纯收益中划出一定比例,集中到中央和省级政府。对此财政部并不认同,理由是,1994年分税制体制就已经明确土地出让金归地方政府,目前再向上级集中资金,并不符合法律程序。
这也正是公共财政专家普遍关注的问题。有学者向记者表示了担心:此番土地出让金全额纳入地方预算后,总的盘子较过去清楚了,会不会更有利于中央和省级政府从中提取一部分?如果中央和省级政府要从中切出一块“蛋糕”,应经过哪些法律程序?一旦中央和省有权支配土地出让金,势必对地方政府造成巨大的影响。
诸多学者向记者指出,以土地参与宏观调控,显然是中国特殊国情下的权宜之计。土地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如果价格不能主要由市场形成,如果不能实现“同地同权同价”,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便难言成功。
而要实现土地“同权同价”,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无论如何不可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