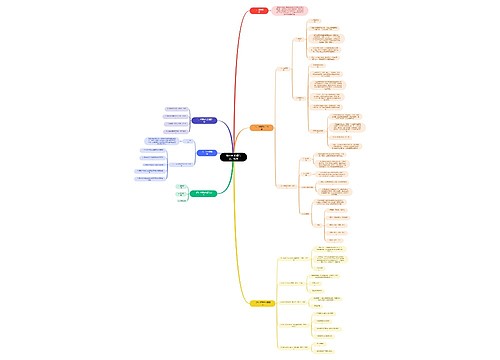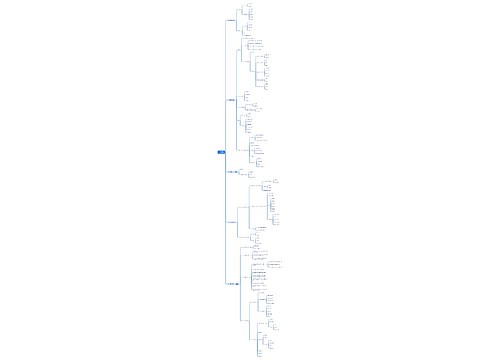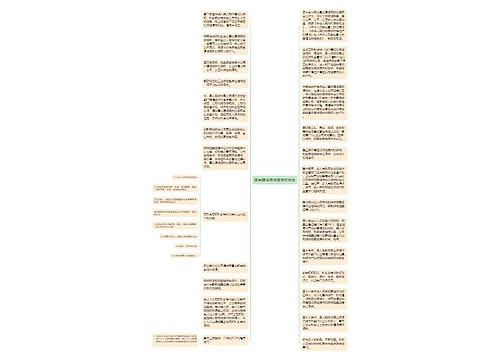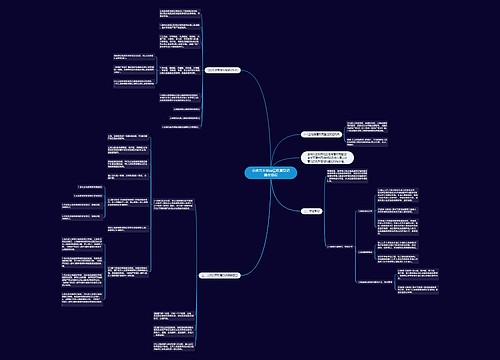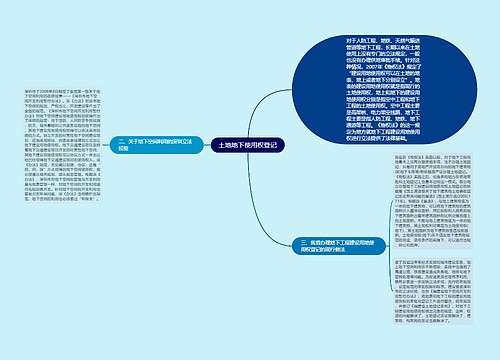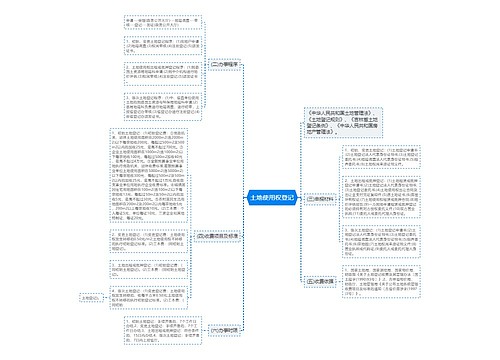发展权,这英美法系的一个名字,其内容主要是指农用地改变用途变为建设用地的权利,由于这一权利的行使不仅决定着土地价值的巨大变化,也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土地利用的模式。在西方一些土地私有制国家中,土地所有权的内容是相当完整的,国家为了从整个社会利益出发来规范土地的合理利用,通过向农地所有权人购买等方式将发展权集中国家手里。而在我国,集体土地所有制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从土地私人所有向国家所有过渡的一种特殊形态,其权利一开始就是不完整的,1998年修订实施的《土地管理法》规定了土地的用途管制制度,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等,这都表明我国集体土地所有者对集体土地没有完全的处置权。西方所讲的“发展权”在我国早已掌握在国家手里,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从其产生时起就没有包括这一权利。
按照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惯例,土地发展权归社会公共所有,理由是土地增值主要来源于地区经济增长,而地区经济增长则得益于地区公众劳动、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政府公共补贴及各种优惠政策扶持等。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我国土地的发展权尚未真正得到体现,土地增值被掩盖在房地产增值中,其结果是本应由社会公有的增值收益流入了房地产开发商的口袋,加剧了社会收入的不合理分配。因此,当前我们急需要解决的不是设立“发展权”问题,而是如何保障土地增值的公共性质和政府对国有土地的合法收益。
土地立法中的法律移植(对称法律继受),简单地说就是对国外优秀土地立法吸收同化,从对我国土地立法的完善上来说,应该是必要的。但是在法律移植过程中,以下因素是必须要考虑的:一是我国土地资源自然条件的特点;二是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三是我国法律文化背景、社会制度及风俗习惯、道德观念与西方差异;四是与之相配合的相关制度建设。因而在借鉴国外经验时,就不应单纯地就某土地权利论权利,而应充分把握这种土地权利形成与存在的社会、历史、经济、政治等背景原因,并将其与我国现阶段的状况及社会条件对比分析,从而避免借鉴中的盲目性。自80年代以来,全国人大通过了大量的法律,但是由于许多法律的条文名称、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参照西方国家的现有法律制定的,这些法律产生于西方社会发展的历史之中,带有其传统政治观念的内涵,而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中人们之间的法律关系具有很不相同的传统。因此,在许多领域中虽然有了相当完善的法律规范,但并未出现我们预期中的法治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