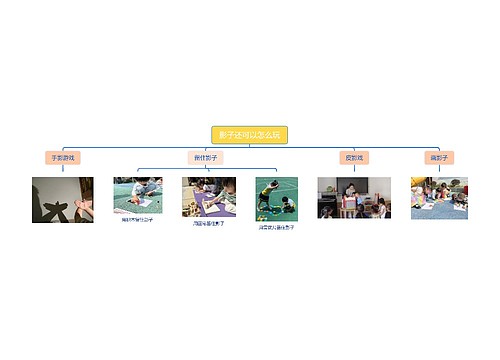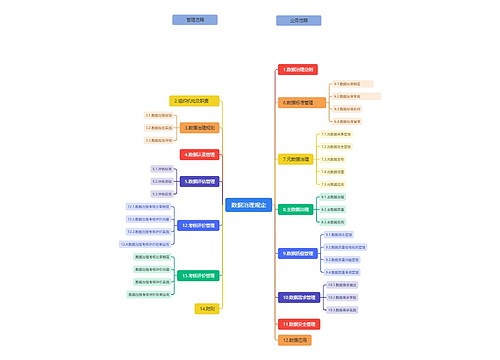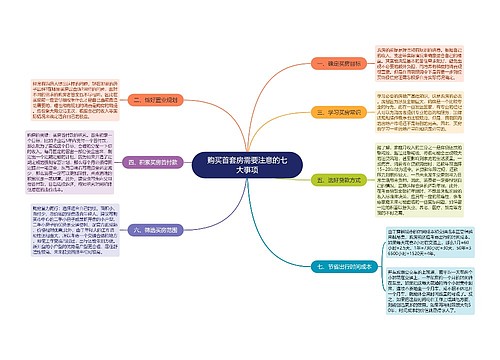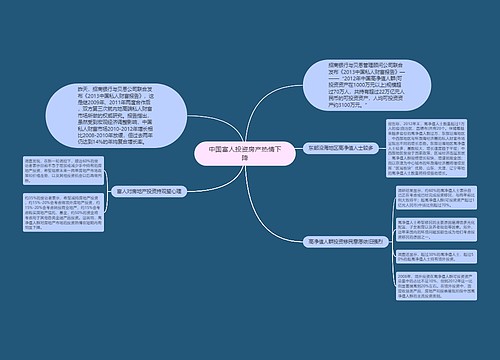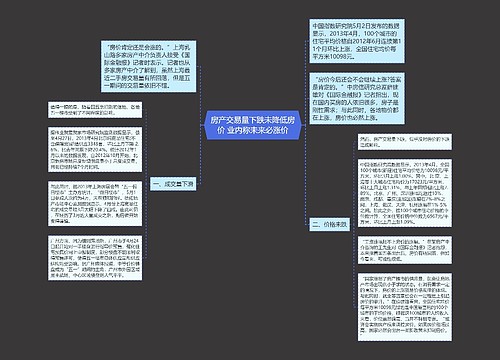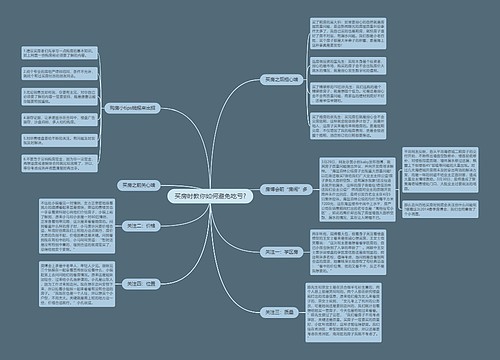它因澳大利亚托伦斯于1858年提出议案并获通过而得名。后为英国、爱尔兰、加拿大、菲律宾、美国等大多数英语国家和地区采用。我国香港也采这一制度。其基本特点有:
(1)采任意登记制,不强制一切土地必须申请所有权及他项权利登记,但一经登记,其后发生的不动产物权变更或设定,非经登记不生效力。
(2)交付产权证书。即在不动产初次登记时,登记机关依一定的程序确定不动产的权利状态,记入登记簿,并发给土地所有权人产权证书(地券)。让与不动产时,当事人之间作成让与证书,连同地券一起交给登记机关,经审查后,在登记簿上记载权利的转移,让与证书存于登记局,对于受让人交付新的权利证书(地券),或在原地券上记载权利的转移,从而使第三人能从该地券中明确不动产的权利状态。
(4)设置保险基金,因登记具有不可推翻的效力,故登记若有错误、虚伪或遗漏而致真正权利人受损害时,从保险基金中支付赔偿费用。
上述三种不动产登记制度孰优孰劣,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因为物权法是具有强烈民族性的法律,它的制度设计与该国或地区的具体情况息息相关。就法律传统而言,同属于大陆法系的登记要件主义和登记对抗主义更易为我国立法所接受。
通过上文论述可以看出,德国法与法国法在不动产登记制度上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我们应如何取舍呢?登记要件主义认为,物权的本质是对世权,具有排他性,所以物权变动必须具有公示方法,同时该公示还应具有公信力,以保障信赖公示的善意第三人的权益。
在登记对抗主义下,登记仅具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实际上,这种立法是自相矛盾的,根据债权合意即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但是该“生效”物权若未登记却又不能对抗第三人,既然不动产物权不以登记为生效要件,第三人又何以能以“欠缺公示”为由主张物权变动无效呢?实践证明,法国法和日本法所确立的不动产登记立法例,不仅在理论、逻辑上讲不通,而且对交易安全有极大的妨碍。
因此,我国立法不应采纳之。相反,登记生效主义由于统一了公示时间和物权变动时间,使二者同步进行,在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上保持一致,更有利交易安全,应属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