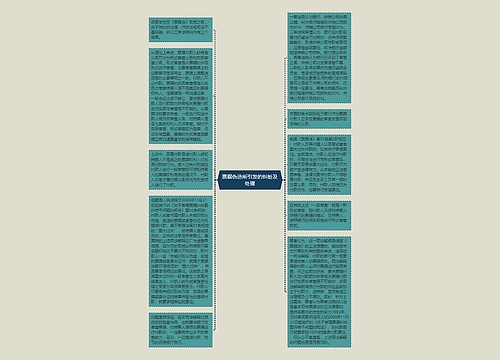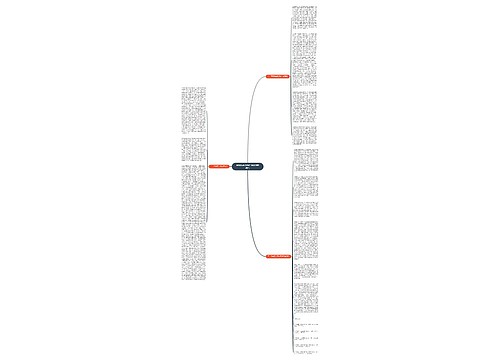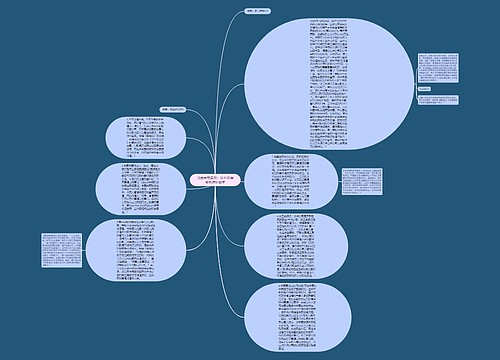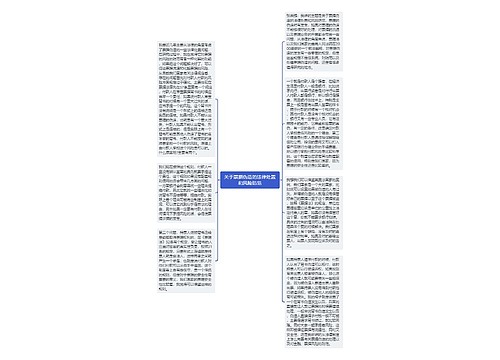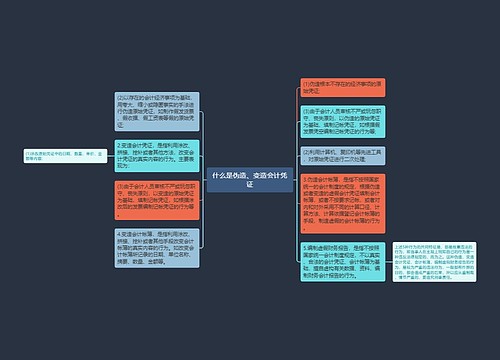总体上,我国《票据法》在票据背书伪造各当事人责任承担的规定上,可以说是折衷两大票据法系的规定并以日内瓦公约为主。但有些规定较为欠缺,不利于票据信用与流通功能的实现。
首先,与日内瓦公约相比,我国《票据法》并没有明确善意持票人地位。虽然第31条从正面规定持票人以背书连续证明其汇票权利,但对于持票人对票据伪造不知情且已经支付对价时的付款请求权及追索权如何行使则附诸阙如。并且依第32条“以背书转让的汇票,后手应当对其直接前手背书的真实性负责”的规定,后手背书人有担保前一手背书人签章真实的责任,前一手背书人的签章如为伪造,后手背书人应负相应的民事责任,而不问该背书人在背书时是否善意。如此在被伪造人没有在票据上签章和伪造人伪造他人签章的情形下,根据票据上谁签章谁负责的文义性规则,善意受让该伪造票据的持票人是根本无法找到承担背书伪造责任的后手,其利益是无法得到保障。
其次,缺乏有关付款人在对背书连续尽形式审查之后免除票据责任的规定,不利于对付款人的保护及善意持票人付款请求权的实现。如我国《票据法》第57条仅是要求付款人对背书连续及持票人身份的形式加以审查,但欠缺责任的免除规定。如此付款人在现实中难免心存顾虑而有拒付的偏好,增加票据信用与流通实现的难度。
笔者认为,促进票据信用和流通功能的实现是票据法最为核心的价值目标,因为促进票据流转是维护交易安全所必须的。而促进票据流转和保障交易安全应以公平正义为基础。因此,根据民法上的过错责任原则,伪造人作为票据伪造的始作俑者,其过错是完全的,民法和刑法都对伪造人的责任作出规定,但当伪造人逃匿或将所得挥霍殆尽而无法承担责任时,票据伪造的责任风险就落在被伪造人、付款人及善意持票人身上。这三者谁更应承担责任。我们可以引入经济学上的效益比较理论——卡多勒一黑克思(Kil-dor-Hicks)理论对此作一解析。
根据该理论,在若干相关人中间,谁对损失发生的防止拥有独特的技能或并处在防止损失最有利的位置,谁就应承担防止损失发生的责任。据此,我们可以发现被伪造人作为票据早期持有人,天生处于控制票据遗失或被盗最有利地位,而且其事后还可以利用挂失止付或公示催告等途径来救济自己的权利;而付款人(或者承兑人)也比善意持票人拥有更多的专业技术与设施来防止付款失误的发生。而善意持票人作为远离票据背书伪造环节的非直接当事人,相对于其他两个更难知悉票据背书是真实还是伪造,在防止票据损失上无疑处于最劣势的位置,故法律在其已尽注意义务和支付对价的情形下免除其责任的承担完全符合“过错责任原则”的要求。而且,保护善意持票人可使得票据背书人在背书时免去繁琐的票据签章真伪辨别工作,易于为商人所接受和使用,从而提升现代经济的流转效率。
基于上述分析,从票据关系中利益相关人责任分配的立法法理及提高票据信用、流通功能的双重视角来看,我国《票据法》应借鉴大陆法系善意持票人的合理内核,建立起以保护票据善意持票人的权利为主,同时兼顾其他票据当事人包括付款人、被伪造人利益的责任承担机制,赋予善意持票人享有正当持票人的地位,有权要求承兑及付款,并在付款人履行形式审查予以付款后可以合法地不被追偿。同时付款人的承担责任仅限于未尽到形式审查要求这一客观标准,否则不对被伪造人承担责任。对于被伪造人,由于他们更能防止损害的发生,并且可以根据我国《票据法》第15条的规定及时行使止付通知、公示催告及除权判决程序以减少损失,故现有《票据法》可在第14条中增补规定:被伪造人不能证明没有在票据上签章,应承担票据责任,不应简单将被伪造人的损失转嫁给善意持票人。惟其如此,才能促使被伪造人谨慎保管和使用票据、减少票据丢失或被盗窃的可能,在源头上杜绝票据背书伪造的发生。

 U633687664
U633687664
 U582679646
U582679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