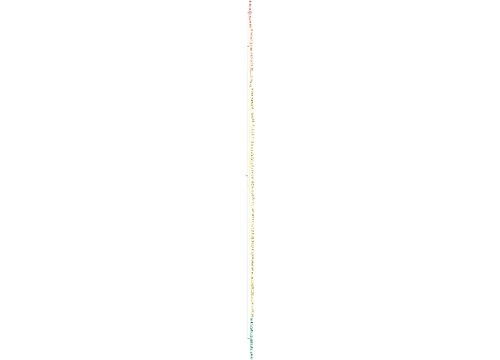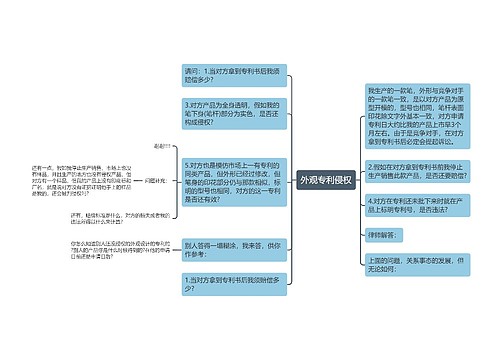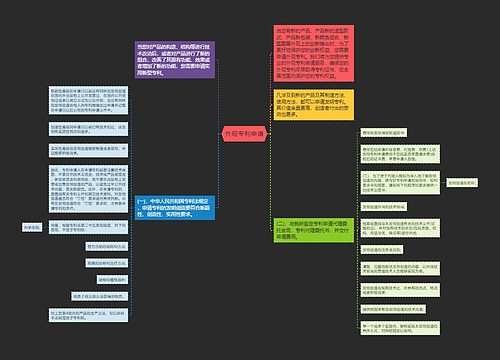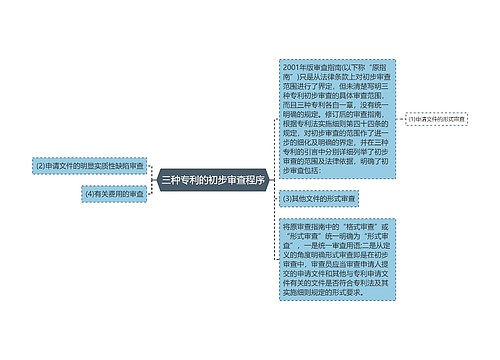我们应当看到,现今药品专利保护制度对人的健康权的实现已经带来消极影响。其主要表现是:第一,由于专利权的垄断性,权利持有人可以控制药品的生产和销售。近年来,在国际贸易中由价格高昂的药物治疗费用引起的发展中国家的健康危机问题引起了全球公众的关注,TRIPS协议一方面为发展中国家技术转让提供了法律环境,但另一方面,严格的药品知识产权的保护却导致了专利药品的昂贵价格以至于超出许多贫穷国家的患者的承受限度,从而影响不发达国家的居民获得治疗5;
艾滋病药物是一个典型代表,但除此之外,专利药的价格与制药公司的垄断密切关联,又受到专利权的保护和支持,因此大量其它因为拥有或控制药品专利权的大公司阻碍了其它公司和产品的竞争,而使救治威胁生命的药品价格高得让人购买不起。
据IMS2002年统计,世界前10名制药企业包括辉瑞、葛兰素史克、默克、施贵宝、阿斯利康、安万特、强生、诺华、惠氏,他们的销售额总和占全球药品市场的58.4%,专利则是他们获取利润的主要手段。一方面,以美国瑞士等发达国家药品生产者为代表的权利人认为,研制药物要投入巨额的资金和大量的时间,医药公司必须尽快收回成本才有可能维持良性循环,如果药厂研制的新药得不到保护,将没人愿意继续投入研制新药。
另一方面,以南非等艾滋病情严重的国家为代表的药品受众认为,当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都面临着艾滋病威胁时,对专利权人的保护理当退居到一个次要地位,公共利益才是首要问题。也正是药业巨头们的“漫天要价”
对于这种矛盾,在找到两种利益的完美平衡点之前,专利制度对专利权人的保护应当退居到一个次要层次,“公共利益才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6第二,由于专利实施的限制性条件,权利持有人可以阻止他人获得药品专利技术,甚至在其政府的支持下限制贫穷国家及其人民获得强制许可。
因为TRIPS协议给予药品的专利保护为发达国家制药公司提供了合法的垄断权力,却严重损害了发展中成员获取急需的,不可缺少的廉价药品的权利。人命大于天,为解决公共健康问题,降低药品价格,在不违反TRIPS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采取灵活措施,更多地从人道主义出发救助艾滋病等重大传染病的患者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
第三,由于专利权的利益推动,制药业的研发投资首先投向市场上最有利润回报的疾病,而不会当然考虑贫穷国家的需求。实际上,发展中国家也有顾虑,除了没有能力消费昂贵药品外,还有另一种担心:药业巨头为了保住自己预定的利润和销量,很可能转向研制和生产富国急需的药品,比如治疗心脏病、糖尿病和癌症等所谓“富贵病”的药品。
因为富国的病人相对更能承受药品价格的压力,满足大药厂维持原有利润水平的要求。因此,他们可能会把肺炎、艾滋病、痢疾、肺结核和疟疾等疾病放在一边。据WHO提供的数据表明,在1975年至1996年开发的1223个化学制剂中,只有11个是用于治疗热带疾病,其余都是治疗阳痿、肥胖和秃头等利润丰厚的药品。
第四,由于专利授予适用于具有新颖性但疗效与在先专利药品相似的产品,从而导致某类专利药品的生产和分配日益集中于少数企业之中。
上述情况表明,药品创造者的专利权与药品消费者的健康权存在明显的冲突。到底是专利阻碍了保护人类健康,还是保护人类健康抑制了专利创新,这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目前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这触发了我们深刻的思考,在专利权人的经济权益与人类的普遍生存权发生冲突时,尊重知识与尊重健康并举的规则该如何定制?专利制度的目的与公共利益关系的深刻内涵是什么?
不容质疑的是,这两种权利之任何一种在其自身的背景中都是有价值的。这是因为,创造者对自己的智力成果享有权利和社会公众分享智力创造所带来利益的权利,都是国际社会承认的基本人权。但是遵循人权优先性的尺度,在特定的情况下,某些人权可以优先于其他人权。具言之,“那些同人生死攸关的的产品一经产生,便成为全世界的财产,但创造者因而有权获得补偿。”在这种例外情形中,人的健康权应高于包括专利权在内的知识产权。
围绕着专利权与公共健康问题上的争端,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力争下,《多哈宣言》确认了困扰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遭受痛苦的公共健康问题的严重性;强调知识产权保护对于新药品开发的重要意义,也承认这种保护对价格的影响所产生的状态;同意TRIPS不应成为缔约方采取行动保护公众健康的障碍。维护公众健康的“行动”,是通过阐释TRIPS关于公共利益的灵活性条款来实现的:《多哈宣言》秉承公共利益原则,以人权优先性的尺度,协调药品专利权与健康权之间的冲突,这一做法无疑是后TRIPS时代对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要调整。

 U882214155
U882214155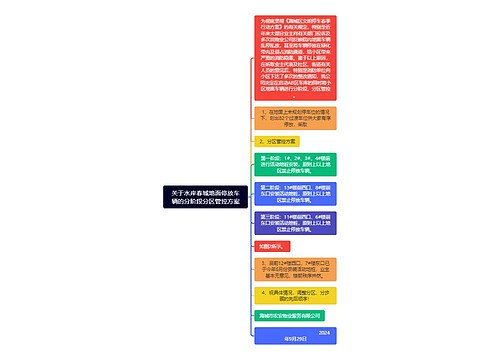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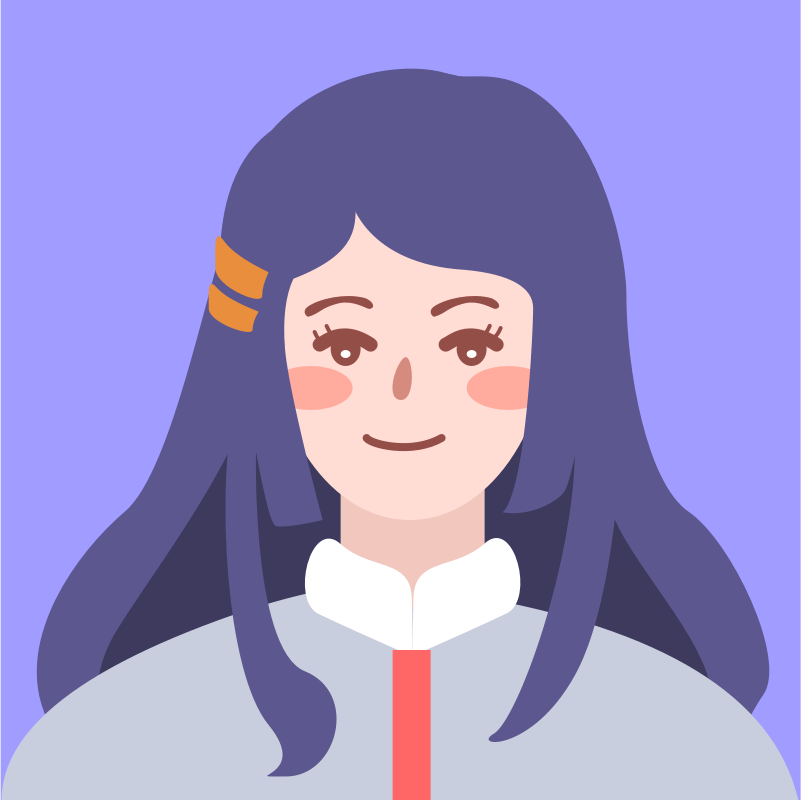 U782058360
U7820583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