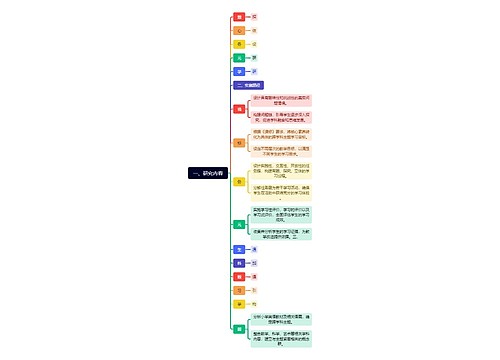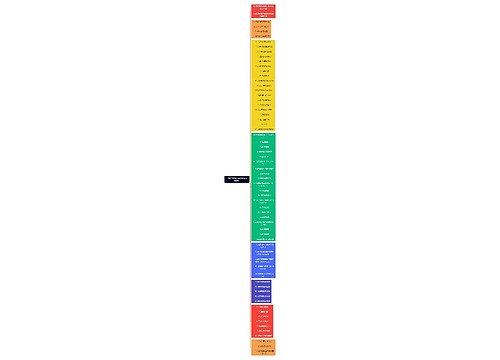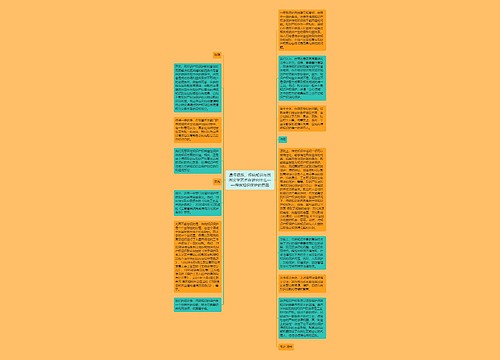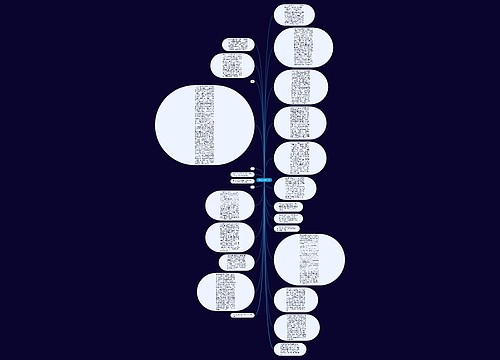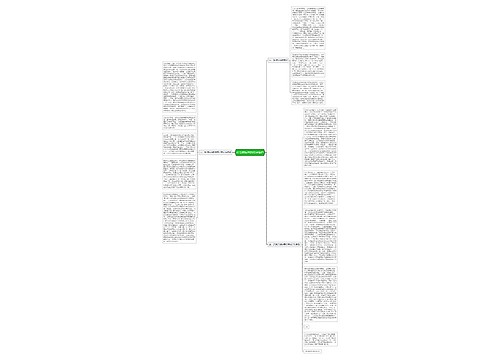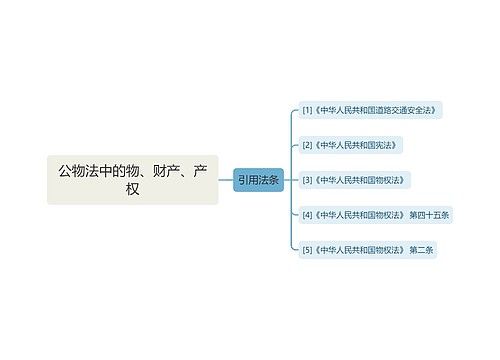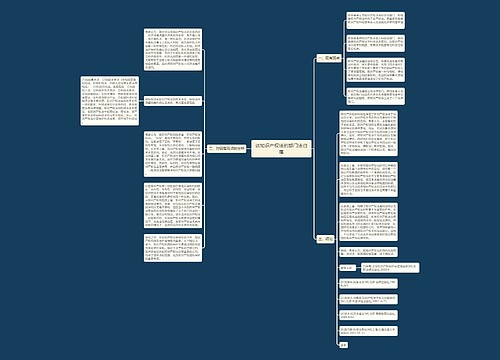一种制度的有效建立和贯彻,依赖于一定的条件。这是考虑用知识产权法保护传统知识所不能回避的问题。知识产权作为一种私权,其核心价值在于界定人们因智力成果及相关成就所产生的各种利益关系。当人们考虑将该制度延伸到传统知识领域时,不得不 回答后者与知识产权既有客体间是否具有共性的问题。
我们认为,这两者是否同质固然应该予以考查。但是,更需要注意到,即使传统知识和既有知识产权客体相同,也不能证明它就应该在知识产权范围内受到保护。因为,知识产权制度从来就不是,现在也不是保护智力成果及相关成就的唯一工具。例如,科学发现一般并不受知识产权保护;所谓“公有领域”之中的智力的成果实际上也不受知识 产权法的保护。
其实,用知识产权保护新的客体时需要解决的更关键的前提条件是客体的确定性和主体的确定性。这两者是成功协调利益关系所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就客体而言,众多的概念虽然都各有道理,但都无法准确在界定作为知识产权客体的传统知识到底包括哪些传统成果,它和不受知识产权法保护的文明成就的界限何在。而这种边界的极度模糊性 必然使得通过财产权制度来理清权利义务关系的目标落空。
至于主体,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仅就学者们提出的各种建议而言,至少包括以下几种 :国家、民族、社区和个人等。而事实上,任何一个主体都很难被确认为某一区域内传 统知识的唯一的所有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有关部门起草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法的过程中,有一种意见认为 ,国家应当然地被规定为唯一的主体,我们认为这种具有浓厚国有制色彩的构想是需要 审慎对待的。
我们无意否定知识产权制度在保护传统知识方面的价值。相反,正是由于传统知识与 知识产权客体之间的深刻的内在联系,使得知识产权法成为传统知识综合保护制度的有 机组成部分。
原则上,传统知识中任何一项可以被特定化,能够确定具体主体的成果,如果符合法定的其他条件,都能够直接地为知识产权法所保护。例如,民间舞蹈可以受到邻接权的保护;传统标记、地理名称可以受到商标法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传统医药、工艺可受到商业秘密法的保护;等等。知识产权法对传统知识的保护还常常以一种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即当地人合法地利用它进行再创作时,有关成果受到知识产权法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知识所有者虽然并非知识产权权利人,但是,其利益在以下方面得到了间接的肯定:文化渊源的确定、完整性的尊重、文化影响力的增加,以及特定情形下分享经济利益的机会,等等。当然,对知识产权保护传统知识所有人利益的局限性 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
事实上,传统知识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对它的保护需要依赖综合的手段,既需要法律 的调整,也需要政策扶持。略加分析就不难发现,许多法律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传统 知识的保护问题。例如,人权保护、文物保护、环境保护、旅游管理及文化市场管理等 法律制度。
另外,还有一些专门法律对保护传统知识也具有重要意义。例如,1997年5月20日颁布 的《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2000年9月1日实施的《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 例》等等。
从性质上来说,上述诸种法律多属于公法,其作用方式主要是通过国家支配公共资源 ,维护、促进传统知识成就的存续和繁荣。
尤其不能忽视的是,传统知识保护是一个全球性的议题。在这个领域中的国际合作是不可或缺的。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各国以及相关的国际组织进行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例如,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制定的《关于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达以抵制非法利用和其他不法行为的国内法律示范条款》、1992年6月5日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签署的《生物多样性公约》、1995年联合国的专门工作组发表的《保护土著人遗产的原则和方针草案》、2001年11月3日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大会通过的《国际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条约》,等等。
改造知识产权制度以满足保护传统知识的需要有着巨大的困难。具有300年历史的知识产权法律是工业时代的产物。经过不断的修补,已经成为一部服务于现代工业、信息社会的严密的法律机器,其“制度上的禀性”决定了它不能成为保护传统知识的主要手段。就算是把这部机器交给了传统社区或者它的代理人,往往也很难有效地运转。
我们的结论是,传统知识的保护是一个世界性的命题,解决它需要综合利用法律、政策等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