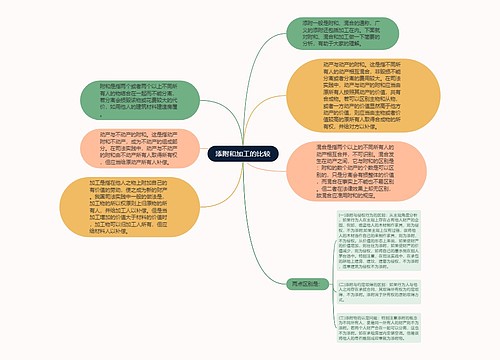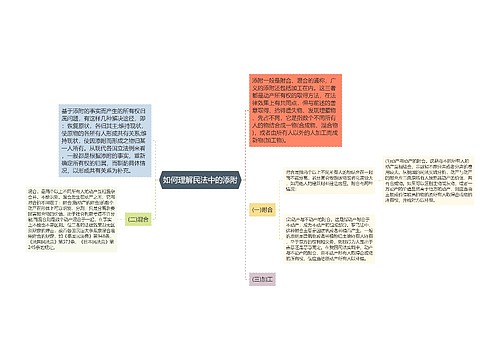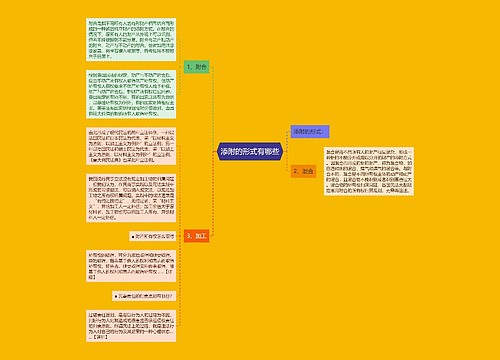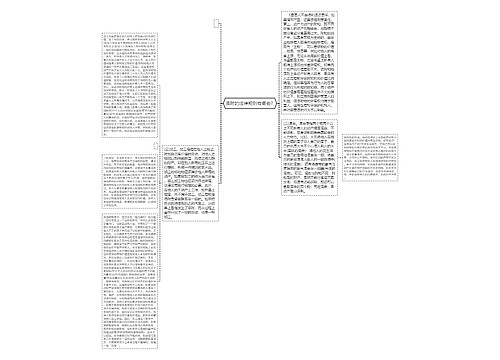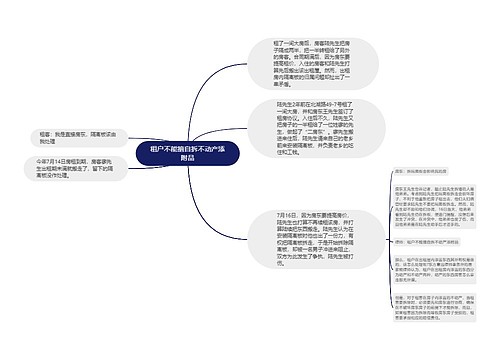周文认为,有主财产、无主埋藏物以及所有人不明的财物都可以成为刑法第270条的“埋藏物”范围,从而成为侵占的对象。 笔者对此持不同意见。
刑法第270条使用“他人的埋藏物”叙述方法, 一来表明该埋藏物在所有权上是属于他人,而非埋藏物的发现人;二来表明立法者并非对所有埋藏物的侵占都纳入刑法治罪,而只是将部分埋藏物纳入侵占罪对象范围。“他人的埋藏物”就是指有主埋藏物,不包括无主物,应当予以肯定。
当然,立法者可以不受理论限制,按实际需要对某种行为进行犯罪化规定,但这里也有其合理性问题。实际上,对本质上属于确权纠纷的占有“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而拒不交出的行为进行犯罪化规定,既完全没有必要,又存在诸多问题。第一,“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一律由国家取得所有权这一民法上的规定,在很大程度上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本位主义观念的产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越来越强调民权优先的民法学界对此规定的合理性已日益提出疑问。在这种状况下,对埋藏物的确权争议予以刑事干预,不仅影响民法观念而且也影响我国整个市场经济法律观念的真正确立。第二,即使民法通则规定“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归国家所有具有合理性,国家仍有多种强制手段来解决它与发现人之间就该埋藏物归属问题产生的权属纠纷,也没有必要运用刑罚手段。国家只有在运用民事的、行政的法律手段和措施,仍不足以抗制某种危害行为时,才能运用刑罚方法,这是现代刑法谦抑原则应有之义。(注: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第三,如果对发现了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而拒不交出的行为人定罪,首先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国家是否可以受害人身份起诉发现人侵占罪(因为侵占罪是自诉案件)?如果不可以,则必须将侵占罪改为公诉罪。一律改为公诉罪,从刑法价值角度讲,则成本太高。即使按周文的建议该罪程序上以自诉为基础,“例外”为补充,国家行使权利通过刑事诉讼取得埋藏物所有权,但接下来仍存在问题:由于这种所有权在民法上是不确定的,一旦真正的物主出现,国家就必须将该埋藏物返还物主。而真正的物主从本意上可能根本就不打算去追究发现埋藏物的发现人的刑事责任,不仅如此,可能他还要感激发现人(因为发现人的发现才使他现实的拥有财富),可是国家却越俎代庖已先让发现人下了大牢!窃以为,国家与民争利本已欠妥,使用刑罚手段与民争利更不应该,而以假定所有人身份行使刑事诉权以解决一个本来是平等主体间通过民事程序即可解决的民事纠纷则是错上加错!
鉴于上述认识,笔者认为: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以及”无主埋藏物“都不应当是刑法第270条”他人的埋藏物“的范围。 对于非法占有这两类埋藏物拒不交出的行为仍应按民事确权纠纷进行处理。
至此,有的同志可能提出,实际生活中地下埋藏物中的有主财物不多,大多数是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而且文物居多,将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和无主物排除于侵占他人埋藏物之外,不利于文物的保护。笔者认为,地下文物不是“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而是国家财产。道理很简单,文物保护法第4条已经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所有地下文物都“属于国家所有”。这说明地下文物是所有权明了的财产,不属于所有人不明的财产,发现文物后非法占为己有不交出就是侵占国家财产的行为,不存在确权争议问题。因此,地下文物属于有主财产且是权属关系明了的国家财产。不过,笔者赞同刑法第270 条的财物是私人财产的观点,因为立法者设立“不告不理”程序表明刑法第270 条的埋藏物立法本意不包括国家财产,而是私人财物。依该条侵占罪来打击侵占国家文物的行为既违背立法本意也不一定收到期望效果。笔者认为解决既要保护地下文物的国家所有权又不违背第270 条的原旨这一矛盾的切实可行的途径是在现行刑法分则第六章第四节妨害文物管理罪中增加一条侵占文物罪,置于第328条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之后。 其对象可以是包括以下埋藏文物在内的所有文物,诉讼程序上设置为公诉罪。这样既解决了第270 条侵占罪的问题(还其本来面目)又完善了文物犯罪的规定,可谓一举两得。

 U633687664
U633687664
 U582679646
U582679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