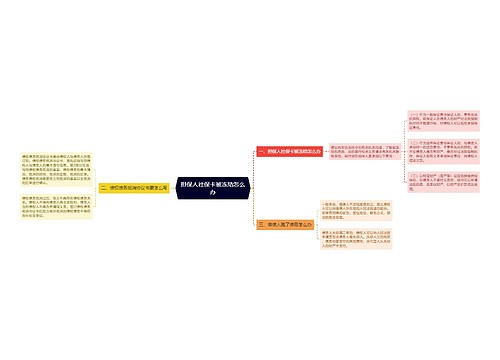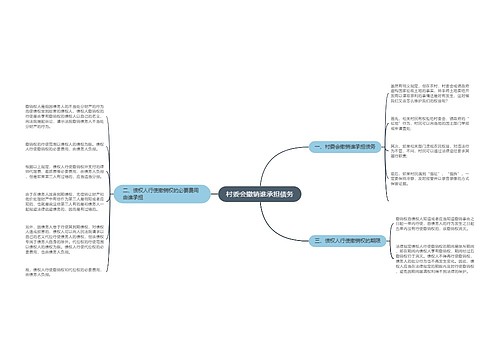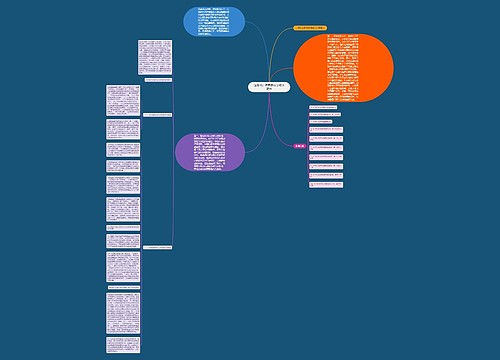(一)根据现在通行的学说,权利系特定利益和法律之力两项要素所构成,法律之力指的是权利人支配标的物、请求他人作为或不作为以及请求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也就是:这个法律之力就债权(相对权)方面来说指的就是请求权。在这个通行的学说下,作为法律之力的请求权与债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梁慧星先生正确地指出:债权系请求权的基础权利,请求权系债权所具有的作用之一。根据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的规定,请求权因时效而消灭,也就是说,这个法律之力(请求权)因时效完成而消灭,既已消灭,则其自身已不存在,为何又说此时只是对方产生一个抗辩权而已?请求权与抗辩权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请求权的消灭与抗辩权的产生是两个不同的内容,其间联系虽然密切,但不能混为一谈。法律之力(请求权)既已消灭,也就其请求法院强制执行力也业已消灭,也就是此时的权利上的作用已不存在,即使对方当事人不抗辩,其法律之力已丧失的特定利益还具有强制执行力么?这个规定,与权利的基本概念产生了严重的冲突。也就是说,此时采纳抗辩权发生主义理论与权利的基本理论发生了一个难于调和的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反而,法院主动适用诉讼时效恰恰与现在通行的权利的基本理论是吻合的。
(二)设立时效的目的和理由是为了维护既存秩序,促进交易安全和降低成本,以及起到促使权利人积极行使权利。也就是说,设立时效是在私权保护方面与社会的大利益作利益衡量之后,以牺牲一定程度的公平正义(私权利)为代价保护社会的大利益(即既存秩序、交易安全、降低成本)。因此,法院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并不违背民法时效制度的本质和市场经济的要求。同时,也并不象梁慧星先生所指出的,违背诚实信用的原则,因为如果说法院主动适用诉讼时效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的话,倒不如说法律规定时效制度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因此,梁先生的这一论断是没有说服力的。
(四)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们论述请求权时,继受了德国理论,实际上主要是从请求权在实体法的角度来论述,忽略请求权在程序上的功能。请求权首先当然说明了一种实体法上的地位,但同时它也表明了一种程序上的功能,诚如拉伦茨所指出的:“这个概念不仅表明一种客观(实体法)上的权利,而且也表明一个特定人针对他人的特定请求可以通过诉讼来主张和执行,《德国民法典》的请求权的概念就是如此……尽管请求权时效的实际意义在程序中更为明显,但民法典仍然是将请求权时效作为实体法的制度加以规定的,这样一来,就使以诉讼法的观点来考虑程序问题的重点转移到实体法的考虑上来。”非常遗憾的是,包括德国、台湾地区以及我国的民法学者们,对请求权进行论述时,大多数并不对这一明显的具有程序法上功能的请求权的意义作出深入的探讨,以致造成理论和实践中的脱节和混乱的状态。实际上,从德国民法典的角度来考察,其对请求权的规定是从实体法的角度来规范的,但是在很大的程度上无法摆脱请求权的程序功能,请求权罹于时效时,相对方取得足于对抗该请求权的抗辩权发生,此时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并不消灭。这是非常典型的请求权在程序功能上对实体权利的制约。但德国民法典却规定请求权因时效而消灭,该规定与德国理论界所持权利的基本理论以及与司法实践都产生相悖的冲突,无法理顺。实际上也无法理顺。台湾民法典继受了德国民法典的规定以及德国民法理论,同样把这个矛盾带进了台湾民法学界,至今也无法理清这个悖论。
(五)无论是《德国民法典》还是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典》,对于请求权的反对权——抗辩权均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而这些规定应该是请求权的主要问题之一。因此,只从请求权这一单一的角度,无法说清请求权本身。

 U633687664
U633687664
 U582679646
U582679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