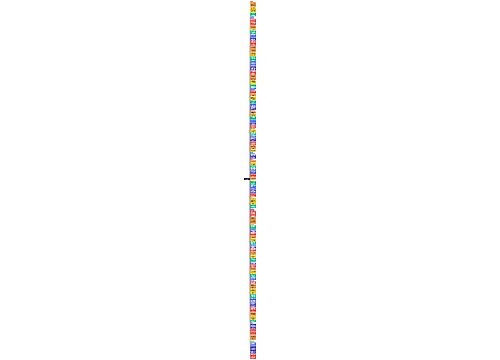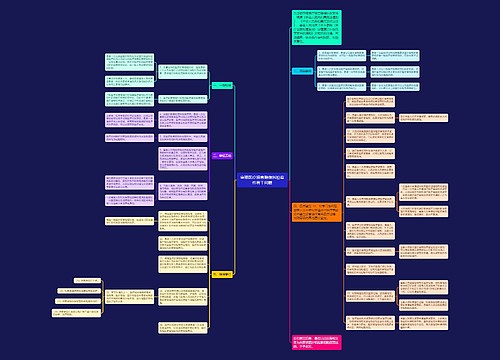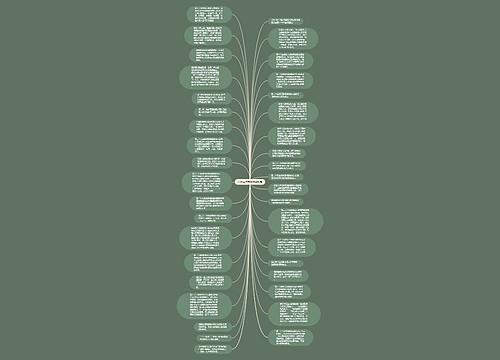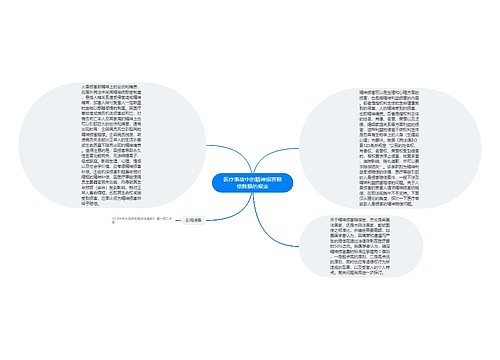我国现行处理医疗纠纷的实体法律规范主要有《民法通则》、《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及《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和《关于审理人身损害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等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在对医疗纠纷案件的审判在立法上不断的予以了完善,但多层次的诸法并存想象由此也形成了一些矛盾和冲突。在司法实践中也确立了“二元化”体制,即:对特殊医疗侵权行为——构成医疗事故的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一般医疗侵权行为——非医疗事故适用《民法通则》等民事法律和相关的司法解释。
但是由于《条例》中规定的赔偿范围和标准明显低于《解释》,由此产生的消极后果是:患者由于具有更严重过错的医疗行为造成相同的损害后果,却得到的是更低的赔偿这样不公平的待遇。如此局面无疑会动摇法律的公信力和导致诉讼的投机行为。因此,肃清在医疗纠纷案件中的法律适用是司法途径解决医疗纠纷首要问题。
对医疗损害赔偿案件中的法律适用之争主要体现在对待《条例》的态度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第一条规定,条例实施后发生的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诉到法院的,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就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答记者问》(以下简称《答记者问》)也体现了在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纠纷案件的审理上优先适用《条例》。
然而笔者认为,“二元化”体制对构成医疗事故的适用《条例》给予受害人较低的赔偿,在事实上侵犯了医疗侵权被害人获得实际赔偿或者完全赔偿的权利,而对医疗侵权机构给予了特殊的保护;“二元化”体制中适用的《条例》在没有经过人大及常委授权的情况下,对应属于只能制定法律的法律事项而不属于行政管理职能事项的医疗损害赔偿制度做出了规定,并直接影响到法院的审判工作,超出了行政机关的管理职能范畴,在法律上侵犯了人大及常委的立法权和干预了法院的司法审判权,是行政权力的过度扩张,甚至动摇了我国的根本政治体制。而《答记者问》对审判工作中适用《条例》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做出的说明并不具有说服力,如果这不是最高法院个别领导的看法而是最高法院的做法的话,那么最高法院对区分不同案件分别适用法律的做法是对法制统一和法律尊严的不尊重。
至于将《条例》置于特别法的地位,则是犯了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理论中的常识性错误,因为该理论是解决同位法的法律规范冲突的原则,而不能用于解决不同机关制定的不同位阶的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
《条例》将医疗事故从医疗侵权行为中划分出来,应该仅仅是适应医疗卫生的行政管理职能需要,其适用范围应该主要存在于行政管理和调解领域。而在民事裁判中,构成医疗事故的侵权和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侵权并无本质区别,对同属于民事侵害纠纷的案件搞区别对待予以划分,对于开展审判工作和实现诉讼任务,即制裁民事违法行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没有任何积极意义。
有人从医疗行为的高风险性、医疗行业的公共福利性、医疗机构的承受能力和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来考虑,对医疗事业的发展予以特殊保护。笔者认为,法治也是追求效率和公平原则的,从效率原则来看,的确有保障医疗事业发展的必要,但却不能以违背公平原则和破坏法制统一为代价。完全可以通过建立医疗损害保险制度、医疗行为豁免制度和依法确立限额赔偿等制度等措施来实现。至于用所谓的“羊毛出在羊身上”理论(即医疗机构对构成医疗事故的受害人的赔偿仍然出自患者或将转嫁给患者),来论证限制医疗机构对构成医疗事故赔偿的合理性则近乎诡辩了。笔者不认同这通过种损害弱势方的权益来减轻医疗机构责任的做法,即使这是出于对所有患者整体的利益保护。事实上以损害少数构成医疗事故的受害者的利益来“保障”多数患者利益的做法,这一与“分散风险”原则背道而驰的做法本身就是错误的,是不公平的。
我们不可否认《条例》与过去的办法有着诸多的进展,然而法院在审判医疗纠纷的案件中,仍应该对适用的法律予以审查,正确的适用法律。而《条例》作为行政法规,其制定主体超出了立法权限,内容中的限制赔偿规定与《民法通则》的实际赔偿原则相抵触,而在实践中“二元化”体制下适用《条例》的后果将造成适用法律的混乱,也不利于对患者合法权益的应有保护。因此,在医疗纠纷案件的审判中,《条例》最多只能起到“参照”的作用,而不能作为裁判规范予以适用,更不能在对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损害赔偿案件中优先适用。
有鉴于此,摒弃“区分不同案件适用法律”的做法,在目前情况下统一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民法通则》和《解释》,且尽快由全国人大单独制定一部专门处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的法律——《医疗损害赔偿法》,或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处理全部内容在民法典中设专章、专节予以专门规定。这对于法制的完善和统一以及现实中顺利开展医疗纠纷审判工作,公平公正的解决医疗纠纷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U182637395
U182637395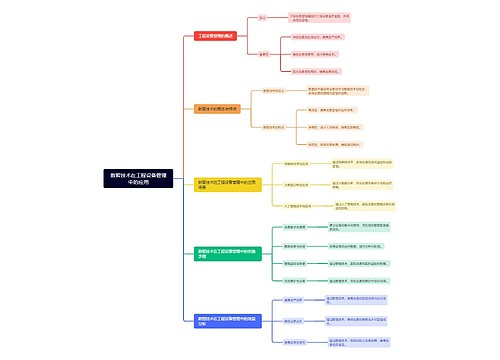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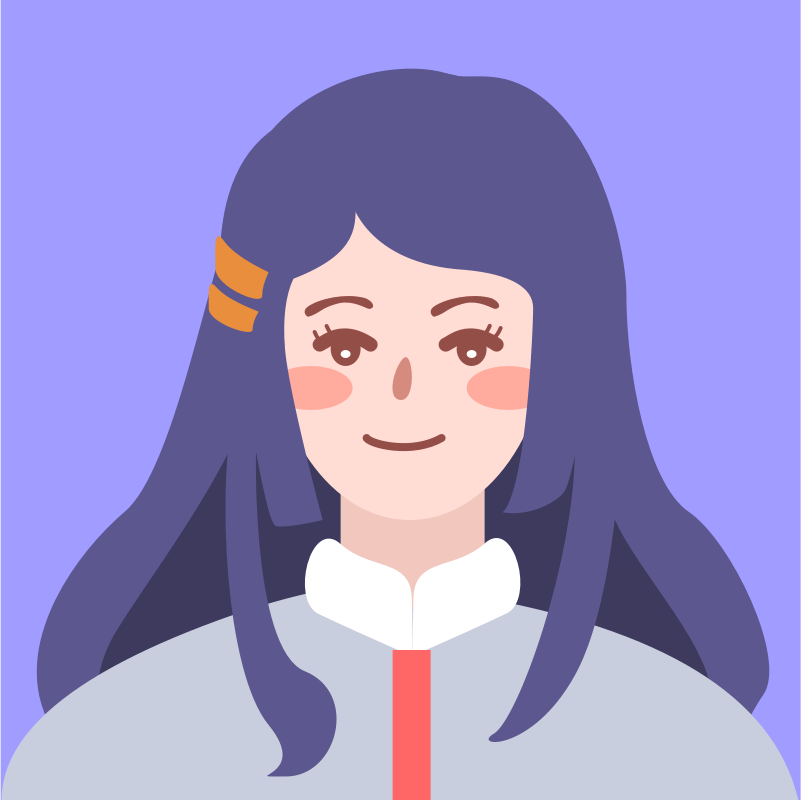 U582017500
U582017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