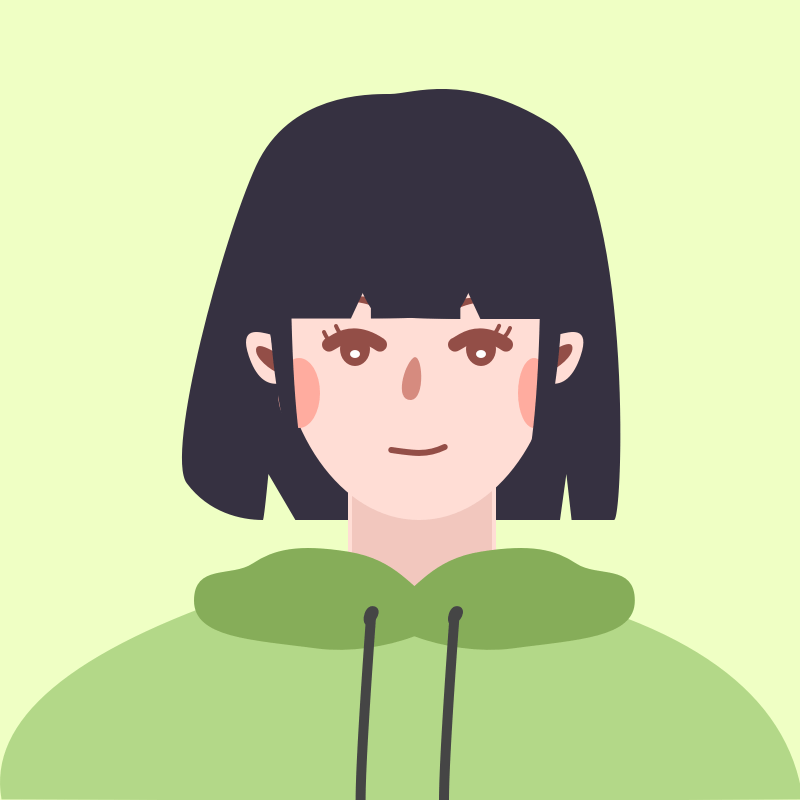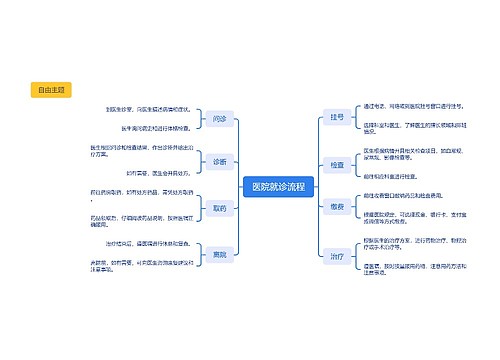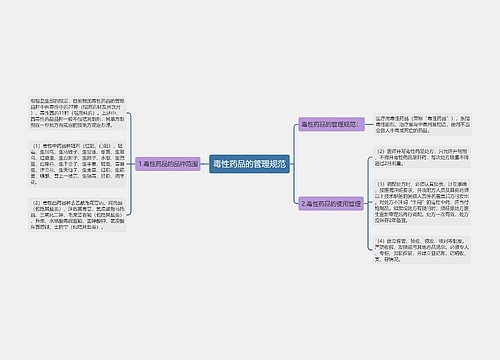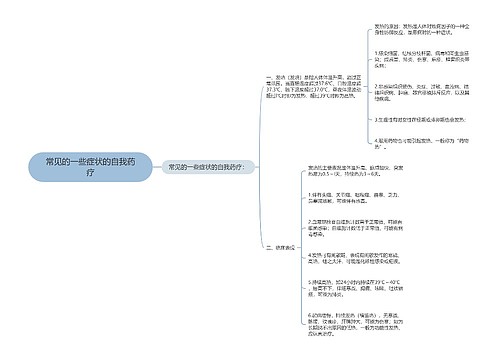主持人:医院同患者签订了“手术同意书”是否就算尽到了告知义务?什么情况下才算患者已经知情同意?
周文杰:医疗活动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手术活动的侵害性,二是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这决定了患者必须要有手术知情权。这也是行政法规的强行性规定,医院必须及时、全面、准确、详细地向患者告知医疗的风险,患者有选择的权利。我国《民法通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此都有明确的规定。作为医院来说,告知义务通常应当是一种充分告知义务,包括患者赖以作出医疗决策的所有信息。具体来说,可以通过四项标准进行衡量,即全面、通俗、精确、真实地告知。医院至少应当将教科书中所列举的常见并发症告知患者。不常见的并发症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果后果严重,同样应该告知;而告知应该通俗易懂,因为其目的是为了让患者知情,如果都是专业术语,患者无法理解,也就没有达到告知的目的;此外,医院的告知应当严谨、完整,不能有歧义,要将不良后果产生的原因和后果均告知患者。最后,医院向患者传达的信息既不能夸大疗效,也不能隐瞒不良后果。
朱世龙:“手术同意书”其实只是“知情同意”中的一种表示方法。医生们都很清楚,手术中发生的意外一般只有两种:一是由于疾病本身的变化所致,医生往往无法去尽力避免,可一旦发生,后果很严重,所以要和病人及家属说清楚。另一种是由于医生本人过失的情况所引起的并发症,如将手术钳、纱布丢在腹腔等,这些都可以通过医生的意志所控制,所以这些情况一旦发生,医生一定输官司。
马亚娟:当然,医院履行告知义务,应该有个“度”。因为患者及其家属由于知识水平的差异,“知情”水平各不相同,对医生的解释理解也就不同。医生力争把情况向患者或家属讲清楚,但不可能做到像给学生上课那样细致。在平诊情况下,医生可以尽量做到对病人病情的详细解释,但对急诊病人往往因病情紧急而很难做到。有时一个病人头一天还好好的,第二天可能突然就发病了。这种病情的突然变化,不要说病人不知情,就是医生也很难把握和预料。医院如果从患者的利益出发,采取保护性医疗制度,这时候,患者的知情权应该让位。比如某些信息(如恶性肿瘤)的真相如果如实告诉病人,可能会产生消极作用,造成病人精神崩溃,免疫力下降导致病情恶化,不配合治疗或者拒绝治疗,甚至导致自杀,可暂缓告知。但是,不得剥夺病人家属的知情同意权。
主持人:生活中,确有患者或家属看到“手术同意书”,感觉在签“生死契约”,担心医院将此作为“护身符”来推卸责任。
朱世龙:这种看法是对医院的误解,毕竟“手术同意书”不具有法律效力。“手术同意书”的每项都是医院通过术前会诊讨论,按照医疗规程,严格论证制定的。患者可根据医院的医疗条件、技术水平、自身的状况同意或拒绝手术,既不存在医院推卸责任问题,更不存在“生死协议”之说。因为术前谈话及签字手术同意书根本的意义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告知,第二就是征得同意。手术本身毕竟是对人体的一种损害,有些手术还涉及器官的摘除等,因此必须在患者完全理解手术可能带来的结果并完全自愿接受的基础上,手术才能进行。当然,法律法规规定的紧急情况下的抢救性措施除外。
周文杰:将签订“手术同意书”视作对医生的免责是完全错误的。“手术同意书”不具有免除医务人员因医疗过错而给患者造成损害后果,应承担的民事责任的法律效力,法律更不会承认任何“生死契约”。在临床工作中,一些医务人员在手术同意书中向患者特别提示了这种风险的存在,同时要求患者自己承担这种可能出现的风险。例如,“如出现以上问题,医院概不负责”或“医院不承担任何责任”等免责条款。按我国《合同法》第53条规定,合同中有关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免责条款无效。因此,上述手术同意书中“医院概不负责”或“医院不承担任何责任”因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而归于无效。
主持人:大多患者或其家属,在签署“手术同意书”时都有“看不明白,也不敢有异议”的感受,更是质疑其为“霸王条款”。
朱世龙:这也是民众普遍存在的对医疗机构信任危机的体现。在我们经历过的医疗纠纷诉讼中,患者几乎都会提出医院的“手术同意书”是格式合同,是被强迫签署的。我们也建议卫生行政部门改变目前不同医院“各自为政”的知情同意书,代之以统一、规范的文本;用“我同意”、“我了解”等表达方式,代替对患者的强制和命令色彩,以换取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和配合。
周文杰:希望相关立法部门尽快出台配套的法律法规和赔偿办法,通过增加整个医疗过程的透明度和提高医护人员的医术、医德,来规范和约束医院手术签字这一习惯做法。在此强调一点,医院对患者知情同意的规范和标准不能只由法律界的专家来制定,应该更多地采纳医院内专事医患关系的工作者的意见,在制定时还须按照疾病划分,分别听取临床经验丰富的医疗专家的意见。但我不赞同将“手术同意书”统一文本格式。医学是一个专业性非常强的科学,疾病有很多种,即使是同一个疾病,医生也需要根据具体患者的情况制定不同的治疗方案,因此从形式上统一“手术同意书”并不现实。如果在“手术同意书”中给出患者过多治疗方案的比较,反而会让患者无所适从。我认为,规范医生对患者的告知行为、改善医患关系,并非只能通过书面的知情同意来解决,医患双方还应加强沟通,以此解除误会和隔阂,做到相互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