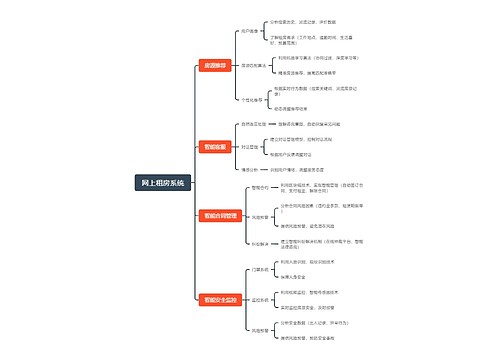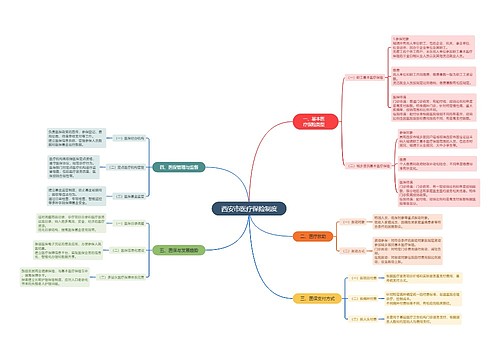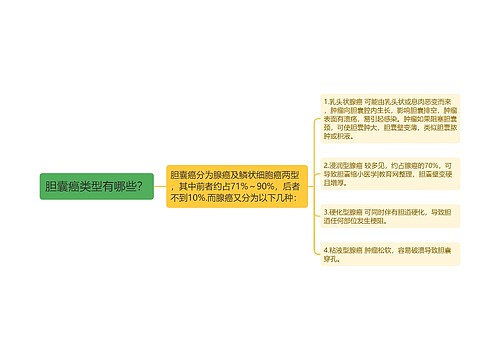格式合同,又曰标准合同、附合合同、定式合同,法国学者称之为附合契约,德国学者称为一般交易条款,在日本称为普通条款,在台湾地区,则称为定型化契约。“定式合同是由一方当事人,有关团体或国家机关制定的,或由国家法律直接规定的,包括全部交易条款的一种合同。定式合同在相同条件下适用于一切不特定的相对人,相对人没有就合同条款进行协商的自由,只能概括的接受或不接受全部条款。”由此可见,格式合同具有如下特征:
其一,合同条款单方事先决定性。格式合同的条款,即格式条款一般由一方当事人确定,实践中多为提供商品或服务的一方制定并提出,但也有些格式合同是由某些超然于双方当事人利益之上的利益团体、国家授权的机关制定的。出现此类情况,或是为了保障交易公平、维护当事人利益的衡平,或是为了实现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的职能,但无论如何对方当事人不直接参与合同条款的制定。
其二,格式合同的条款和形式标准化。在同等条件下,格式合同适用于一切不特定的相对人,不因相对人的身份等因素不同而改变合同的条款和形式。一方当事人与不特定相对人之间订立此类合同,是一种机械性的重复活动,每份合同的差异仅仅是对方当事人的姓名或名称的改变和可能的标的物数量的多寡。
其三,相对人在订约过程中的服从性。格式合同的一切条款和合同的形式都已定型化,相对人无协商余地,只能概括地接受或不接受全部合同条款,不能就合同条款讨价还价,这表明相对人在合同关系中处于服从的地位。
其四,格式合同以书面形式为原则。格式合同多由提供商品或服务的一方当事人印制成书面形式,原则上提供合同条款的当事人应将合同条款明确印刷于一定文件(如:车船票、保险单)之上,以便当事人了解。但在实践中也有非书面形式的格式合同,如理发美容合同。
“大约一个世纪,或许大约自1807年以来,政治思想、社会经济条件和法律开始发生持续性的发展变化。”无疑,格式合同乃现代经济活动的产物。在大量交易的社会,个别磋商的传统缔约方式,无法适应现代交易的需要。因此,格式合同的产生,首先是基于经济的发展,对高效率追求的需要;此外,社会中一些优势经济实体的产生,也为其产生提供了必要。
格式合同的应用可以简化交易方式,节省时间,降低交易成本;“有利于事先分配合同风险”;“可以促进企业合理经营”;“有助于改变商品的品质及降低价格,对消费大众有利”;“一个案件的判例可以为另一些类似案件的解决提供指南。”
但毫无疑问,格式合同的广泛运用,对契约自由所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其主要表现为:第一,由于格式合同的条款提供者多位事实上或法律上的垄断者,这就使得在缔约时,相对人缺乏选择缔约伙伴的完全自由,“拉郎配”变成了缔约的一个十分普通的现象。第二,由于格式合同当事人各自经济地位的悬殊性,这使得缔约当事人,尤其是经济上弱势的一方在缔约过程中所表示的“自愿”,不是真实的自愿。第三,由于一方在缔约时只能就另一方事先拟定的条件作出取或舍的决定,这就剥夺了当事人一方在缔约时进行协商的权利。第四,格式合同的条款提供者会经常利用自己优越的地位,拟定有利于己方而不利于另一方的条款,在形式自由的幌子下严重背离公平与公正原则。
因此,基于格式合同固有的缺陷,“如何在意思自治的体制下,维护合同正义,使经济上的强者,不能凭借合同自由之名,压榨弱者,是现代法律所面临的艰巨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