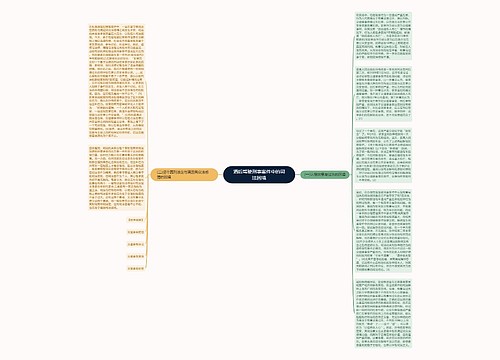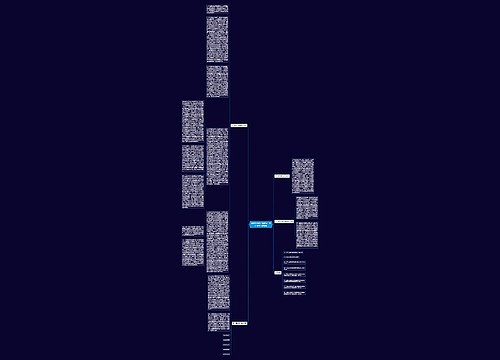另外,也有学者针对目前学界关于酒后驾驶肇事的刑法定性主要围绕着行为人的主观罪过进行,由此在结论上出现了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相对立的路径,独辟蹊径,主张避开酒后驾驶肇事案件中行为人的主观罪过,以客观行为作为标准,在酒后驾驶肇事案件的法定刑上坚持一种行为主义的进路。[⑤]理由在于对行为人的主观罪过的判断是一个缺乏标准且极富主观性的过程,会随着判断者的不同结论各异,因此立足于主观心态的分析思路无益于实际问题的解决。笔者认为,纯粹行为主义的进路有失偏颇,因为任何行为的构成都离不开主观意志和在意志支配下体现出来的外部客观行为两个方面,而且前后两个意志不总是体现统一性。后面的折中理论将进一步印证这一观点。
笔者认为,阻碍我国酒后驾驶入罪的理论依据在于我国所采用的结果无价值立场,即主要对行为所造成侵害法益的后果进行否定性评价。在违法性理论中,人们把违法性的焦点最终集中到对法益的侵害还是对社会伦理规范的违背上,进一步形成了结果无价值理论和行为无价值理论两种对立观点。
两种价值理论都有其致命的缺陷,如结果无价值理论对“法益”的界定模糊,既不能区分有形法益与无形法益,也不能辨别侵害法益的行为达到何种程度才能受到刑法的否定性评价;而行为无价值论基于社会伦理来判断行为是否有违法性,易使法与伦理混淆。于是出现了以结果无价值为基础,同时考虑行为无价值的折中论断,笔者赞同这种观点。因为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法益的价值、侵害的程度以及行为人当时的主观恶性,都会对影响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两个不可偏废。
以折中论作为酒后驾驶入罪的正当性基础,判断行为的违法性首先以侵害或者威胁法益为衡量标准,然后再根据社会伦理作出限定。具体到酒后驾驶行为,其对生命、财产安全的危险性是威胁或侵害到法益的确证,加之其具有明显的违背社会伦理性,可以说酒后驾驶行为本身是无价值的,但其违法性本质决定了该行为需要纳入刑法的视野。
在学者提出的不少建设性意见中,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如建议在现有的交通肇事罪“其他恶劣”中增加酒后、醉酒(包括超速等严重非法行为)驾驶等情形;可以由最高人民法院重新对“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作出解释,将“酒后、醉酒驾驶”、“超速行驶”和“无证驾驶”等直接作为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上升一个等级来追究其刑事责任;还有学者主张通过刑法的“扩张解释”解决危险驾驶问题,即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将危险驾驶的情况以“恶劣情节”和“特别恶劣情节”纳入交通肇事罪法定刑的第二档和第三档等等。
归纳之,无非就是修改刑法、通过司法解释和通过刑法修正案三种方式,具体采用哪种方式更适合国情,牵扯一个立法技术问题。立法技术高低与酒后、醉酒驾驶入罪的必然性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跟“制度依赖症”的疑问具有类似性,任何好的制度制定出来如果监管不力、执行不当都不会达到所预期的效果,但制定层面和执行层面分处不同的台面。我们在大胆创新出好的制度后,务必要依靠有效的运转机制、灵活适当的工作方法,也要仰仗执行者 的尽职尽责和兢兢业业,但不容忽视的是,创造出好的制度才是前提和基础。另外,我们绝不能因为一项改革会遇到种种困难就却步不前,畏首畏尾,哪一项改革与创新又会是一帆风顺呢?笔者坚持,将酒后、醉酒驾驶加以犯罪化。
总而言之,酒后、醉酒驾车对人身和财产安全造成巨大的威胁,将酒后、醉酒驾驶犯罪化处理适合当前我国交通安全和社会发展的形势,也能够反映人们道德要求的底线。而取结果无价值与行为无价值理论之长的折中理论,则为酒后、醉酒驾驶提供了正当性理论基础。相信随着立法技术的不断提高,随着刑罚、行政处罚等内在体系的协调,酒后、醉酒驾驶入罪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

 U633687664
U633687664
 U582679646
U582679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