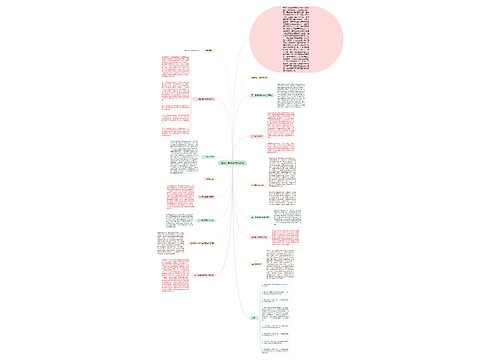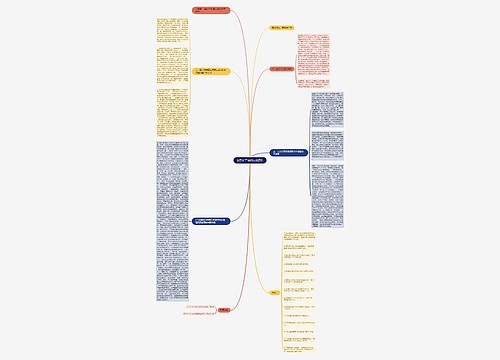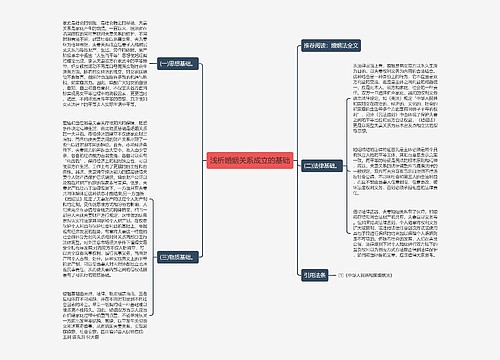有人提出,违反忠诚义务的民事责任可以包括“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对于造成对方精神痛苦和精神创伤的,可以适用精神损害赔偿,以一定的金钱,物质来惩罚过错方,补偿慰抚无辜方”。①这些责任方式简单地,想当然地套用了一般民事责任。在婚姻关系这片与人的情感世界密切相关的领域中,这几种责任方式的在操作上可行性值得怀疑。
例如“停止侵害”,且不论具有真正感情基础的婚外性行为是否仅凭一张“停业侵害”的判决书就可以作个了断,用法律的强制手段规范私人的情感活动往往会引起当事人的逆反心理,在本已恶化的夫妻关系中雪上加霜。即使排除了婚外性行为的干扰,接踵而来的“冷战”也可能使婚姻关系归于终结。如果真的出现了上述情况,这种责任方式到底是在“停止侵害”还是在“加深侵害”?
又如“恢复名誉”,问题在于:“到底是恢复谁的名誉?”如果恢复的是无辜方的名誉,就会出现一种荒唐的推论:夫妻一方的不忠行为反而贬损了另一方人格、名誉。如果法律是为有婚外性行为的一方进行考虑,要求他或她珍惜自己的名誉,恢复因其自己的越轨行为而对个人名誉造成的损害,那么,也得以当事人自愿为基础,否则规定这种责任方式也是吃力不讨好。
婚外性行为属于个人稳私问题,极少有人公开,更不会有人宣扬。如果要求“消除影响”,首先就不知道影响范围有多大,程度有多深。而且怎样消除也是个棘手问题,极易产生出“欲盖弥彰”的效果。
至于“精神损害赔偿”也有其弊端。我国实行的是夫妻共同财产所有制,婚后财产一律归双方共同所有,共同管理。责令违反“忠诚义务”的一方进行任何物质性的赔偿,实际上也就是无辜方自己的钱赔给自己。
也有人还主张,对于严重违反“忠诚义务”的,可以用“罚款、拘留、有期徒刑等刑事责任”①加以处理。须知刑法不是个别社会群体用以泄愤的工具。刑罚作为最严厉的制裁手段,作为社会关系的最后一道屏障,其调整范围有严格限制,不能随意扩展,否则会迫使社会关系的畸形发展。婚外性行为中也确有构成刑事犯罪的,即重婚罪,那是因为重婚对“一夫一妻”制形成了公然的挑战,严重破坏了社会整体利益,而不是因为该行为违了“忠诚义务”,损害了对方“配偶权”,不能以重婚为例,将所有的婚外性行为不加区别地纳入刑法调整范围。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婚外性行为这一点上,法律似乎显得无能为力,找不到适当的,行之有效的手段将其纳入自己的调控之下。这是正常的,我们必须承认,法律不是万能的,而婚外性行为似乎正是法律的“盲点”。
婚外性行为的大量出现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问题。它与人的情感世界联系之密切是其他任何法律问题所不能比拟的。仅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也许“忠诚义务”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一涉及到社会调查,单纯的法律有时就不得不屈从于无奈的现实。
婚外性行为产生的原因是多样的、复杂的,婚姻质量的偏低而离婚成本的偏高也是促成婚外性行为的原因之一。如果进一步对婚姻增加约束,对性伙伴的选择如此严格,人们选择婚姻也就十分沉重。人们为了逃避责任方可选择同居。婚姻不再是两性关系中唯一被社会认可的形式,那么婚姻制度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
对美好婚姻和家庭的向往,是人类从古至今的不懈追求。无可否认,婚外性行为有违于人类的这一理想,它给社会带来的众多的负面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但“家不是一个商业企业,该团体中的每一个成员无权通过法律程序弥补在家中失去的所有利益。”①婚外性行为其客体是个人之间产生的一种很难界定的感情,其主观方面是个人动机与欲望,这个复杂的内心问题应该、也只能通过道德管辖,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言,“法律不曾亦不能涉及道德的所有领域,若将一切道德的责任,尽行化为法律的责任,那便等于毁灭道德。所幸的是,这是不可能的事。没有任何法典,能够直觉到人间这如许的变化不定的情状,而这些情状正是决定道德责任的权威-他们要求立法,以禁止奸淫和未婚男女的同居。他们不知道,有种种行为,他们极有视为道德上罪恶的理由,却不一定是政治立法相当的对象。”②《婚姻法》可以在总则部分用导向性的语言提倡“夫妻应当相互忠实”,而不能设立一个冷冰冰的“忠诚义务”,西方有一句谚语“把恺撒的东西还给恺撒,把上帝的东西还给上帝”。意为世俗领域由世俗政府管辖,精神领域的由教会管辖,我们同样可以说:“把道德的东西还给道德,把法律的东西还给法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曾华

 U633687664
U633687664
 U582679646
U582679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