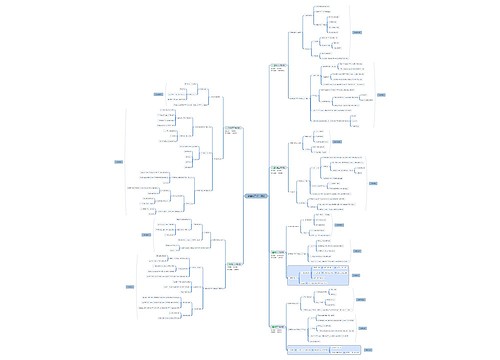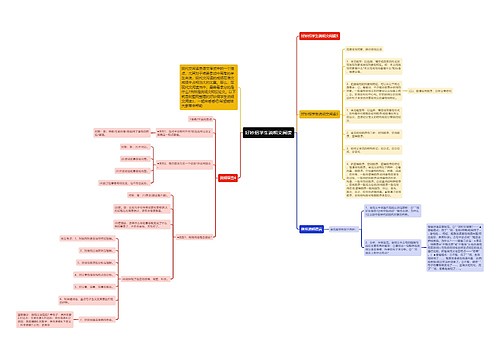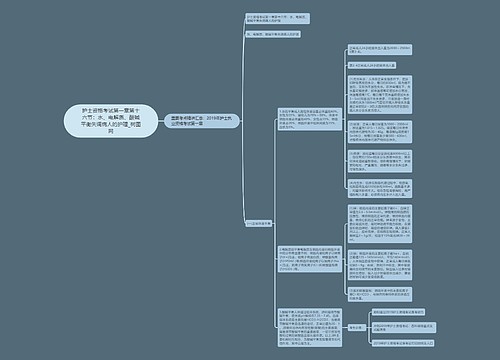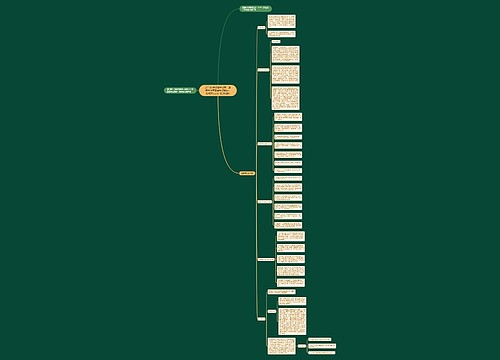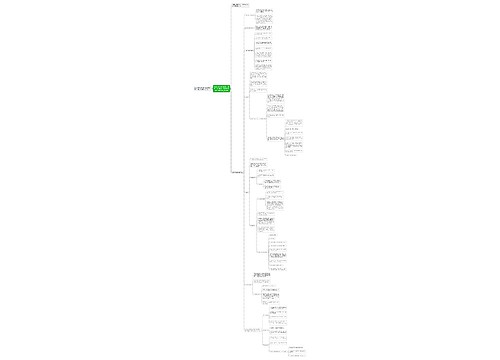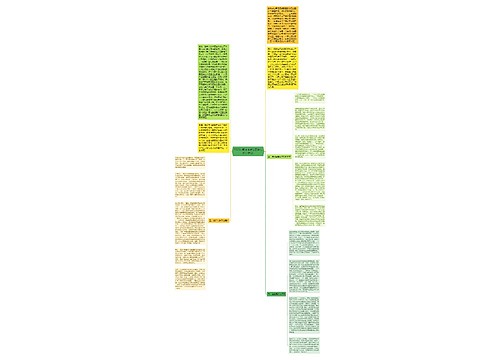观点之一,法官自由裁量权存在确有必要。法律具有规范、指引、评价、预测、教育的功能,法律的适用应当具有确定性,这种确定性就是体现在对相同或类似的行为应当有相同或类似的处理。但是,法律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存在着漏洞(特别是成文法国家)。主要表现为: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模糊性和滞后性。如精神损害赔偿相当长时间内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法权而不被借鉴。同样,对该案很多人提出精神损害赔偿应当明码标价、定额化,基于这种议论,最高司法机关在司法解释的草案中,也曾经提出了这样的意见。事实上,这是不合适的。因为社会中的人和事都是具体的、生动的,千变万化,情况各异,即使对同样的一件事,各人的感受也有所不同。精神损害要素的多元性、易变性、难测性等,决定了法律无法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规定得详尽无遗,加之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水平不一,要在全国制定统一的赔偿标准显然是不现实的。普遍的法律规范和个案处理之间总是存在一定的距离,这是自由裁量权存在的现实基础。丹宁勋爵将之形象地比喻为:“法官绝不可以改变法律织物的纺织材料,但是他可以也应该把皱折熨平。”
观点之二,法官自由裁量权有其内在缺陷。法官自由裁量权是一把双刃剑,其优势是自由性,其内在缺陷也在于自由性。在“宜粗不宜细、成熟一条制定一条”的立法思想指导下,我国已制定出的法律存在着规范不详、弹性极大、可操作性差的问题,导致法官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如本案中的1万元和11万元,正是其具体表现之一,极易造成司法之随意性进而膨胀为司法专横,直接损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乃至国家和社会公众的利益,最终破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破坏我国法制的统一,有损于司法机关的形象及权威,有悖于司法机关的性质和宗旨。这也是公众对司法进行指责的口实之一。波斯纳将法官自由裁量权比喻为“黑箱”;英国法学家戴西也认为自由裁量是一种专断的权力,与法治原则是不相容的。因为法治要求行为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对其局限性必须有充分认知。
观点之三,规制与约束,自由裁量权的必由之路。必须承认,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是法官行使司法权力的一种常态,法律适用中同时并存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可测性与不可测性等特点,决定着适用法律也必然与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并存。只要我们对法官自由裁量权涵义及内在缺陷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然后设计出一套完善合理的监控制度来有效控制它,就能使法官自由裁量权发挥最大效用,正如肖扬所言,“依法限制自由裁量的空间,实现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有机统一”,上级法院的法官根据当事人的请求运用自己的法律专业知识和司法经验对下级法院法官的司法判断行为进行监督,使不正当运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得到纠正。这种监督实际上是职业法官之间在共同的知识背景下所进行的一种专业性对话与交流。
但必须要申明,只要一审法院对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未超过合法、合理范围的,二审法院就应当尊重一审法院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如无新的事实依据,不得擅自改变其审判结果,而不是本案的结果。

 U633687664
U633687664
 U582121265
U582121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