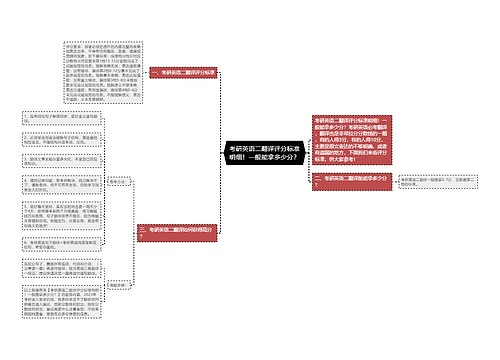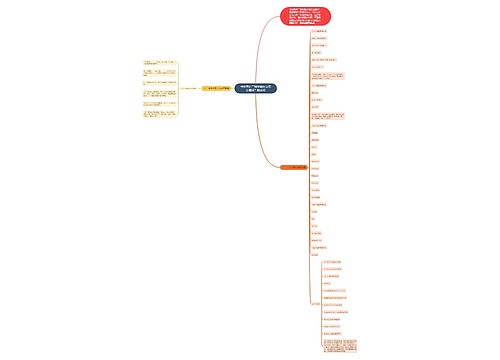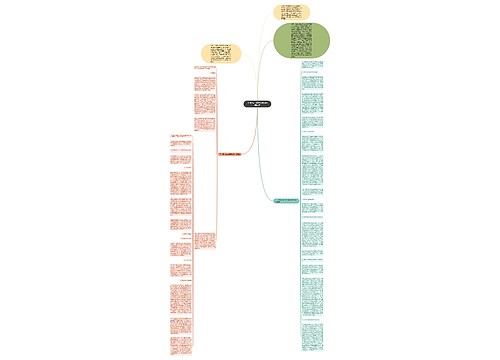美国证据法中的证明力规则(下篇)思维导图
人生岁月几度寒
2023-04-04

美国证据法中的证明力规则(下篇)
论述分析
四、反思证明力规则尽管美国的证据法实践中存在诸多证明力规则,但上文的论述并不表明证明力规则是普通法裁判中的一个普遍现象。
树图思维导图提供《美国证据法中的证明力规则(下篇)》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美国证据法中的证明力规则(下篇)》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fccc064ef685c72c1caeabc8a91cd5ed
思维导图大纲
相关思维导图模版
美国证据法中的证明力规则(下篇)思维导图模板大纲
尽管美国的证据法实践中存在诸多证明力规则,但上文的论述并不表明证明力规则是普通法裁判中的一个普遍现象。相较行政事务,民事和刑事案件中适用证明力规则的案件数量相对较少。并且,上述证明力规则并没有获得理论层面的认同,而是被证据法学者视为个案或者例外,主流的证据法学界奉行的仍然是塞耶、威格摩尔等人的理论,沿袭的是《联邦证据规则》以可采性为核心建构证据法的思路。
在上述思想的阴影下,证据法学者很少关注证明力问题,学术专著中亦很少大篇幅论述证明力问题。甚至,英美主流的证据法学者对于证明力的基本问题都没有形成共识,但对于证明力规则已经形成基本的共识,在“到最近绝大多数法学家都认同证据评价几乎不受规制的观点”的影响下,即便承认司法实践中对证据评价可以进行有限度的控制,但普遍认同的是“不存在证明力规则”(no rules of weight)。
尽管上述思潮占据主流,然而,对于证明力问题一直存在诸多反思的声音。在反思证明力的观点中,既有从总体上反思《联邦证据规则》基础理论的声音,又有对证明力规则本身的反思,既有证据法史学角度的梳理,又有新兴证据科学背景下的反思。
(一)作为证据法基础的最佳证据原理?――证据法理论基础的反思
证据法学的一个永恒的话题是证据法是否有一个体系性的(organizing)基础理论。关于证据法的基础理论而产生的争论可谓仁智互见,尽管最佳证据原理在吉尔伯特的证据法中占据核心地位,但后来的证据法学者都试图重构证据法的理论基础。其中,塞耶、威格摩尔的控制陪审团(Jury Control)理论――不信任外行陪审员的能力以及内森(Charles Nesson)教授的裁判的可接受性原理即为其中的代表。特别是控制陪审团理论作为传统学说的代表为学界长期接受而成为正统的观点。
随着上述理论的提出,吉尔伯特的最佳证据原理早已风光不再,“虽然一些现代的观点仍然谈到‘最佳证据’的概念,好像它是今天一项普遍的支配性的法律原则,但更多人接受了现代教科书的作者提出的观点,即并不存在这样一项普遍原则。”如朗本教授所言,“以庭审中证人证言为核心的现代证据法在18世纪末以及19世纪取代了传统证据法,抛弃了将文书证据优先的最佳证据规则作为证据法体系性原则的努力。”尽管最佳证据原理已经被边缘化,但反思最佳证据原理、为最佳证据原理正名甚至以最佳证据原理重构证据法的观点一直存在,南希(Dale A. Nance)教授的系列论文即为其中的典型代表。
南希教授的“最佳证据原理”一文可谓其观点集大成者,该文开宗明义指出,其核心命题即证据法的原则是诉讼各方应当向法庭提交其能够获得的与涉诉争议事实问题有关的最佳证据(the best evidence reasonably available)。在该文中,南希教授认为既有的证据规则解释框架存在诸多弊端,而最佳证据原理作为解释机制较今天通用的原理更有说服力,并且认为其观点与近来历史学派声称的制定现代证据规则主要是控制律师而非陪审团是非常一致的,并对最佳证据原理的竞争性阐释原理――不信任外行陪审团(distrust of the lay jury)作出评价。
在南希教授看来,无论哪种诉讼概念更为恰当,无论哪种诉讼模式最有助于实现最终目标,发现真相是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的首要任务。在一个可以想象的无成本的世界,最佳证据就是所有相关证据。当然,在一个真实的世界,诉讼是在合理的时间、金钱以及其他资源限制的条件下探求终局性的实践性事业。诉讼当事人共同的责任是在费用、诉讼不便以及终局性要求的限制下提出最有证明力的证据。源于18世纪的格言反映了这一纯粹的思想:必须提交案件所容许的最佳证据。
南希教授的最佳证据原理与吉尔伯特当初的观点存在诸多差异,但不能否认的是,尽管当下的最佳证据原理强调运用合理手段获取证据,但其核心理念仍然是获取最有助于帮助事实的裁判者作出正确裁判的证据,这依然与证明力问题紧密相关。南希教授对相关性问题作出的创造性阐释即为突出的例证。尽管南希教授承认现代证据法的基石(corner stone)是相关性,但他认为,相关性问题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相关性,而是附条件的证明价值(conditional probative value),并认为这是最佳证据原理的一个例证,力图运用一以贯之的最佳证据原理重构《联邦证据规则》。恰如上文所述,证明价值(probative value)是与证明力(weight)难以界分清楚的概念。从中可以看出,运用最佳证据原理阐释证据法就无法绕开《联邦证据规则》回避的证明力问题。
当然,最佳证据原理提出后亦面临诸多挑战,如伊姆维克里德(Edward J. Imwinkelried)教授在全面分析控制陪审团原理以及最佳证据原理的基础上,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最差证据原理(theworst evidence principle)――防范证人伪证作为证据法的基础理论并据此分析证据规则以说明其有效性。
尽管对于最佳证据原理存在争议,但不容否认的是,南希教授对于最佳证据原理的重构影响很大,在短时间内就“被广泛引用”(often-cited)。通过上文对于最佳证据原理的介绍,可以看出,对于《联邦证据规则》理论基础的反思,使得证明力问题得以凸显,并侵蚀了传统的可采性规则的领地,南希教授甚至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最佳证据方法对排除规则的实践具有一种普遍的腐蚀作用。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在最佳证据原理(the best evidence principle)的重构下,相当一部分典型的可采性规则都可以解读为认识论的最佳证据规则(epistemic best evidence rules),这些规则允许和鼓励提出最有证明力、最实用的证据。可以看出,在最佳证据原理的框架下,相关性问题、可采性问题都转化为证明价值问题、证明力问题,甚至可采性规则都可以运用本质上为证明力规则的最佳证据规则进行解读。
(二)作为证据法改革方向的证明力规则?――证明力规则本身的反思
除了上述从宏观上反思证据法理论基础的声音外,新近亦有学者(巴赞)从证明力规则本身切入展开分析,在对证明力规则的历史作出全面梳理之后,结合司法实践中最新的判例对美国证据法中的证明力规则作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反思。
巴赞指出,现代证据法的一个核心假设为其规则仅为可采性规则,即,它们仅仅告诉法官某一特定证据是否提交事实认定者审查,但是它们不会告诉事实认定者如何评价已经被采纳的证据。然而,我们可以假设有一类规则体系能够通过指导事实认定者并帮助其衡量证据的证明力,例如,法律可以规定一类证据如传闻证据的证明力较低。事实上,这些规则――证明力规则――是根植于罗马法的古老观点。但是,它们被证据法学者长期忽视,即便被提及也是被视为过时的、与陪审团审判格格不入。
巴赞认为对证明力规则怀有这样一种敌意是不公正的,并且应当认真对待证明力规则并将其视为证据改革的一个可能的方向。考虑到陪审团审判现在日益稀少,并且,即便在陪审团审判中,其自由裁量权已经通过多种方式予以限制,对于证明力规则的正统观点看起来已经不合时宜。进而言之,有充分理由表明证明力规则有助于科学的事实认定。证明力规则在过去法庭审判中的运用、在当今行政审判中的运用以及认知哲学的最新研究都表明其能够使事实认定更公正、更有效率,并且最重要的是更准确。证明力规则具有的这些优点使得联邦最高法院在Allentown Mack一案中对于证明力规则的谴责难以自圆其说。
就笔者目前的阅读范围来看,该文无疑是对于证明力规则论述最为细致、最为深入的一篇文章。仔细研读“证明力规则”一文,可以发现,巴赞的论述详尽、全面,认真梳理了证明力规则的早期历史以及学术观点,对威格摩尔等人的学术观点提出质疑,令人信服。细致梳理、总结了当下美国证据法实践中存在的证明力规则,并结合新近的判例考察联邦最高法院对待证明力规则的态度,全面展示了异于制定法的证明力规则的真实面相。此外,为了论证其观点的有效性,巴赞详细论证了证明力规则对于事实认定的潜在效用,从概率论的角度论证了证明力规则有助于准确认定事实;从风险分配的角度论证了证明力规则有助于公正地认定事实;从机构裁决的角度论证了证明力规则有助于高效地认定事实。价值层面的深刻阐释则充分展示了证明力规则潜在的优越性。
需要指出的是,巴赞的论述仅仅是一种要求重新审视证明力规则的观点的表达,并且,其中的论证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巴赞将证明力问题诉诸公正、效率、准确的价值论,而价值问题则是一个难以言说的、仁智互见的问题,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导致其中的论述难免掺杂过多的主观倾向。
当然,巴赞谦虚地坦陈其研究更多的是在提出问题,并特别指出,“法律对待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大不相同的认知应该开启这一研究而非终结它。”在笔者看来,巴赞的研究确实将对于证明力规则的研究推向了深入,相较于主流观点,主张证明力规则无异于标新立异,但正是对于主流观点的直接挑战才更使人反思,其促使我们反思反对证明力规则的主流观点在当下是否切合时宜,促使我们深思证明力规则自身存在的价值,更促使我们思考证明力规则能否成为巴赞所言的将来证据改革的一个可能的方向。
(三)证明力的复兴?――证据科学背景下的反思
审视美国的证据法实践,可以发现,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新的事实认定方式逐渐渗透进司法领域,法庭的事实认定越来越依赖于具有专门知识的专家,“越来越多对诉讼程序非常重要的事实现在只能通过高科技手段查明。随着人类感官察觉的事实与用来发掘感官所不能及的世界的辅助工具所揭示的真相之间鸿沟的扩大,人类感官在事实认定中的重要性开始下降。”
由此,事实认定领域出现了事实认定科学化的问题,进而对自由心证形成了巨大冲击。在事实认定的科学化日益广泛、法庭越来越依赖于技术专家的背景下,自由心证面临重大变革。正如达玛斯卡指出的:“自由心证原则是现代大陆法系证据法的基石之一,在不远的将来需要对它作出重新的思考和定义。对此不要有什么误解。科学将持续地改变生活,事实认定的伟大变革摆在了所有司法制度面前,这些变革最终可能与中世纪末期出现的改革一样重要。”尽管,当下事实调查方法的科学化对自由心证总体影响不大,但“我们应当承认,将来的情况可能会有所变化: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更为可靠的仪器和方案很可能就会开发出来;而这些手段的应用,将会给事实裁判者的自由心证施加更大程度的干涉提供正当性”。尽管无法预见将来的具体变化,但不可否认的是,事实认定的科学化已经并将继续对自由心证产生影响,这一趋势同时意味着证据的证明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演化为科学问题进而限缩了法官在证明力问题上的自由裁量权。
同时,与事实认定的科学化结伴而行的是跨学科研究的持续发展以及证据科学的兴起,证据学研究发生的这一转向使得证明力问题进一步凸显。
传统的证据学关注的是教义性研究,即“主要对规则进行分析并系统化,从而促使这些规则进行再概念化(reconceptualizd)或者使之获得改进”。教义性研究的核心关注点为证据规则本身,尤其是可采性规则。自20世纪中叶证据学研究开始从关注证据规则的领域转向关注证明过程,从而产生“新证据学”。其实,这样一种转变,如同伦伯特(Richard Lempert)教授所言,证据学从关注规则的表达转向对于证明过程的关注,不过是对于威格摩尔伟大作品的重新发现。其后,其他学科纷纷进入证据法研究领域,形成了证据法跨学科研究的诸多分支。
随着证据法研究发生转向,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证据法学研究领域的深入应用,证据科学日渐兴起。相较于传统的教义性研究对于审判领域可采性问题的关注,证据科学更为关注相关性、可信性和推断(或者证明)力。证明力问题在证据科学背景下得以凸显,传统的可采性问题正在为证据的相关性、可信性和证明力所取代。并且,证据法实践似乎也在验证这样一种判断,即排除规则的例外在不断增加,排除规则适用的范围被大大限缩,可采性问题逐渐为相关性、证明力问题所取代。
当然,证据科学在当下只是出于起步阶段,仅以此断定证明力问题将因此而复兴尚为时过早,但证据科学对于证明力问题的关注无疑是证明力复兴的一个积极信号。
结语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在美国成文的证据法中,几乎没有证明力规则的生存空间,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的证据法实践中存在诸多证明力规则。尽管传统的证据法学研究对证明力规则持一种否定的态度,但新兴的证据科学却将证明力作为重要的关注点。前文的分析给我们展现了这样一幅图景:在美国,文本中的证据法与实践中的证据法形成了表达与实践的背离,传统的证据法学研究与新兴的证据科学呈现出传统与现代的对峙。文本与实践、传统与现代两相呼应,相映成趣。
上文的分析似乎给人这样一种感觉:实践中的证明力规则反映了证明力规则的真实面貌,新兴的证据科学则预示了将来证明力规则的发展趋势。并且,如果我们走得更远,甚至可以将证据排除规则视为证明力规则,正如达玛斯卡在评述排除规则时所指出的:“司法制度为了富有成效地贯彻排除规则的目的,而悄悄地向证明力规则投怀送抱――其中,例证之一是:对于不具可采性的证据,预定其证明力为零。显然,这种证据规则明显违背了以下原则:证据的证明价值不应由法律预先加以规定。”这一判断富有新意,然而,如若真将排除规则视为证明力规则显然有点牵强附会。
然而,证明力规则的当下以及未来图景并没有上文所描述的这样简单、乐观。在笔者看来,实践中的证明力规则仅仅是对于成文证据法的补充,新兴证据科学对于证明力的关注仅仅是一个信号。在当下的证据法中,无论是普通法还是制定法,可采性依然居于核心地位;而证据科学仅仅处于起步阶段,以此来判断证明力规则将来的发展趋势或许为时尚早,当然,事实认定科学化对于证明力带来的冲击却不容忽视。
尽管本文考察的是美国证据法中的证明力规则,并对相关学者的论述作了简要述评,描绘、还原了美国证据法实践中证明力规则的真实图景以及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的反思。然而,这一研究不仅仅在于展示美国证据法的另外一个侧面,其更深层次的目的在于反观当下中国的证据法实践以及证据法学者对待证明力规则的态度。
罗杰・帕克等人指出,当法律显失公正、严重混乱或者极速变迁的时候,教义性研究便会兴起。[36]如果这一论断成立的话,我们的证据法研究将长期处于教义性研究的阶段,传统的可采性问题、证据能力问题将长期成为证据法研究的重点。当下的证据法学研究验证了这样一种判断。然而,当下中国的证据法以及证据法实践是以证明力为导向、为核心的证据法,由此,如何回应当下的实践以及如何引导实践就成为证据法学者面临的问题。尽管本文的研究无法给出上述问题的答案,但本文所描述的证明力规则的发展演进、当下图景以及未来预测告诉我们应当对其秉持一种历史的眼光、开放的心态、前瞻的思维。惟有此,我们才能明晰怎样面对当下、如何回应未来,进而达致理论与实践的融合。
查看更多
销售经理半年规划思维导图
 U582121265
U582121265树图思维导图提供《销售经理半年规划》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销售经理半年规划》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e614d6bcf03e9318109240a18697c5d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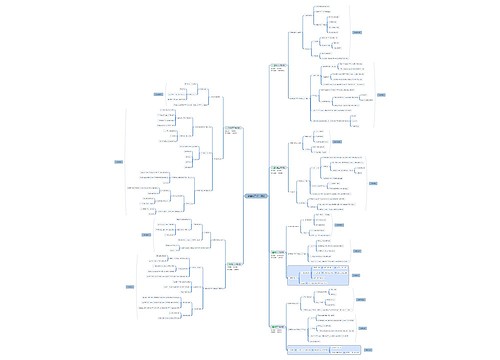
数智技术在工程设备管理中的应用思维导图
 U182637395
U182637395树图思维导图提供《数智技术在工程设备管理中的应用》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数智技术在工程设备管理中的应用》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f9a2de84ad9a9ceebc96385d71be9eb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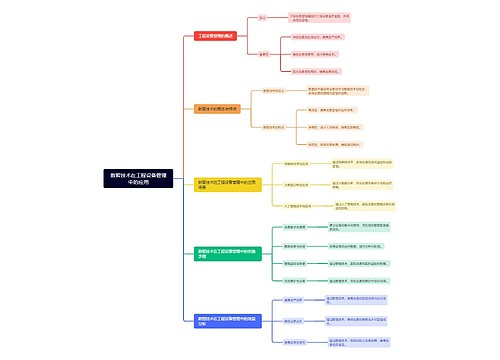
相似思维导图模版
首页
我的文件
我的团队
个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