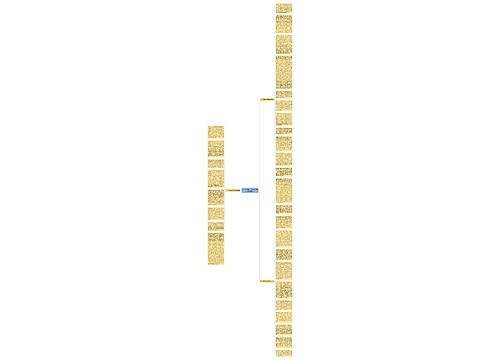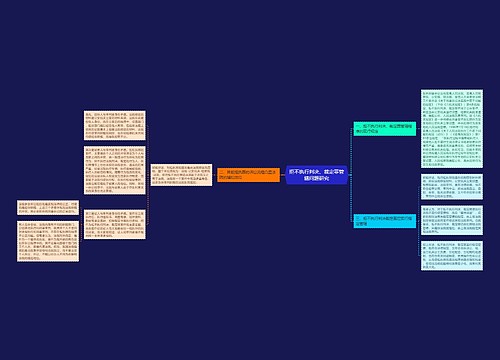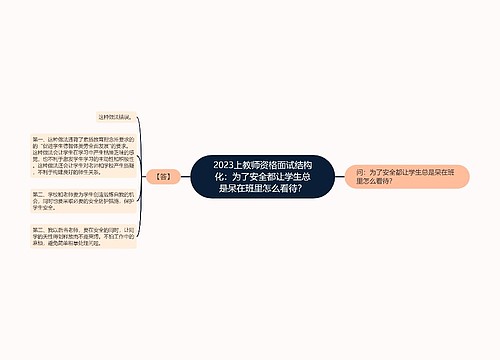论诉讼调解中的职权因素思维导图
同游生死
2023-04-04

论诉讼调解中的职权因素
论述分析
诉讼调解,又称法院调解,是指诉讼的双方当事人在审判组织的主持下,对彼此争议的法律关系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调解协议,然后由法院将调解协议的内容做成调解书以终结诉讼,了结法
树图思维导图提供《论诉讼调解中的职权因素》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论诉讼调解中的职权因素》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82065d6db437ea9f55abe95c8807a53d
思维导图大纲
相关思维导图模版
论诉讼调解中的职权因素思维导图模板大纲
诉讼调解,又称法院调解,是指诉讼的双方当事人在审判组织的主持下,对彼此争议的法律关系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调解协议,然后由法院将调解协议的内容做成调解书以终结诉讼,了结法律争议的民事诉讼制度。从形式上看,诉讼调解制度中并存着矛盾的两个方面:双方当事人的自愿和审判组织的作用,当事人的自愿或者合意因素反映了诉讼调解的契约属性,而审判组织的职权或者强制性因素与契约属性之间存在着矛盾关系。但是,这个矛盾的综合体缺少矛盾的任何一方,就不能保有其本质属性:如果没有契约属性的一面则诉讼调解与判决无异,如果没有审判组织的职权因素则诉讼调解与诉讼外的和解也无异。
两种因素协调时诉讼调解就能定纷止争、促进和谐,成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有力的一环。但是,审判组织的职权因素相对于当事人自愿因素过于强大,有时候会抑制、扭曲当事人的自愿,造成当事人“合意的贫困化”,也就是通常说的,“法官的职权主义色彩过重,当事人自愿没有得到充分尊重;调审合一,影响司法公正;调解程序不规范,缺少程序法约束;片面强调调解结案率;对法官的实体法和程序法约束都被弱化,调解活动缺乏监督”等问题。在诉讼调解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中,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就是如何削弱诉讼调解中的职权色彩,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恢复其契约属性。为了全面认识诉讼调解制度和我国“调判结合”的民事诉讼模式,真正发挥制度优越性,达到“案结事了”的目的,有必要正视职权因素的积极作用,本文拟从如下四个问题展开对职权因素的讨论:
1.诉讼调解中的职权因素是否可以被去除?如果是诉讼调解中的职权因素导致了其契约属性的异化,那么调解程序与审判程序是否可以“分离”或者“分立”以达到切割职权色彩的目的,这就是诉讼调解的改革中最常见的“调审分离”和“调审分立”的建议。“调审分立”是完全将调解和审判分开,取消诉讼调解制度。而“调审分离”则是在诉讼过程中、在法院里形式上保留调解程序,但是不能由有审判职权的审判组织来实施,而是在立案阶段实施或者由专门的调解法官、受委托的调解员来主持。
2.如何保证诉讼调解结果的公平和效率?改革者不遗余力地“疾呼”要让诉讼调解真正回归其契约属性,以当事人的合意为的基础,以当事人的合意为灵魂,以当事人的合意为诉讼调解正当性基础的决定性因素。但是,仅有合意能否得到公平效率的结果是有疑问的,在调解程序中如何克服当事人之间协商处理争议的信息障碍和情感障碍?普通契约中可能存在的欺诈、胁迫、隐藏的合意欠缺、认识错误、显失公平、交易基础丧失等问题在诉讼调解中如何处理?
3.“事清责明”原则对于诉讼调解是否必要?“事清责明”原则又称“调解真实原则”,来源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有观点认为这一原则限制了诉讼调解的效率,查明事实、分清责任需要大量诉讼成本,只有在判决中是必要的,在调解中也作此要求就是增加诉累,混淆了调解和判决的界限。但是,支持“事清责明”原则的观点认为,否定“事清责明”原则其实是混淆了诉讼调解和诉外和解的界限,没有正视诉讼调解中的诉讼法律关系。如果不需要“事清责明”原则会让诉讼调解协议像民间借贷中的借条一样方便快捷地确定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但是事实不清、责任不明的调解书是否还可以有既判力?
4.对诉讼调解的瑕疵应采取何种救济方式?瑕疵救济在当事人一方来说是损失补偿机制,而在审判组织一面则是一种事后监督机制。现行民事诉讼法对“调解违反自愿原则”和“调解书内容违法”用法院再审程序给予救济,但是由于要尊重调解书的既判力,其监督作用非常有限。如何在既判力和对职权因素形成有效监督之间寻求平衡是诉讼调解瑕疵救济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诉讼调解中的职权因素不能被去除
(一)“调解优先、调判结合”是人民司法的特色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要求,把调解作为处理案件的首要选择,自觉主动地运用调解方式处理矛盾纠纷,把调解贯穿于立案、审判和执行的各个环节,贯穿于一审、二审、执行、再审、申诉、信访的全过程,把调解主体从承办法官延伸到合议庭所有成员、庭领导和院领导,把调解、和解和协调案件范围从民事案件逐步扩展到行政案件、刑事自诉案件、轻微刑事案件、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国家赔偿案件和执行案件,建立覆盖全部审判执行领域的立体调解机制。
该意见的要求表明,审判实践已经拒绝了“调审分立”或者“调审分离”的设想。但是,“调审分离”的设想仍然支持者甚众,其理由在于:首先,“调审分离”可以隔离诉讼调解中的职权因素,可以根除职权强制与当事人自愿之间的矛盾。但是实际上使“诉讼调解”变成了“诉前调解”,使“法院调解”变成了“发生在法院的调解”;其次,“调审分离”有利于对调解程序的规范。有人认为调解要求的“流动性”和“随意性”和严格依法解决纠纷存在矛盾,会为审判权寻租和腐败创造了条件,所以要规范调解程序就要实现“调审分离”。还有观点将“调审分离”与“调解优先”联系在一起,认为“调判结合”的模式无法在操作层面和法理层面体现“调解优先”的原则,必须“调解在先、审判在后”然后才有调解程序的规范化。
“调审分离”代表了学术界和实务界希望裁判和调解在各自制度上纯化的一种理想。在一部分学者和司法人员中存在法制和调解是相悖离的认识,认为调解在虚化法律的作用,不能适应公民权利意识增长的需要。审判程序和调解程序应该各自分开,法官只需要“坐堂问案”,调解这一类群众工作应该交给其他机构来做。这种做法反映了将法律专业化和司法工作的人民性对立起来的观念,只重法律调控,不重“案结事了”、“促进和谐”的观念,不符合民事审判工作的根本目的,也不符合我国司法机关和司法权力的基本定位的。尽管当前我们要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形成司法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相结合的“大调解”工作格局,最高人民法院仍然要求法官要加强调解能力,加强做群众工作的能力,“马锡五审判方式”、“调解型审判”这些传统经验在我们的民事诉讼程序应该得到坚持和发展。
(二)职权因素是诉讼调解既判力的来源
我国的法院除了审判权和裁判的执行权之外没有其它的权力,诉讼调解中的职权因素不外乎审判权,从本质上和现实上说“诉讼调解是我国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法院审判权行使的重要方式”。所以,有观点直截了当地指出对诉讼调解程序的规范就是对其中“司法权力的控制”。但是,对于诉讼调解的应然认识仍然存在分歧,并且反映在对诉讼调解本质的认识中。对于诉讼调解的本质存在着三种认识:处分行为说或称私法行为说、审判行为说、审判行为与处分行为结合说。讨论诉讼调解的本质不是指望从一个“形而上”的定性出发,通过理论推导得出所有实践问题的答案,这种方法不免将我们导向类似“按图索骥”的错误。但是,与实践问题并存的“形而上”的理论架构必须保持自身的逻辑一致,能自圆其说。
认为诉讼调解中只有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的认识代表了一种理想:让诉讼调解完全契约化,摆脱使其扭曲的强制性因素,但是却让中国的诉讼调解的理论架构产生了矛盾。持处分行为说和混合行为说的逻辑结果都是否定和限制诉讼调解的既判力,这与其它国家诉讼调解的现实相适应,但是与我国诉讼调解的具体情况不一致,因为我国的诉讼调解依据民事诉讼法具有完全的既判力。我国的民事诉讼法能赋予诉讼调解如此特殊的效力,原因正是我国的诉讼调解制度包含“调判结合”的特色因素,具备了既判力的理论根据。既判力的来源认识有两种通说:制度性效力说和程序保障下的自我归责说,不论何种来源都离不开法院或者法官的职权,只有法院或者法官才具有解决争议的制度权威,才有保障正当程序在诉讼中得以执行的权力和职责,单纯的契约根本不能提供这些条件。契约既不具有国家审判权的制度性权威,又没有正当程序的保障,所以普通的契约并不具有既判力和执行力,只有通过法院的裁判转化为裁判确认的债务才具有这样的效果。从既判力的角度,可以认识到审判权对于诉讼调解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必要性。
(三)“调审分离”限制当事人的自愿选择
“调审结合”意味着在审判程序、审前程序以及执行程序中,法定程序与调解程序之间可以灵活转换,这不仅是法院的职权,同时也是当事人的合意可以选择的。“调审分离”表面上取消了调解程序中的职权因素,但是制度的纯化同时强化了诉讼程序的职权主义色彩,限制了当事人的处分权。民事诉讼的程序规则应该与实体规则一样可以由当事人双方合意选择适用,只有在涉及公益或者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实质不平等时,法律或者法院职权强制他们接受程序安排才是必要的。这也就是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落实23项司法为民具体措施的指导意见》中规定“民事诉讼过程中,调解可以在任何一个阶段进行,法院不得以调审分离拒绝当事人进行调解的正当请求”的理由所在。
二、职权因素保障诉讼调解的效率和公正
传统的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要求法官的职权因素越小越好,在思考诉讼调解的完善时,许多观点也带着当事人主义的理想。但是,这种诉讼模式实践到今天已经暴露其不足,纯粹的当事人主义在审判程序中会导致诉讼权利的滥用和诉讼程序的拖延,而在调解程序中则不能避免现实的契约中包含的问题和瑕疵同样发生在调解协议中。所以,诉讼调解程序需要审判权的介入才能实现效率和公正,只是这种介入应该建筑于“协同主义”的新理念之上,就是以诉讼的公平、公正和节约为目的审判权和诉权的协同合作。我国传统的“调审结合”的审判模式与新的“协商型司法”有很深的契合之处,这种审判模式下的法官职权可以发挥促进调解效率和公正的作用。
(一)职权因素为协商解决争议的前提
对利益的分配存在合同配置和权力配置两种方式,在经济社会中以当事人合意为基础的理想的合同配置被认为是最公平最有效率的,但是合同配置还不够,在当事人合意不能实现或没有效率的时候,还需要行政征收、司法判决等权力配置方式。比如发生侵权纠纷或违约纠纷时,一方未经他人同意,违背其利益直接占有他人的权利,除了少数情况下,由于有道德义务存在,占用权利的人会与受到损害的人会用一个补偿协议来恢复公平,大多数时候还是要靠权力的强制配置实现矫正正义。道德上的强制性因素是法院外的调解形式能够成功的主要原因,主持调解的人在争议当事人之间越具有道德权威,法院外的调解的成功率就会越高。然而,法律上的意思自治如同经济自由一样,并不一定能导向公平正义。实际上法院调解不可能离开法律和审判权作为保障,可以说它是一种法律和审判权“监护”下形成的合同。如果不是法官有“能调则调、当判则判”的权力,存在不利判决的威胁,争议双方当事人不可能坐到谈判桌前。
(二)诉讼调解的公平结果需要审判权的介入
现实中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和谈判地位的不平等,合同失灵和不公平的结果比比皆是,隐藏的不合意、欺诈、胁迫、错误、显失公平、乘人之危、交易基础丧失都是需要合同法的强制调整才能恢复公平。所以一旦发生争议,合同不会直接得到权力的支持获得强制执行力,而是要经过司法审查才具有执行力。调解协议的实质也是合同,而且不同于其他国家仅承认调解协议有限的既判力,我国法院主持下的调解协议具有与判决相同的既判力和执行力。如果在此过程中审判权“置身事外”,放弃必要的司法审查,则是对调解的当事人极大的不公平。
急于取消诉讼调解中强制性因素还会趋向另一种观点,就是法院的作用只能限于程序性的:(1)适时提供对话、协商的机会和起到沟通、中介的作用;(2)在当事人对话陷入困境时帮助恢复对话;(3)提出调解方案供当事人讨论;(4)当事人达成协议后予以笔录和认可。这远不能满足公平公正的调解协议的需要,主持调解的人至少还应该保证程序最基本的正当性,保证协议上签字的主体是有权作出决定的,正确理解对方的意思表示和协议条款、无欺诈,无来自对方的胁迫。法院在主持调解程序时,审判权因素可以对最后公正的调解结果发挥极大的作用,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为协议交易的标的定价,减少信息成本。调解协议也是一种交易,交易的标的物就是法律中争议的权利。如同我们逛商场时大多数交易尝试在第一次询问价格后就放弃了一样,为争议权利的绝大多数交易尝试都是因为交易双方对于标的物定价差异过大而失败。原告方努力证明受损权利价值非常高,而被告方努力证明受损权利价值非常低,双方定价差异非常大。定价成本从本质上来说还是一种信息成本,这种信息成本对于双方当事人来说无法克服,而由法官来承担则是可能的。如果法官在查明事实、适用法律的基础上为当事人做出核定,则会让当事人对权利重新定价,并更容易趋于一致。其他的调解人也可以为当事人做类似的核定,但是相对于对案件有审判职权的法官来说他们的核定欠缺权威性,未必能促使当事人调整自己的预期。
2。公平定价,弥补法律定价的缺陷。法律对于权利实际上都是
有定价的,甚至对于无法衡量价值的生命权。依法行使的审判权是权力配置资源的一种重要手段,波斯纳告诉我们要实现法律配置资源的高效率,必须用“法律模拟市场”,实际上法律对于权利的定价确实在努力接近其市场价值。但是“市场定价”有一个重大缺陷,就是无法模拟争议中包含的传统、道德和情感因素的价值。所以在“采光权”、“安宁权”、精神损害这一类“看不见的损害”引起的纠纷中判决结果一般很难让原告满意。而且模拟市场配置权利的结果有时候会趋向绝对的不公正。例如最近引起大家重视的在公路上“飙车”的现象就是证明,如果不考虑剥夺人身自由的刑事处罚,民事赔偿制度只会让富人占有公路更多的通行权。对此,德沃金指出法律模拟市场对于平等并不恰当,“因为它贬低了穷人的要求,穷人希望花更少的钱,他们没有更多的钱”。
法官以外的调解人在提出调解方案时,只能预测争议权利在法庭上的一般价值,或者说是“市场价值”。但是,对案件有审判权的法官则不同,只要有合理的理由,他提出的定价可以偏离“市场价值”,把争议权利中包含的弱者一方的道德、情感因素考虑进去。这些因素在审判程序中会被排斥,因为它们是不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
3。平衡双方的谈判地位,保障公平的剩余分配。争议双方在调解程序中是形式上的平等主体,但是双方实质的谈判地位并不平等,这一点大多数研究调解制度的人并没有注意。生活经验和博弈论都告诉我们,在讨价还价的连续博弈中更有耐心的一方会从合作产生的收益(合作剩余)中分得较大的部分。受害方在忍受损害而加害方在实际“占有”着权利,随着谈判的拖延谁损失大谁损失小,谁对谈判更有耐心非常明显。现实中往往就是加害方对调解持更为傲慢和无所谓的态度,并且受害方的经济状况越糟糕越会加重他的无耐心程度,会出现“以判压调、以拖促调”的现象。如果不重视实质谈判地位的平等,调解的结果也将趋向于不均衡。一般的调解人没有力量改变双方谈判地位,诉讼调解中的法官则不同,他可以发挥作用平衡双方的谈判地位,比如预测一个对加害方较为不利的判决结果,让加害方对于拖延谈判更无耐心,或者让一方的出价具有“最后通牒”的效力,对方不接受这个调解方案就终止双方合作的可能。
三、“事清责明”是诉讼调解的必备原则
“查明事实真相不是调解成功的充要条件,调解在本质上不像法庭审判一样是一个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过程”。要求在诉讼调解中取消“事清责明”原则的观点正确地指出了调解和判决是不同的解决争议的过程,并不是所有的调解结果都要做到“事清责明”。同时,“如果所有的调解协议只要一经达成就具有判决裁定相同的效力,当事人选择调解时就会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也不一定完全是一件好的事情。”诉讼外的调解不具备裁判相同的效力,没有做到“事清责明”也是妥当的,可是对于具有裁判相同既判力的诉讼调解则存在疑问。
(一)“事清责明”是既判力所必需的
既判力有其主观范围和客观范围,即一项生效法律裁判对哪些主体之间的哪些法律争议有最终的确定力,这些争议法律关系经过裁判处理后不能再提交法院。在诉讼中人们的生活关系与法律关系是分别处理的,法院通过审判解决争议的目的虽然不限于解决法律关系争议,还要做到“案结事了”,恢复社会关系的和谐稳定,但是也只能通过调整法律关系来达到。如果一项诉讼调解不能明确自己解决的是哪一个法律关系,就不明确法院对哪些法律关系做出了处理,发挥不了它定分止争的作用。假如原告和被告之间有长期连续的供货关系,但是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原告只能提供被告签收的收货单做证明,这样的法律争议非常常见。要求取消“事清责明”原则的调解人会劝说双方当事人各自让步,接受将债务关系一次解决的调解方案,至于具体发生了多少笔债务,哪些没有清偿,既然无法查明就不用查明了。即使双方当事人签署了调解协议,一旦原告又提出了新的收货单向法院起诉,谁都没法说清这笔债务是否在上次的调解协议中得到解决了,也就是说是否包括在上次调解书的既判力的客观范围中。诉讼调解的“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并不是指一定要查明客观真实,分清法律是非,而是至少要能清晰地界限出既判力的主客观范围。如果一项调解协议达不到“事清责明”的要求,则只能作为一般的契约对待,一旦有不公正的情况存在,或者有查明事实的机会出现时,当事人还可以提交法院裁判。
(二)“事清责明”原则是保护第三人利益必需的
双方当事人恶意以诉讼调解的形式损害第三人利益是恶意虚假诉讼的一种形式,而且比用判决形式更为简便有效,原因就在于诉讼调解的事实不用查明、是非不用分清就可以具有与判决相同的既判力。如果在诉讼调解中完全取消“事清责明”原则,那么利用诉讼调解逃废债务、损害债权人利益就变得很简便。例如债务人以协议方式低价转让财产、放弃到期债务损害债权人利益,债权人都可以行使撤销权,但是债务人如果以诉讼调解方式实施上述行为,债权人将无法对法院确认的调解书行使撤销权。诉讼调解不仅是解决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争议,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发生拘束力,它与判决一样还具有对世效力,为了让这种对世效力不被滥用,“事清责明”原则是重要的制约。
(三)“事清责明”原则是规范职权因素必需的
在诉讼调解中对于法官职权的程序法和实体法的制约都被弱化,对此已经存在共识。如果要继续坚持诉讼调解制度,就必须考虑如何规范法官或者审判组织在调解程序中的职权的问题。必须坚持“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才能保留实体法对于法官职权的最低约束,否则任何调解方案都可以通过“以判压调”等不正常手段迫使当事人接受,而且不用担心会受到任何正当性质疑。如此一来,诉讼调解书就会变成一纸欠条,不从知晓债务的原因,也不能知道是否有欺诈、胁迫、滥用职权的情况发生,甚至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可以对调解案件再审的两种法定原因也无从适用。
四、诉讼调解瑕疵的救济
(一)契约化的救济方式。有人提出了对调解协议进行事后实体审查的方案,也就是诉讼调解实体瑕疵的救济问题。这种观点首先质疑我国民事诉讼法上仅将违反自愿原则和违反法律作为诉讼调解的再审原因远远不够,应该仿效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中的做法,扩大调解协议无效和可撤销的法定原因。甚至还要再向前一步,将实体法上所有可能存在的合同瑕疵救济,包括法律对无效、得撤销和效力待定合同的规定都应该适用于调解协议。这种观点忽视了日本民事诉讼法对于民事调停中形成的协议只认可其有限的既判力的具体情况。表面上法律给调解协议可能存在的所有瑕疵都给与了救济,但是也会让调解协议变得与普通的合同毫无二致,完全不发挥不了“定分止争,案结事了”的效果,完全的既判力实际上无法维持。如果在有调解人的情况下,甚至是在法官的主持下还会发生类似普通合同中,当事人欠缺行为能力、意思表示错误,受欺诈的事实,则调解制度就毫无优势和必要性可言了。其实,契约化的救济方式最适合于没有既判力的诉讼外的调解协议。
(二)判决化的救济方式。对于瑕疵的调解书可以像判决一样提起上诉、申请法院重审、申请检察监督,对调解程序中的审判权形成全方位的监督,但是当事人合意的作用就被完全忽视。一方面当事人反悔变得非常容易,成本很低。另一方面法官为了免受纠错,在事实查明和法律适用方面必然非常谨慎,使调解结果与判决无异。如此一来诉讼调解在程序上的效率优势就荡然无存。
(三)独立的救济方式。民事诉讼法中对诉讼调解实行的就是一种不同于契约和判决的独立的救济方式,只是这种救济方式对于规范职权因素和救济当事人略显欠缺,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无法保证“事清责明”原则在诉讼调解中得到落实,也就无法对职权因素的滥用形成有力制约。为此,在可以申请再审的原因中除了原有的“违反自愿原则”和“调解书内容违法”,还应该增加违反调解真实原则为必要的再审事由。只是审查的标准应该与审查判决的“事实查明”和“法律适用”标准有所区别,在事实方面调解书只要明确调整的是当事人间的哪些法律关系,也就是明确既判力的范围。调解书的责任分配不能根本违反法律对这些法律关系强制规定,但是可以有偏离。
查看更多
数智技术在工程设备管理中的应用思维导图
 U182637395
U182637395树图思维导图提供《数智技术在工程设备管理中的应用》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数智技术在工程设备管理中的应用》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f9a2de84ad9a9ceebc96385d71be9eb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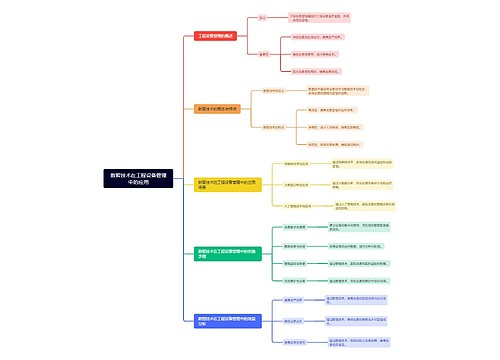
title: 2024-11-8未命名文件 tags: 影像诊断与手术后符合率统计与分析报告鱼骨图思维导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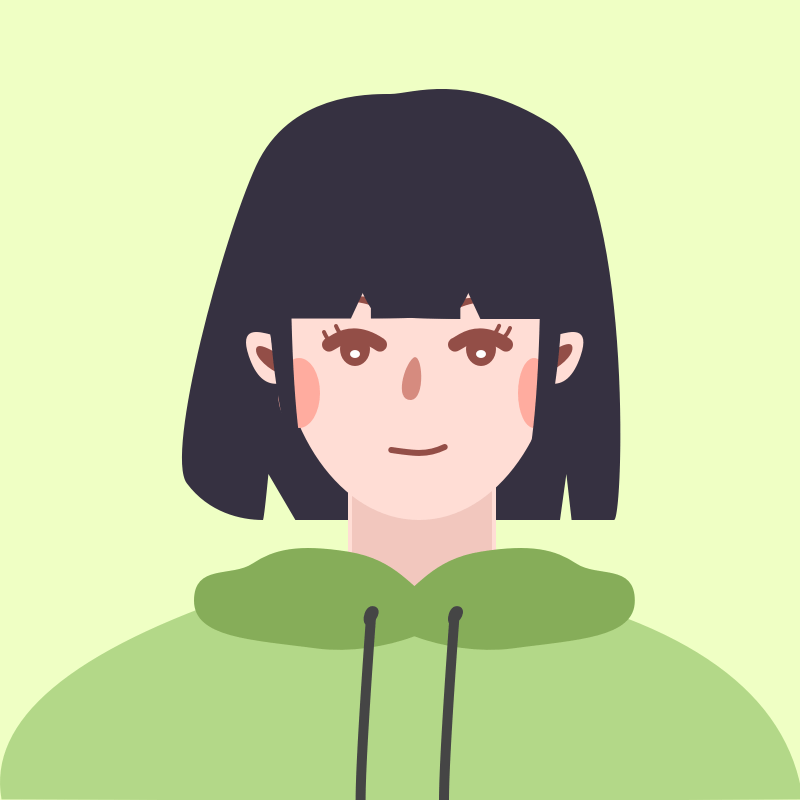 U880271396
U880271396树图思维导图提供《title: 2024-11-8未命名文件 tags: 影像诊断与手术后符合率统计与分析报告鱼骨图》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title: 2024-11-8未命名文件 tags: 影像诊断与手术后符合率统计与分析报告鱼骨图》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f19c198bf7435acf7735ee5051a89d7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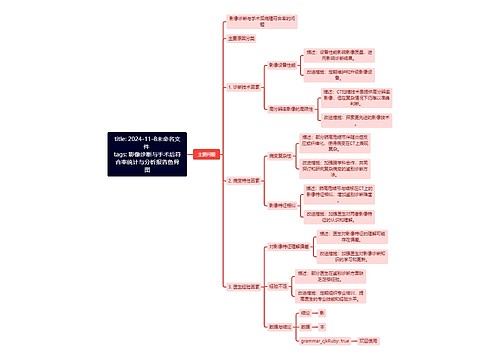
相似思维导图模版
首页
我的文件
我的团队
个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