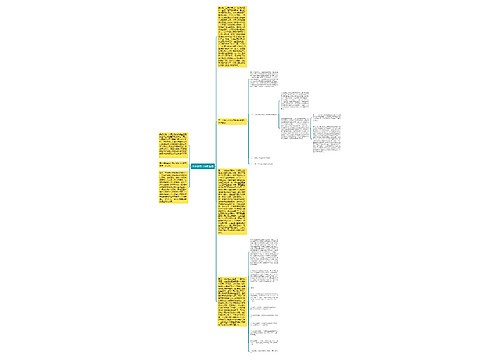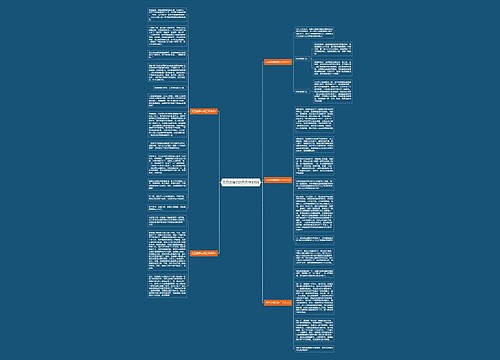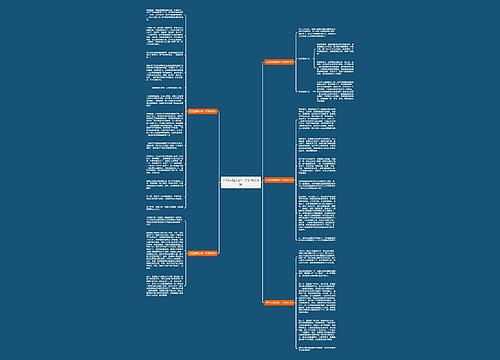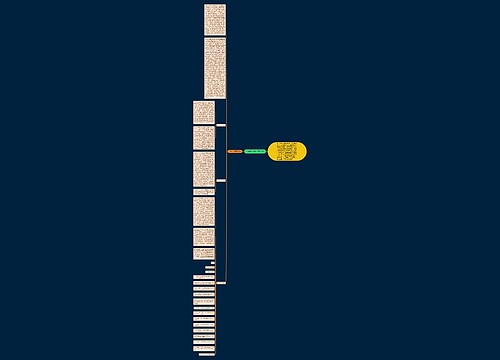律师和法官同为法律职业者,英文中“lawyer”指熟知法律的人,既包括律师,也包括法官,他们都是法律职业者。在日本,将辩护士(律师)联合会,与最高法院、法务省同称为“三法曹”。而律师常有“在野法曹”之称,并与作为“在位法曹”的法官相对应。律师与法官的职能都负有正确执行法律,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职责。他们都是为建造法制大厦添砖加瓦的人,其共同目标完全是一致的。
法官的司法活动并不是孤立的,而必须要取得律师配合。在现代社会,尽管律师不是司法者,但司法制度与律师制度关系十分密切,司法的公正不可离开律师的活动。因为诉讼活动是颇为复杂的,要通过诉讼维护社会正义,首先必须要消除人们对法院的感情上的隔阂,使人们不惧怕诉讼、不厌恶诉讼,这就要通过律师的活动使当事人与法院之间进行制度上的沟通,使当事人不觉诉讼繁琐、陌生或可怕,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几千年来儒家文化的“息讼”“无讼”思想影响深重的国家,消除民众对诉讼的恐惧心理是十分重要。正如本世纪初中国在开始酝酿律师制度时,一位政府官员在其所编的《律师法草案》中所阐释的。
律师对法院的司法活动配合表现在,律师制度的存在是保障司法公正的重要手段。现代司法仅要求实体的公正,而且要求程序的公正。而程序的公正乃是司法正义的固有内容,并具有独特的价值。律师制度在配合司法作成裁判、实现司法公正方面的作用表现在两方面:
(一)律师在实现程序公正方面的作用。从程序上公正来看,裁判的正确只有通过公正的程序才得以保障现代程序法所贯彻的诉讼地位平等,对诉讼权利的尊重,处分自由、充分对话、诉讼权利的充分救济、诉讼中人权的保护和诉讼参与等,都要通过律师的中介活动传递到当事人,或需要律师的参与。公正的程序是有助于发现案件的裁判结果是正确的。这是不能缺乏律师制度的。我国几千年来一直没有律师制度,因此程序制度极不发达且不合理。尤其是在刑事案审判中,因历代封建专统治者提倡和容忍使用酷刑来榨取口供,以至经常发生屈打成招、含冤致死、乱攀乱供现象。诉讼完全采用纠问式方式。这也极易导致裁判官的恣意妄为。尽管历代统治者希望通过制定完备的成文法,或者以例补法及通过建立惩治贪官及不负责任等措施来实现裁判公正,但因为没有公正的诉讼程序制度,因此许多学者认为此种裁判结果很难保证公正性,而造成这一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律师制度的结果。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开始建立和完善现代化的诉讼程序制度,尤其是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修改,审判方式的改革,都在为建立公正诉讼程序迈出了坚实的步伐。然而各种程序,如庭审方式的对抗制、强调诉讼当事人的平等、当庭质证、注重辩论,切实保障当事人的诉权,审判公开等都离不开律师的参入,换言之,在设计这些制度,就必须要考虑到律师的作用,如果律师不能参与诉讼活动或者不能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很难设想这些程序的适用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即使能够适用,它也会与立法者的初衷大相经庭。尤其是在审判方式改革中需要引入对抗制,而采用对抗制的前提是具有一套完备的律师制度和高素质的律师队伍,律师能够在诉讼中发挥重要重要。如果没有律师参与诉讼,则在我国现阶段当事人的水平仍然十分底下的情况下,根本不能实现诉讼的程序公正,也不可能实现对抗制……所以,我认为现代诉讼程序制度是与律师制度绝对不可以分开的。
美国学者布鲁兹尔(Brazil)在讨论律师在诉讼中的作用时,提出律师在诉讼中常常可能具有五个目的(1)将官司打赢;(2)赚钱;(3)避免因过错而被起诉;(4)获得声誉及同仁的称赞;(5)发展自己。具有这些目的很难说是自私的,而是一种制度所固有的。这些目的存在将促进和刺激律师在代理为当事人进行诉讼的过程中,会基于客户利益的最大化(the client‘s best interests)而努力收集对客户最有利的证据(当然也可能会收集到与真实不符的证据)从而促进一种真实的发现[3].我认为这一观点具有一定的道理,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当事人,由当事人负责举证,他们会通过其律师,最大限度地收集、提供有利于自己的有关案件事实的证据。可以最充分地揭示、发现证据的潜在证明力和价值。当然律师也可能会收集一些与案件的真实性不符的证据,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我们要看到,由律师收集的证据,必然增加了证据的数量,这是法官所做不到的。法官收集提供证据的动力绝对不会超过当事人。即使证据可能与事实不符,但通过双方的质证、辩论,能够逐渐暴露证据的真伪及价值。更何况证据最后的认定权在法官,法官面对着认定具有相当数量和质量的证据,总比自己亲自收集要轻松的多也公正的多。最后,即使法官认定的证据不利于一方,那么该受不利认定的一方也可能负有责任,因为他并没有通过其律师收集和提供足够对其最有利的证据而说服法官。
原有的审判方式和程序之所以适用很长时间难以更正,不仅受到一些旧的观点的束缚,很大程度上乃是因为担心当事人能力不足,知识欠缺所造成的,这乃是因为缺乏律师制度的缘故。我国近几年来推行审判方式改革,实践证明效果显著,在刑事诉讼方面改革的经验已部分被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所采纳,使我国程序制度向现代化、公正性方面迈出了一大步,而审判方式改革之所以能够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因为我国已经建立了一支数目可观的、有一定质量的律师队伍,并且已逐渐建立了律师制度。如果没有律师的作用,庭审方式的改革和程序不完善是根本不能实现的。
我们再讨论法官在裁量中以法律为准绳的概念,以法律为
沈家本先生在清末修律时,建议实行律师制度,其中一个理由便是律师可以弥补司法官知识的不足,此处所说的知识主要是指法律方面的知识。当今世界各国,律师帮助法官适用法律及在弥补法官知识不足方面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例如在美国,尽管法官大多是从具有较高的法律素质和实践经验的律师中挑选的,但律师仍然为法官适用普通法和制定法提供了重要参考因为在一个特定的案件中,如果要适用普通法,则判例如汪洋大海,应该选择哪一个案例?除先例外,是否还要适用制订法,制定法是联邦的法律还是州法,这些都是一件十分复杂的工作,而律师从有利于当事人的角度出发,而提出适用法律的建议,对法官而言,无疑是重要的参考。
当然,我们说律师的建议可以作为参考,并不是律师的意见都必须要被法官所采纳。法官是裁判者,是否采纳律师的意见应由法官决定,律师可以在法庭上说服法官采纳其意见,但不得对法官施加任何不正当影响。
律师在调解过程中,也具有重要的作用。一般来说,律师总希望法官在调解中接受其观点,并会努力说服法官接受其观点,但同时,律师也可以帮助法官从事调节活动。因为尽管是民事案件中的一方当事人的代理人,但他与当事人并不完全同一,律师自身是法律工作者,应以追求法律和正义的实现为目标。因此在一个案件,其代理的一方是否在法律上有充足的理由其证据的证明力如何,据此对判决的裁判结果的合理预见,都应当有所了解,如果律师认为自己代理的一方理由并不十分充足,而当事人因不懂法律和其他原因而拒绝接受调解或者提出不合理的请求,律师可以根据法官的要求而主动做其当事人的工作,耐心解释法律,说服当事人不得无理缠讼,或自愿接受公正的调解。
律师还应当看到,律师代理专利中说,商标注册从事谈判和签约等活动,可以使当事人准确地了解法律用语及相关知识,尤其是能够帮助当事人准确地签订合同,预防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种纷争,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和浪费,这对于法律秩序的形成十分有利,而不必要的诉讼的减少,也减轻和缓解了法官的负担。
保障程序的公正,必须要充分发挥律师在监督法官依据程序法办案中的作用。从狭义上理解的监督,是指由法律明确规定的监督机构(如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检查院等)对法院的监督,这些机构享有法定的监督权,其监督行为乃是合法行使权力的表现。律师本身并不是监督机构,法律也没有明确规定律师有权监督法院的裁判行为,但我们认为,监督还有另一层含义,即从广义上来理解,任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管是行政工作人员还是司法工作人员都应当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律师作为法律工作者,熟知法律,对法官的执法活动理应监督,这不仅是由社会主义民主决定的,而且是由律师具有比一般民众所不具有的监督执法活动的能力,以及作为法律工作者所应有的监督执法活动的职责所决定的。
总之,律师制度是实现裁判公正、司法正义的有利手段,他们和法官一样都担负着保障法律的正确实施,保护公民和法律的合法权益的重要职责,其与法院审判行为的宗旨和目的是一样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律师作为法律工作者担负着重要的职责。
在法治社会,律师的作用不仅仅是局限在诉讼活动中,相反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到律师的身影。只要法律能够作用到的角落,都必然会有律师的作用的舞台。律师因其熟知法律,具有娴熟的法律技巧,因此也成为依法治国的重要人才。以美国为例,迄今为止,美国历届总统大多数出身律师,而国会议员中有60%以上出身律师。至于行政管理者如部长、洲长等,许多人都是律师出身,而法官则根据普通法的传统均要从律师中选拔。律师在宣传法治、推动守法意识和法治观念的传播方面也具有重要作用。因为法律学毕竟是一门复杂的学问,一般公民并不熟悉法律,由律师提供法律帮助,不仅解决民众对法律服务的需求,而且也广泛地传播了法律知识和观念,也增强了全社会的守法意识。从而为法治社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正因为律师在法治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其理应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
[1] 转引自杜钢建、李轩:《中国律师的当代命运》改革出版社,第17页,1997年版。
[2] 参见陈旭:《试论中国特色的审判方式》载《法学》1996年第11期。
[3] Wayne D Brazil: The Adversary Character of Civil Discovery: A critique and proposal for change, Vanderbilt Law Review, Vol.31, 1978 P1311.
[4] 参见虞令维锋呈文:载“北洋公牍类纂续编”第248页。
修改版原载于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修改版),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十四章第二节。

 U633687664
U633687664
 U582679646
U582679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