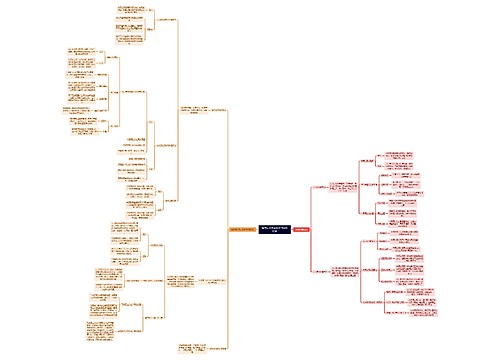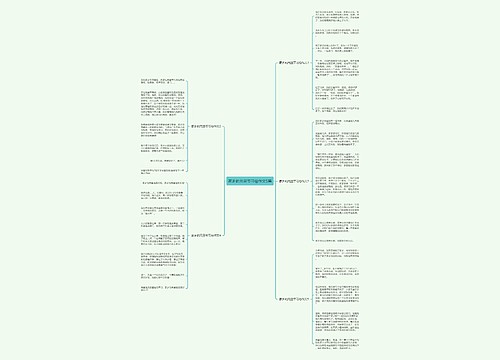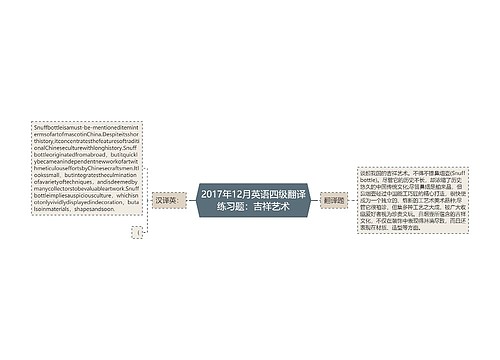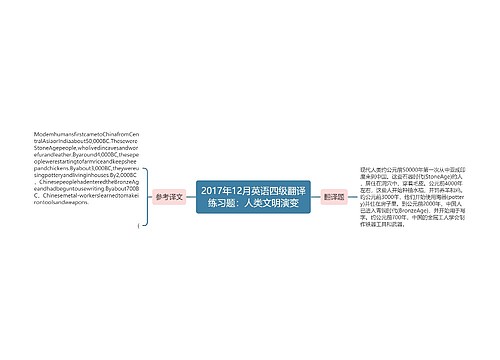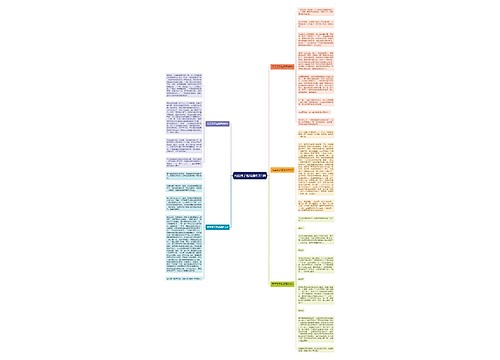与世界其他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家和民族一样,近代中国的宪政并非发自传统,而是被动的从西方“泊来”。说其“被动”是因为伴随着西方工业革命而来的殖民风潮席卷全球,全世界都被西方的殖民风潮拖入了而不是走进了“近代”的进程,中国也不例外。中英鸦片战争以来,效法西方成为当时中国“救亡图存”的唯一选择,在殖民炮火的征服声中,中国无暇从容地寻觅自强之路,以西方为师是当时中国人明智而痛苦的抉择。考察宪政在中国的历程,我们不能不对力倡宪政的思想先驱充满敬意,因为有了他们的勇气和热血,我们在充满屈辱的历史中找到了自信和希望,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也是因为他们的智慧,中国的“近代”在坎坷与曲折中毕竟也发展着,并最终走向自立、自强。然而,本文的撰写目的,并不是要重述先驱们有目共睹的功绩,而是要探求宪政在中国的发展为何如此艰辛,寻找宪政在中国发展中的误区。
考察宪政在西方的缘起,是正确理解宪政含义的前提。谁都不会否认,宪政在西方产生有着其特定的传统作为基础。近代宪政所要求的权力制衡制度与民主思想在古希腊思想家的论著中即可找到依据。如果我们将古希腊哲人柏拉图的《法律篇》、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与近代宪政理论的奠基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同置案上,翻阅比较,不难看出两者的继承关系。孟德斯鸠对政体类型的阐述,对共和政体与民主政治的制度设计无不镌刻着雅典、罗马城邦制的历史印记,宪政因有了传统的支持和历史的依据而合理并神圣。说到宪政,就不能不说“宪法”,因为宪法是宪政的文本和纲领。西方人是从传统认识或理解宪法的。按照一般的宪政理论,宪法是建立在社会契约基础上的,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规定国家最重要机构的职权和相互间的关系。从社会契约的角度阐释,国家的权力产生于公民的委托,而宪法就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契约。国家行使权力不能损害公民权利,相反而是应该以保障公民的利益为目的;权力制约的目的则在于防止权力的滥用。宪法的这种契约性质,使每一个生活于此的公民都会感到自己的切身利益系于宪法,感到在实际生活中宪法的不可或阙。更为重要,同时也是被我们所忽视的是,宪法在西方是一种民族精神的凝聚与展现,是传统文化与价值观的肯定与浓缩。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为全体公民长久以来形成的公认的价值观,“契约”才具有约束力,才不流于形式。
在中国一百多年的宪政史中,人们见到了甚至熟知了“权利”、“分权”、“人权”这些在以往典籍中查找不到的名词,学者呕心沥血地介绍了西方宪法的种类,宪政的模式,但宪政与历史传统的关系,宪法与民族价值观的关系却被忽视或回避了。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不乏外来文化冲击的先例,可以说中国文化的本身就是不同文化融合的产物。但是这个“融合”不是简单的“拿来”和仿效,而是在自身文化的平台上进行的再创造。外来文化在融合中“中国化”,中国文化在融合中不断更新自我。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的文化属于创造型,在接纳外来文化时要“心领神会”地体悟固有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相通之处,而不只是“形式”的拿来。外来文化融入中国文化的过程可以用“精琢细磨”来形容,一些适合民族、国家发展生存,可以丰富文化内涵的成分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体系中找到更恰当的表现形式,继续发展。而一些不适合国情民风的成分在甄别和批判中被改造。自东汉以来传入的佛教典型地展现了中国文化的这种融合力与创造性。自汉至唐,佛教在中国发展,也在中国受到批判和改造。有为了信仰而不辞艰辛赴西取经的中国僧人,也有理性分析并质疑佛教原理、社会作用的儒生。正是在这种从容的探讨和分析中,佛教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佛教因为中国化而焕然一新,更具发展的潜力;中国文化也因为融合了佛教更加生机勃勃。文化的融合力与创造性一向是中国人的自豪。中国近代宪政的不幸在于:宪政西来之际,正值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时,即使真诚赞美宪政的人也无暇从容地品味应与宪政与时俱来的历史文化韵味,更无法如汉唐祖先那样冷静地探求自身文化与这一泊来品之间的相通相异及其磨合途径。不平等、被动、甚至是被迫的接纳与仿效,不但破坏了中国文化的巨大融合力,而且也破坏了他的创造力。在前所未有地对传统文化失去自信的状况下,我们最初是“不得已”,其后是囿于惯性和成见而放弃了“融合”与“创造”的习惯,改为机械地“拿来”。
如果说学界的急切与不切实际的理想使宪政由西土“文化自然演进的结果”在中国变成“预期而设的用来解决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的一种工具”(12) 并由此而失去了其存在与发展的社会基础的话,那么,政治上的蓄意诱导则使宪政的处境更为尴尬——这是中国宪政的又一个误区。
自清末始,证明政权合法性成了宪法最重要的功能。因此,“根本大法”与风俗、民意风马牛不相及,反倒与政权形同孪生姊妹,其只是出自政权,或政权掌控中的“国会”。清末“大权统于朝廷”的“预备立宪”和北洋军阀政府接二连三的宪政闹剧,不仅使宪政成为政治集团之间较量的工具而失去了其本意,更严重的后果在于他的欺骗性使本来对宪政就陌生的民众产生了误解,甚至反感。民主也好,宪政也好,不仅无法阻止军阀混战,反而成了战火不熄的借口。在民不聊生的社会中,规定在宪法中的公民权利在民众的眼中只能是欺骗。这便是宪法在遭到破坏时,民众之所以冷漠的重要原因。
当然,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也不乏宪政的真诚拥戴者。但即使如此,在民族和国家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立宪者也只有将宪法作为一种工具。1912年《临时约法》的匆忙颁行,1913年《天坛宪草》的匆忙拟订,虽为不得已所为之,但这些匆忙之举,确实给宪政的形象带来了负面的影响,为此后军阀对宪政的利用留下了隐患。“欲速而不达”常常是社会变革失败的原因所在。自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公布,至1947年的《中华民国宪法》完成,不足四十年的时间中,随着政权的频繁更迭,中国竟出台了十部全国性宪法。中国宪法更替的速度之快是东邻日本的十余倍。
日本宪政的成功经验,一度成为中国主张宪政者的楷模。比如,只要说到宪政,梁启超则言必称日本。但以日本为师恰恰又是一个中国宪政的误区所在。对这一误区的分析,不能不涉及到文化的特征。
近代以来,中日同是效法西方,变法图强。但日本在“变”中收效颇丰,常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而中国却常常在“变”中进退维谷,变的“结果”常出意料,自认为种的是甘甜之“橘”,收获的却是苦涩的“枳”。中日甲午海战后,中国人不得不承认昔日的蕃属国日本的实力及其效法西方的成功,中国人的焦躁也因此而生。于是,便有人将效法日本作为变法图强的捷径,将学习的目光从欧美移至到东邻日本。一向被学界视为稳健持重的清廷重臣张之洞在其轰动朝野的《劝学篇》中大力提倡留学日本,并明确指出“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其理由是“路近省费可多遣”:“去华近易考察”:“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事半功倍,无过于此。”张之洞的这一番“事半功倍”的效率主张与中国传统的官僚、士大夫等对事物精益求精、探本溯源的从容风度已迥然有别。为弥补与传统的裂痕,张之洞补充道:“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变法,包括宪政在中国的引进确实有了一个变化,即从仿效欧美转向学习日本。这种转化的原因当然基于张之洞们所言的为使“中国速强”和“中日情势风俗相近”的思想。但遗憾的是这两点在当时人以至今人看来都顺理成章而又重要的理由,恰恰犯了中国文化的大忌。若从文化特征考究,中日间的差距决不逊色于中西。这就是,日本的传统长于“学习”,而中国传统则注重“创造”。
中国不同于日本,自秦之后的“大一统”文化一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中华文化是一个以中国人为主体“经营”积累了数千年的文化体系,虽然日本及东南亚一些地区和国家都被包含在这个体系中,或接受了这个文化,但是他们并非是“原创”者。由于是原创者,所以中国人格外珍惜“文化”,不可能像日本那样不在乎在仿效中失去自我。但是,中国文化并不封闭,相反,历史证明其具有巨大的融合力。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中,中国人强调的是“融会贯通”,是文化的扩容和更新。在学习和吸收中,中国人不仅不会放弃自身的文化,而是会通过种种缓和的途径使对方发生“汉化”,异质文化汉化的过程,便是中国文化更新的过程。这种学习的本身,与其说是学习,不如说是创造更为贴切。所以,中国人在学习中最忌讳形式的照搬和直接的套用。“探本溯源”、“厚积薄发”、“实事求是”是中国人的学习原则。这种学习的方法需要以传统为平台,需要从容甄别、精琢细磨,需要将异质文化中的优良成分演变为自身文化中的有机组成。因为中国属于“创造型”文化,所以在日本可以“速成”的西制,在中国却成效甚少。
我们无法简单地用“优”、“劣”来评价中日两国传统所赐的在“学习”方面所具有的不同特征。历史只是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同是仿效西方,同是实施宪政,日本可以从形式做起,可以直接搬用,中国则不能,如果这样做了,也不会取得成功。同样,中国在吸收外来文化时的自我更新及新途径的开辟,这样的学习境界日本也难以企及。我们更不能责怪近代许多有识之士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对传统的焦躁,因为历史没有给他们“从容”的条件,更没有给他们精琢细磨的机会。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现在是否有耐心寻出适应于自身文化的宪政之路,而不是在急于求成中再次迷失自我。在中国,任何成功的变革,无不是以批判开始,而在继承和融合中圆满完成的。
综上所述,对宪政含义的误解、政治的蓄意诱导、因急于求成而盲目地以日本为师是近代中国宪政的误区,这三大误区无不与传统的自信在近代失落相关。那么,可以让我们寻回自信的传统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我另文所要论述的“论礼治的改造”。

 U633687664
U633687664
 海沙
海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