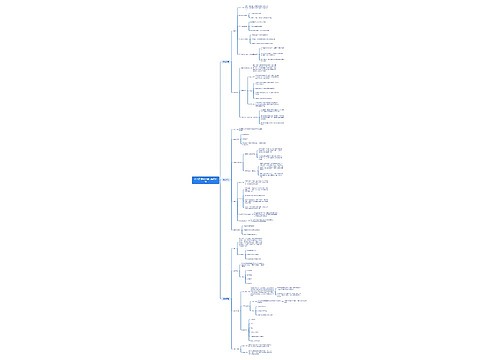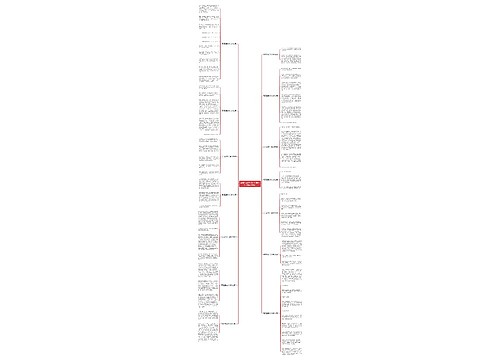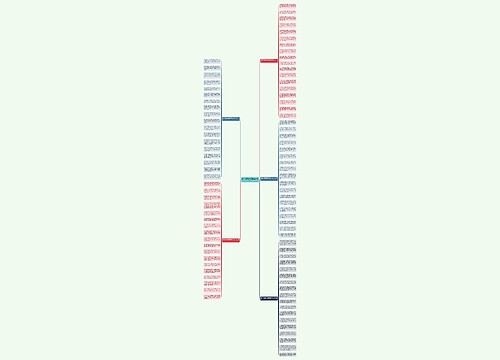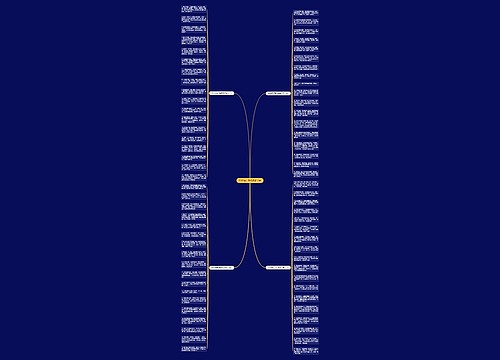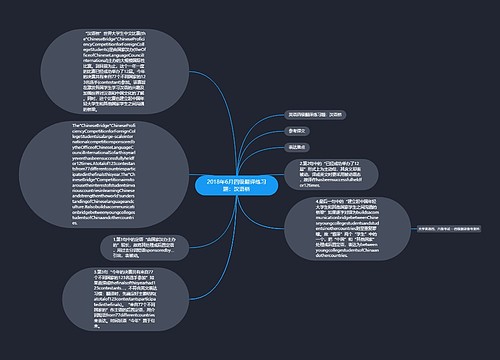道德与社会秩序之间是一种互动的过程,一方面道德有赖于体现了公平与正义的社会秩序的支撑;另一方面,道德又是公平与正义的社会秩序的前提,特别是当政府实现了道德化,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因为,政府不是脱离社会环境而孤立存在的,政府自身的秩序也同样离不开一个国家的整个政治系统内部要素的相应协变以及整个社会的支持和强化。如果政府在强调社会秩序和稳定的过程中,不是对社会秩序和稳定的性质进行考虑的话,仅仅依靠压制、剥夺公民基本自由权利来强化原有的社会秩序,就包含着引致民怨沸腾进而使原有政治系统陷于更为被动不利的境地的可能性,而没有社会基础的认可和支持的政治系统是不可能长久地维持社会秩序和稳定的。
当前,在我国存在着大量的不利于社会秩序安定的因素。近几年来,社会冲突表现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在范围上有着不断扩大的趋势。从理论上说,控制这些社会冲突从而获得社会秩序可以有这样几条途径:第一,把发生在冲突主体间的各种社会冲突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保证其不会扩散为大规模大范围的冲突;第二,通过全社会范围内道德意识的提高而使社会成员远离冲突;第三,建立健全个人和社会利益要求的表达机制,使每一项冲突具体化为个案和属于制度结构中的一些具有个性特征的冲突,使各类冲突之间不具有共性。因为,冲突如果能够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内有序地进行的话,那么冲突本身也就构成一种秩序的力量。当前我们控制社会冲突的方式主要是第一种,这是以政府掌握的公共权力的强制力来实现的,但这种选择不是长久性的最佳选择。当然,我们可以通过进一步的政治改革来做出第三种控制社会冲突方式的选择,即建立健全个人以及社会的利益要求表达机制,化解利益要求演化为社会冲突的可能性。这种方式是西方社会广泛使用的最成功的方式,也是目前一切理论设计所能提供的最为直接的控制社会冲突的途径。但是,最为根本的社会冲突控制方式是实现社会的道德整合,特别是通过政府的道德化来消解社会冲突。如果政府能够真正成为社会公平和正义实现的主体,就必然会带动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大幅度提升,就会实现对整个社会的道德整合,并获得稳定的社会秩序。
一切道德都是社会的,因为任何一项道德规范一经形成,就必然带有某种超越个体意志的必然性。只要道德规范是从社会客观存在中、从符合社会需要的社会关系中概括出来,而非道德家人为地杜撰出来的,那么,这种道德规范就具有客观的历史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在康德那里以“道德律”来界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家那里则以“天道”与“人道”统一来体现,而基本意蕴都在于强调道德具有社会整合的性质和功能。当然,个人如果能够在其行为中通过自觉地遵守道德规范,再到自为地合乎道德规范,他就可以超越道德规范,而成为“从心所欲”的有道德的自由主体。但是,这是一个目标设定,是一种理想状态。在现实中,我们所注重的是道德在社会秩序获得中的价值。
面对腐败,人们往往在法律的惩罚中获得快意。但是,法律的惩罚实际上是从“罪—赎”观念中发展出来的,是一种形式化的强行赎罪方式。它并不能从根本上制止腐败,并不能真正从源头上消除导致社会冲突的因素。所以,我们认为,在法律惩罚的基础上还应当有着道德的惩罚,即通过一种让人只有在自新中才能获得重新做人的机会的手段来实现对腐败的遏制。
法律对道德的影响是通过人的道德行为的中介而发生作用的。当一个人的不道德观念外化为某种具体行为,而这种行为又为法律所禁止时,法律就发挥了它的强制性道德规范作用。可见,法律与道德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及其互动的过程,正是社会秩序的保证。但是,法律与道德的互动作为社会整合机制以政府具体地执行这种整合为前提的,需要由政府来贯彻法律的原则、维护制度的框架和推动社会道德水平的广泛提升。在政府存在着严重的腐败问题,使法律原则得不到贯彻、制度框架扭曲变形、整个社会的道德滑坡的情况下,由政府来供给社会秩序是不可能的,相反,恰恰是政府成了破坏社会秩序的恶的力量。一般说来,在政治文明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政府的权威不是首先来自于暴力,而是首先来自于政府的公正、廉洁和高效。当政府中出现了严重腐败的时候,它已经不能提供社会公平和正义了,所以它在社会秩序供给方面除了暴力之外已经无可选择。而暴力不仅不能增强政府的权威,反而会削弱政府的权威。一旦政府失去了权威,那么社会秩序的普遍混乱就是一个必然结果。所以,政府的道德化是一条根本出路,政府只有彻底摆脱了腐败问题的困扰,才能够真正地贯彻法律的原则和维护制度的规范,才能带动整个社会的道德提升,充分实现社会秩序的道德整合。
[1]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141-142.
[2]霍贝尔。初民的法律——法的动态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369.
[3]杜尔凯姆:自杀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212.

 U582679646
U582679646
 U882673919
U882673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