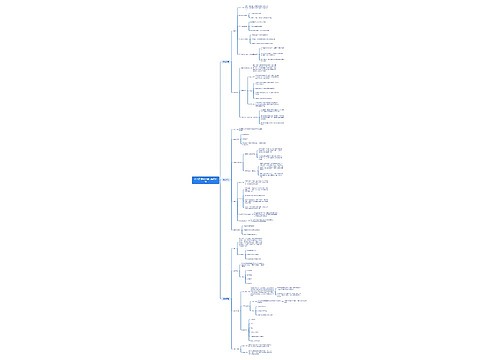[关 键 词]特权/自由权/普遍资籍/中国传统社会
自由的意义关涉自由的历史。所谓自由的历史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个人在有史可证的社会—历史中所享受的自由的情况及其变迁;其次,在这样的事实和变迁之中,人们对自由的理解及其演变;第三,与上述两项须臾不可分,人们对自由要求的变化。因此,所谓自由的历史,就既是作为规范的自由的历史,亦是自由的概念史和追求自由的历史。以上述三项内容组成的自由史表明,自由的演变乃是从特权发展为普遍资籍的过程。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自由的三层意义以及自由史的三项内容,为考察和分析一般的自由问题和一般的自由史提供了正当而必要的理论框架,因此它们并不局限于某个特定的地区和特定的时代。然而在现代社会尤其在西方社会中,作为基本价值观念的自由以及在现代政治哲学尤其西方政治哲学之中的自由概念,却是直接起源于近代西方社会,并且由此发扬光大而来。于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由与西方社会特有的自由,既在理论上又在实践上区别开来了。认识和承认此种区别,对于诠释自由、权利及其相互关系并因而构成一般的自由和权利的理论,乃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西方社会特有的自由,与自封建制度建立之后的近现代西方社会特定的政治、宗教、经济和历史等等观念、制度和活动,盘根错节地纠缠在一起。因此,在分析其他社会的自由情况(比如中国传统社会的自由情况)时,如果说一般意义的自由乃是分析的原则和基础,那么处于特定语境之中的西方自由就是一个必要的参照,但并非是厘定是非的标准。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第一章起首说道:“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注: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页。)接着,他就将自由与否与主人和奴隶的关系联系在一起。这样一来,就径直将自由与否归结于某种人为的社会规范,即政治制度和人身依附。卢梭的思想标志了自由观的一个根本转折:在此之前,自由被看作是做人之主人的那种状态,即一个人因主人地位而具有的各种特权;而卢梭所代表的革命性观点恰恰相反,就是每一个人都成为自己的主人而拥有自由,而这样一种自由状态才是真正的、为每一个人都拥有的自由。于是,自由在卢梭那里总是与平等联系在一起。
这些作为特权的自由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特征,即它们都是通过某种契约确定下来的,并且受到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法律保护。自由(特权)、契约和法律的这种共生关系,对西方社会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的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这些特权的另一个特征,就是特权总是与义务结合在一起。领主的一切特权虽然从形式上和历史上来自契约,但其实质条件就是为领地上的人民,提供从安全到生活的各种不同形式的保护和保障。如果我们将这一特征与中国的宗族制度作一对照,就会发现许多形式的和内容的相似性。在这里,特权(和某些基本保障)与不自由之间所体现出来的一定的交换关系,就其一般的形式而言在现代社会里依然存在,不过所依据的原则及其观念已经大为不同。
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视野里我们可以看到,在自由成为每个人的平等资籍之前,或者在达到如此状态的社会之外,自由总是体现为特权。在古希腊民主社会,享有自由的公民只是所有人口中的一部分,因此公民就是一个特权阶层。他们存在的基础和条件就是奴隶的存在;简而言之,奴隶状态是所有不自由状态之中的极端情况。自由与奴役的两极并存并互为构成社会,是西方社会—历史所特有的基本现象,它并不仅仅出现在民主政体的社会里,也出现在其他社会里。孟德斯鸠说:“在罗马的世界里,同在拉栖代孟一样,自由的人极端自由,当奴隶的人受到极端的奴役。”(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53、186页。) 在欧洲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某些地区人口的80%竟为不自由农和更低等级的人群。其中的农奴毫无财产权利,甚至他们的人身及其所有物,都是领主的财产(注:赵文洪:《私人财产权利体系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0—71页。)。20世纪民权运动之前的美国社会中,宪政民主与奴隶制及其遗产(即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共存的现实)又为孟德斯鸠的断言提供了明证:一群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自由的人,与另一群最不自由的人共存在一个社会之中。据此可以得出一个一般性的结论:倘若自由是以特权的形式存在的,那么它就必然要以另一部分人自由的缺乏作为条件和代价。
解答中国传统社会是否存在自由这一问题的困难,还来自于一个更为基础的窘境。这就是现代学术尚无法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性质作出合理的、因而令人信服的一般规定(或者几种可供选择的规定)(注:无论封建社会、集权社会、专制社会、绝对主义社会这些原本用以规定西方及其毗邻文明的概念,对于中国传统社会都是不合适的。)。我在这里回避了这个综合性的理论问题。这一问题的悬而未决,自然会影响到此处讨论的理论意义,不过有关自由问题的分析,也可以因此成为解决中国传统社会性质这一综合性问题的一种具体路数。这里先让我们回到作为特权的自由这一问题上来,并且按照上述自由的三层意义来探讨和分析它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情况。
就自由第一层意义而言,这里的关键在于参与构成(或确认、诠释)社会规范以及相应制度的资籍。由于中国传统政治的议事和决策方式的独特性,以及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和规范的稳定性,这样一种特权在通常的情况下是通过参与中央政府的议事而实现的(这里所谓的议事,当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从更为广阔的视角来看,自秦汉之后,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规范以及据此而形成或改进的基本结构的创制、解释和实施,主要掌握在士大夫这一阶层手中,因此这就是士大夫阶层的特权。倡议和实施变法和维新,当是士大夫此类特权的特例。此类作为特权的自由有其可靠的制度保障,这就是所谓文治政府、科举制度和庶民的平等(注:参见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五章。)。中国乡村自治中诸如确立和维持社会基层秩序这种权力,属于乡村的士绅和宗族的家长。士阶层的特殊地位和中国乡村的自治,为受过教育的精英分子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规范秩序、教化社会、左右舆论提供了相当广阔的自由空间。在先秦,各国最高议事的权力是属于贵族的特权。战国时期士阶层在各国政治领域的纵横捭阖,他们所享有的自由以及由此而发挥的作用和影响,乃是中国社会—历史之中仅见的现象。
上述作为特权的自由虽然为一定的阶层所具有,但是在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并无等级的差别。而四民原本就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这与欧洲封建社会贵族和自由民只占人口的少数恰成鲜明的对照。重要的一点是,这些作为自由的特权不是世袭的,而是通过科举产生的:“考试选官,本身是体现了公平竞争这一精神”(注: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15页。);而科举有一整套严格的制度,不是任何人可以随便改变的。
从拥有的人群的广泛性来说,中国传统社会里这些自由中的某几项应当算作多数人的资籍,而不是少数人的特权,比如迁徙自由、科举投考自由等。然而当我们联系到第三层意义上的自由理论,就会发现那些自由在前提和基础上包含了若干严重的先天弱点。这些弱点可以从如下三个层面来分析:
第一,作为自由主体的个人乃是相对的自为者,缺乏充分的独立性。中国传统社会的诸多自由的主要观念基础是仁爱和民本思想,但是仁爱是要区别对象的,而民本之民并非独立的个人,总是被视为处于特定伦理关系中的特定的身份,这样民本之民主要被当作一个整体来对待。比如,三纲五常之中的五常,为个人的自由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而三纲却规定了相当严格的臣属关系和人身依附。君、父、夫虽然同样受到伦理规范的束缚,但相对于臣、子、妇时,就具有优先和必要的权威,而此种权威适足以正当的理由单向地取消后者所享有的上述自由,直至生命。虽然人们必须注意到,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的自由事实上总是与某种人身依附现象和规则共存在一起的,并且只有在这样情况之下,自由才表现为一种特权,然而由于上述诸种原因的整体作用,对于个人来说,这种自由就是不稳定的,人身依附在这里就体现为因人而异的偶然性(注:瞿同祖分析了父母对子女的权威意志所具有的剥夺子女自由的决定性权力。此种权威意志大大加强了此类自由,包括人身自由的偶然性和脆弱性。参见《瞿同祖法学论著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于是我们看到,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规范和原则里面,资籍对个人来说并非是一种普遍而形式的东西,而是实质性的。因此在不同的境遇,相对于不同的他人,个人的资籍就发生相应的变化。
第二,与欧洲封建社会中作为特权的自由相对照,中国传统社会的自由并不以契约为前提和保证,即使形式上的契约前提也并不存在。其原因可以追溯到中国传统的社会历史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上。诸如社会的基本规范和原则(尤其它们的根据),被视为外在的而自然生成的,这就是所谓“天生烝民,有物有则”(《诗?烝民》,又见《孟子?告子》)。孟子与其万章关于尧禅让于舜的那段经典对话也可以引作佐证。万章问孟子:“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回答说:“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而是“天与之”,“民受之”。孟子接着用《尚书?泰誓》中的一段话作总结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君主与人民的关系虽然是由天决定的,但是天的意见与人民的意见是一致的。然而关键的一点是,尽管人民的意见就是天的意见,实际上他们的积极行为也仅限于“受之”,毫无与即使像尧舜这样的贤明君主立约的意思和要求。毫无疑义,立约与契约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乃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双方以平等身份实施的立约仅限于私人之间的民事关系。在统治关系方面,即使立约也是统治者单向的约定,如刘邦的约法三章,旨在颁布而非与父老豪杰的平等约定。在欧洲封建社会,从形式上来说,在各种社会—国家一类的实体即大大小小的采邑中,各种等级的贵族,包括从国王到骑士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与其采邑上的其他相关人等的关系,都是通过契约建立和确定下来的,因为此种契约是在双方同意并且就此而论乃平等的基础上签订的(尽管实际上立约在多数情况下并非处于平等的地位)。自由即使作为特权也就有了一种一般的意义,就正常情况而言,不会因其持有者与他人的特定关系而改变、乃至被取消。与此同时,基督教思想又为契约双方的平等地位提供了宗教观念上的根据和保证。这种契约中最为典型的,就是英国的《自由大宪章》,它可以说是欧洲该时代一份最大的自由契约。
在上文我已经指出,作为特权的自由在人类历史的绝大多数社会—国家一类的共同体中存在过。欧洲封建社会和中国传统社会中所存在的此类自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种。从这类自由内容的广泛性和自由的普遍性来看,中国传统社会的自由所达到的程度,远远高于欧洲封建社会所达到的水平,而且某些项目在西方乃是在民主革命之后才达到的。然而尽管如此,那些自由并不是普遍的资籍,除了前面所分析的其固有的弱点之外,始终有一部分人被排除在享有那些自由的资籍之外。在所有那些自由仅仅是作为特权因而赋予具有特定地位、身份或资格的个人的社会—国家里面,总是存在着将某一或某些特定的人群贬于卑微等级的根据和理由。消除这些根据和理由,从而使自由成为每个人都能够享有的同等的资籍,是从启蒙时代起首先在西方人头脑中酝酿、并随后确立起来的现代人类的主要理想和基本目标。然而如所周知,作为普遍资籍的自由是尚未付诸实现的。这一点不仅就整个世界范围来说是如此,而且在现代所有宪政民主或自由民主的社会国家内,情况也是一样,因此作为普遍资籍的自由依然是一个理想的目标。然而,这并不意味在人类的自由境况方面,现代宪政民主或自由民主社会—国家与诸如中国传统社会和欧洲封建社会之间没有什么差别。相反,需要强调的是,今天的宪政民主或自由民主社会—国家努力通过某种宪法或类似的规范,从原则上来规定其公民的自由,并且通过独立的司法系统来保证这些原则和自由的落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们能够与自由仅仅作为特权存在的社会—国家形成对照。
然而,作为普遍资籍的自由之主体是所有的个体这样一个基本的原则,显然与现在世界上的社会—国家这样一种确定个人资籍的制度是相矛盾的。鉴于现实可能的最为普遍的自由只能在一个社会—国家之中实现,于是,普遍资籍之普遍性,就收缩为特定政治共同体内的周延。然而,这直接导致了生活在这个特定社会—国家之中的个人并不能都享受到作为同等资籍的自由。因此,当自由被设计为一种普遍的资籍时,它就涉及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亦即世界秩序问题。仅就这一点我们也可以说,原先在社会—国家内属于特定人群的作为特权的自由,就演变为属于特定社会—国家的人民的同样作为特权的自由。不过问题并不仅限于此:作为普遍资籍的自由的普遍性,也会因其与政治、经济和法律等等的关系而受到质疑。
问题和困难也就接踵而来。作为普遍资籍的自由是每个人所享有的自由,这些兼容而可以共享的自由是如何确定的?就是说,哪些范围属于自由的畛域,而哪些又不属于自由的畛域,这是如何得到规定的?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自由不可能通过某种人为设计的宏观的秩序和计划而得到保证,相反这种计划、设计而成的宏观秩序将导致自由的丧失。然而,这个观点所面临的非难是:当自由不再是特权而成为普遍资籍时,那种兼容而可共享的自由无法通过个人之间的契约或谈判来得到合理而周全的规定,自由也无法因此而公平地遍及于每一个人,而必定要通过某种形式的共同协商来确定。于是,此种协商的形式及其可能性就成为问题的关键。卢梭认为,自由是人所共有的,并且是人性的首要法则。然而对他来说,困难并不在于这个主张,而在于证明这样的自由是能够得到所有人的同意而作为一种社会秩序确立起来的:“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注:卢梭:《社会契约论》,第23、51页。)卢梭通过社会契约、人民主权和公意等一系列理论构造,来保证为每个人所具有而又是大家共同同意的自由。最后,契约、公意和自由都落实到法律上面:人民服从法律就是在服从自己的意志,所以人民依然是自由的(注:卢梭:《社会契约论》,第23、51页。)。卢梭的思想受到许多批评,甚至遭到否定。然而,就如罗尔斯依然沿循卢梭的思路,为一种政治的正义原则获得普遍同意而设计原初状态这一事例所表明的那样,这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难题。这个难题表现为一个类似二律背反的困境:自由作为普遍的资籍需要普遍的同意,而一种规定所有人的平等、兼容而共享的自由的原则的普遍同意,无论以任何形式都是无法达到的。因此,就对所有人平等、兼容而共享的自由来说,始终就是由部分人决定的,或者由不同的人依不同的组合、在不同的时间和情况下决定的,所以作为普遍资籍的自由是由部分人确定的。作为普遍资籍的自由只能是由部分人来确定的,于是,这种作为普遍资籍的自由,既会因决定者的不同导致因人而异的结果,又会因这个事实本身与作为普遍资籍的自由的龃龉而自相矛盾,因此作为普遍资籍的自由必须得到所有人的同意。这个二律背反其实牵涉更为深刻的问题(比如罗尔斯提到的代际的关系),因而也就包含了更多的自由困境。
我们看到的事实是,无论是作为普遍资籍的自由,或者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自由,这个要求既在理论上也在实践上都面临巨大的、似乎不可克服的困难。它作为一种主张和理想不仅未被人们放弃,相反却成为现代世界的主流观念。在现代形形色色的政治哲学之中,情况也是如此。这一点提醒人们,可行的路数或许不在于直接追问作为普遍资籍的自由如何达成这个一般而确实抽象的问题,而在于如何规定自由?或者换言之,人们需要并且应当得到的,究竟是什么样的自由?

 U582679646
U582679646
 U882673919
U882673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