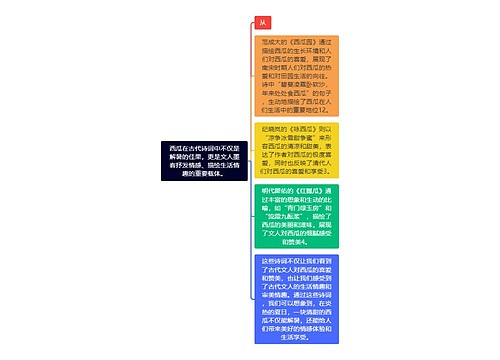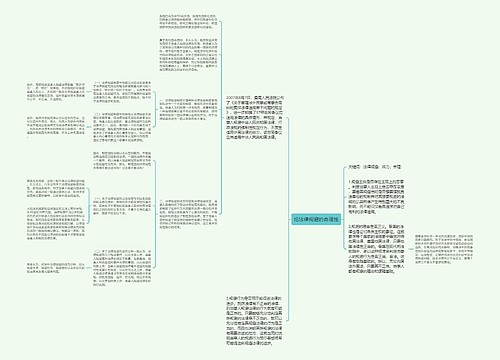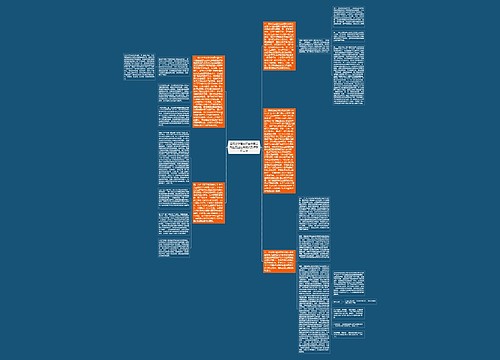内容提要: 法学社会学属于知识社会学范畴,知识体系依不同范式可一分为三:科学、规范学、人文学,三者分别追求:真、善、美。社会自由是知识发展的重要条件。法学的研究具有特殊性,法律可以被权力者私用,也可以成为公器。好的法学只是好的法律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中国的法学社会学需要研究的课题太多,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想象”得从知识社会学说起,因为想象中的她当是知识社会学的一个分支。说起知识社会学,所谓的“李约瑟难题”就是一个典型的知识社会学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以此为主题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当然,也有人认为李约瑟难题没有意义,席文(Sivlri)就认为,与其追究现代科学为何未出现在中国,不如去研究现代科学为何出现在西方。不过,不管李约瑟难题有没有意义,双方的论辩都是在知识社会学的范围内展开的。知识社会学发端于拿破仑时代的意识形态学派,意识形态学派是科学泛化的时代产儿。想当年牛顿的成功使科学知识成为一切知识的权威,种种知识都“沐科学而冠”,意识形态名列其中。拿破仑的臣民法国人塔西认为,意识形态也是科学,他甚至创立了一个意识形态学派,不过拿破仑对此嗤之以鼻,认为那不过是不明事理的知识分子的胡思乱想。虽然现在没有多少人会记得这个塔西,但是他的研究却催生了一个新的学科:知识社会学。
知识社会学是一门研究知识或思想产生、发展、知识与社会互动的学科。1924年,德国社会学家舍勒在《知识社会学的尝试》一书中率先使用“知识社会学”的名称。早在上世纪30年代,知识社会学就已传人中国。但是1949年以后它失音,即使在改革开放以后哲学界有人提起它,法学圈子里还是很少有人提及。在数以十万计的法学论文中,只检索到6篇刘星、徐亚文等教授的涉及知识社会学的文章,且均把知识社会学当作研究工具使用,并不是研究知识社会学。
我最早接触知识社会学源自巴伯的《科学与社会秩序》,这是一本科学社会学经典著作,它对我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信念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力,为我打开了一扇思考的大门。它使我知道,思想与社会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也从一个侧面告诉我自由的价值社会自由是知识发展的重要条件。“‘自由’社会的社会价值和社会组织,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和自主总体上一致这一结论,也适用于社会科学。”“我们的确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一个把社会价值置于‘批判理性’之上的社会,社会科学也能达到甚至是现今相对低水平的发展阶段。”美国的社会“理性化进程”“包括并建立在对所有社会组织结构、所有社会价值的批判性审查基础之上·一正是由于能自由地理性地去研究社会的最基本的东西,才形成了社会科学,也由于有了这种自由,社会科学的未来发展才有了保障。”[1]我相信理性人很难驳倒上面的结论。
如果说知识社会学还有人提及的话,那么,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法学社会学”这一名词则至今在中文里我还没有看到。我这样说是因为有的人将“法律社会学”称为“法学社会学”,那是误用,不能算数。
我想象中的法学社会学属于知识社会学,它研究法学知识与社会、与法律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当然不是永远正确的“作用、反作用”的空谈。将法学与其他知识社会学分离出来专门研究有意义么?回答是肯定的。不唯如此,我认为意义很大。法学社会学研究的意义建立在法学的个性上。这得从我的知识“三分法”说起。
我认为将所有的知识都称为“科学”是对“科学”的误用,是唯科学主义的产物。现如今我们的图书分类中只有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极容易误导学人。人们没能区分“科学”和“学科”这两个词。我的知识三分法中,知识的范围很广,是“科学”所不能囊括的,“科学”只是知识体系的一个“学科”。依知识体系的不同范式,知识体系可以一分为三:科学、规范学、人文学。这三者各有自身的追求:真、善、美,他们也各有自身的范式:因果范式、该当范式、实用范式。规范学包括:法学、伦理学、神学、道德学。古代规范学的权威是神学,现代规范学的当家人则是法学。法学是追求善的学科,它的范式是规范的论证,该当性结论的论证,它的主要逻辑工具是演绎而不是归纳,科学恰恰是归纳的。
法学追求善这个特点就使法学同社会的关系相较于科学、人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更加密切;同时,法学研究的对象—法律—本身与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不同,法律可以被权力者私用,法律也可以成为公器,从而不同的社会中,法律对社会、法律对法学产生极大的、迥然不同的影响;再者,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法学本身可以成为法律的一部分,在这一点上,法学知识是远远不同于其他知识的。因此,法学社会学就具有了与其他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人文学社会学)的不同点。如果说巴伯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最终要寻求建立一种与自然秩序相仿佛的社会发展的“人类秩序(Order of Human Nature)”的话,[2]那么,法学社会学的研究则要更进一步:建立一种“善的人类秩序‘,。猴山上的秩序是法学社会学的反面参照。这些,当然不止这些,就使法学社会学独立出来进行研究具备了意义。
进一步,他论证道,好的法学也只是好的法律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法学再好,弃之不用,也是白搭。“然则有极善之法,仍在乎学之行、不行而已。学之行也,萧何造律而有文、景之刑措,武德修律,而有贞观之治。及其不行也,马、郑之学盛于下,而党锢之祸作于上,泰始之制颁于上,而八王之难作于下。有法而不守,有学而不用,则法为虚器,而学亦等于危言。此固旷观百世,默验治乱之原,有足令人太息痛哭者矣!”读了沈家本带着哭腔的睿智之语,今人笑得起来吗?
沈家本进一步痛斥当时的人自己不守法,而埋怨法律无用;不行法学,而斥法学无用。“法立而不守,而辄曰法之不足尚,此固古今之大病也。自来势要寡识之人,大抵不知法学为何事,欲其守法,或反破坏之,此法之所以难行,而学之所以衰也。是在提倡宗风,稗法学由衰而盛,庶几天下之士,群知讨论,将人人有法学之思想,一法立而天下共守之,而世局亦随法学为转移。法学之盛,馨香祝之矣。”[3]读读沈家本一个世纪前的痛诉,想想不按法理出牌的大法官行于世,再看看种种屁股指挥脑袋的法学现象,法学社会学的研究不正是当下中国法学之急务吗?
沈家本上面提到的问题都是法学社会学极其重要的问题,当今之世我们碰到的问题与沈家本的问题极其相似,有的比沈家本时代还要严重。用法学社会学的方法,我们就得如此发问:当法律没有起到很好的社会效果的时候,我们不当“软化法律”,更不当舍法律而治。而是当问:第一,法律得到实施了么?如果回答是,我们当进一步再问:第二,法律如何?当法学的社会效果不怎么样的时候,我们不是放弃法学,而是当问:第一,法学“行”了么?如果行了,我们要问:第二,法学如何?如果法学有问题,我们就得问第三个问题:法学为什么幼稚甚或低劣?这又有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法学研究者的素质如何?法学研究的方法与范式如何?法学的价值观是不是有问题?法学研究的组织结构是否有利于法学的发展?什么样的法学研究组织有利于法学之盛?社会有没有为法学研究提供良好的环境?法学发展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条件?等等等等。
法学社会学的问题远远不至这些,它天天在拷问着我们,只是它看见我们,而我们却时常看不见它们而已。比如,最近,江平、郭道晖、李步云等前辈法学家在回顾学术历程的时候,一个个不堪回首,甚至涕泪横流,我相信这是一个法学社会学的大问题。又如,前一时期大家都在问“法学向何处去”,中国的法学是不是法学家想怎么走就怎么走的?种种法学思潮与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如何?这些也是法学社会学的大问题。再比如,刑法学界关于犯罪构成三要素说和四要素说的争论,特别是其争论的方式,也是很好的分析个案。余者如中国特色论、本土资源论、权利本位论、大局司法论、调解优先论、“马锡五审判学”、法律全球化论等等,都可以作为法学社会学的分析对象。
上面的问题对于法学社会学研究而言当然是挂一漏万。我想象中的法学社会学问题分为两块一是总论,二是分论。总论部分讨论这样一些问题:法学是什么?法学研究什么?法学及其研究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条件?法学对社会发展有何影响?法学产生社会影响的条件是什么?分论可以讨it:法学的组织(重点是中国法学会)与法学发展、中国法学教学研究机构中的法学家、中国法院中的法学家、中国的期刊制度与法学发展、法学评价制度与法学发展、中国法学抄袭现象的法学社会学分析、法学家个人人格与法学发展……
想象到这里,巴伯在将近50年前的研究结论蓦然跳出来:自由是科学发展的条件。这一下将我击回到现实中,耳边响起奥巴马的就职演说:我有一个梦……
注释:
[1][美]伯纳德?巴伯:《科学与社会秩序》,顾听等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90页。
[2][美]伯纳德?巴伯:《科学与社会秩序》,同上注,第310页。
[3]上述沈家本引言均见沈家本:《法学盛衰说》,《历代刑法考》,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43页以下。

 乐三白
乐三白
 U275265419
U275265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