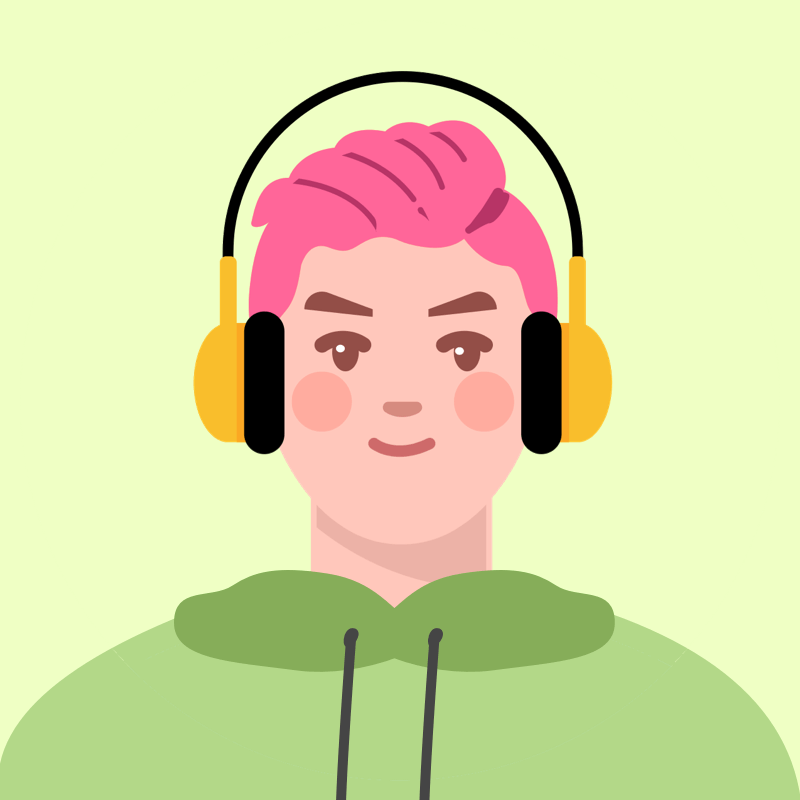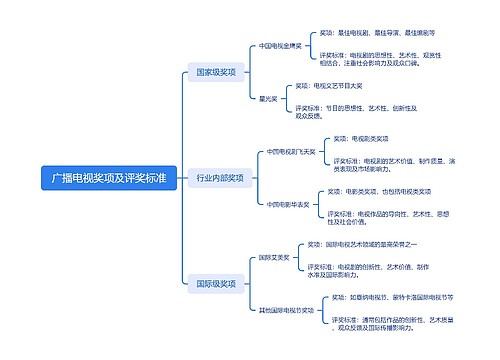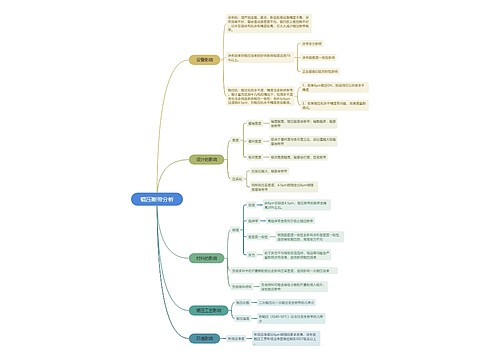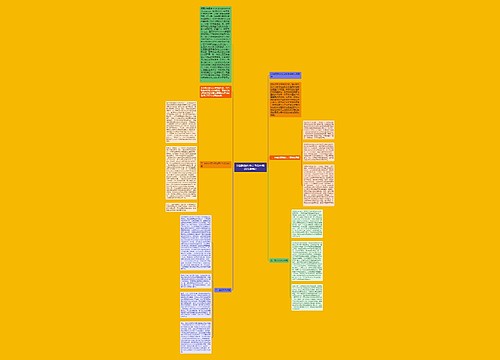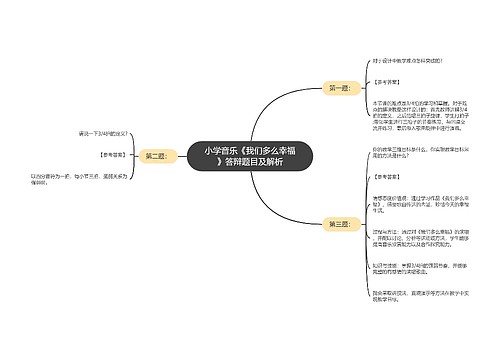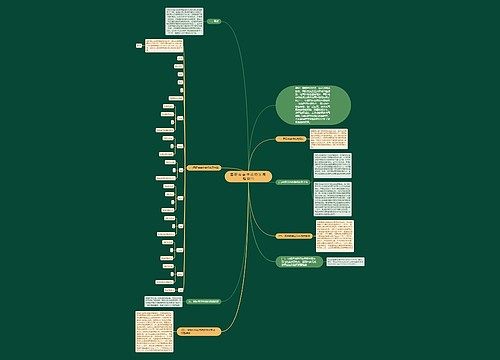(2) 涉及到公平、正义的法律目标和国家的基本法律政策、善良风俗及社会公益 ,即公共秩序的规则。有的学者认为应对这两部分作明确的区分 ②,但从法律功能的角度来讲 ,强制性规则和公共秩序所起到的作用是一致的 ,即限制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排除本应作为合同自体法的外国法的适用 ,或直接适用国内法 ,维护特定国家的司法利益和公序良俗。
特定国家的强行法制对维护本国利益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各国的国际私法理论与实践中得到了普遍的重视。但由于强行法的概念本身有着不确定和富于弹性的一面 ,其直接后果就是赋予法官在适用时广泛的自由裁量权 ,当然也包括滥用的可能。公共秩序滥用的直接后果是大大降低了国际私法在协调各国法律冲突中的价值 ,导致的进一步的后果就是妨碍了国际民事交往的稳定和安全 ,这与当今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是相违背的。③可喜的是 ,随着国际民商事交往的日益频繁 ,对强行法尤其是公共秩序的适用加以限制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要求 ,各国在此问题上表现出了积极的变化:
(1)采用“客观说”或“结果说”,即并非仅仅因为外国法的内容与本国强行法制相冲突即加以排除 ,只有当适用该外国法的结果危及本国利益时 ,才予以排除 ,且这种危害是实质性的和明显的。④
(2)区别国内公共秩序和国际公共秩序 ,在国际商事纠纷的处理中只适用国际公共秩序的标准。
(3)在本应适用的外国法被排除时 ,并不绝对代之以本国法。⑤
(4) 将公共秩序保留作为冲突法的例外 ,谨慎适用。
在国际民事诉讼中 ,受诉法院作为国家司法权的代表 ,有义务服从本国的法律适用规范。有在可能适用外国法的情况下 ,必须严格服从本国的强制性规范和公共秩序。属于本国法律专属管辖的事项 ,必须排除本应适用的外国法 ;国内没有强制性规定的 ,如果适用冲突规范指向的法律将违背法院地国的国家利益、法律秩序及政策、善良风俗等 ,则该外国法同样应予排除。
国际商事仲裁较之国际民事诉讼是完全不同的两套体制。自治性的特点给国际商事仲裁预留了广阔的空间 ,但国际商事仲裁的有效存在需要国内司法制度的配合。因此 ,作为国内法体系的组成部分 ,强行法必然也会给国际商事仲裁的实体法律适用带来若干影响:
首先 ,在仲裁过程中 ,仲裁庭为保证将来做出的裁决不被撤销且能得到及时的承认与执行 ,仲裁员在法律适用的过程中应当考虑到特定国家的强制性法律规范和公共秩序。所谓特定国家 ,主要是指仲裁地所在国和承认与执行地国。由于争议当事人在选择仲裁地时更多是出于中立的考虑 ,存在着很大的随意性 ,因此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并不存在着传统国际私法意义上的“法院地法”。同样 ,仲裁庭的选择亦是出于当事人的合意 ,仲裁庭更多是对国际商事交易负责 ,而不对任何主权国或其国内法负责。因此 ,仲裁庭考虑以上强行法制的出发点不同于国际民事诉讼的法官 ,与其说是出于对特定国家利益的考虑 ,不如说是对自身做出的裁决可执行性的关注。同时 ,出于公平合理的考虑 ,仲裁庭甚至可以绕开特定国家的强制性规定 ,这也是仲裁庭对当事人负责的表现。在伊朗 ???美国索赔案的审理中 ,仲裁庭结合《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⑥及《国际商事合同通则》⑦涉及利息的规定 ,将利息请求视为赔偿总额的一部分 ,以“赔偿代替利息”的原则 ,成功规避了伊斯兰教的利息禁止规则 ,为裁决在伊斯兰法制环境下的执行扫除了障碍。⑧
其次 ,在对国际商事仲裁进行监督时 ,仲裁地所在国的公共秩序被作为一个通用的标准。迄今为止 ,几乎所有的国家均在本国仲裁法或民事诉讼法中将违反“公共利益”或“公共秩序”作为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 ,无一国家愿意放弃这最后的“保险阀”。随着“意思自治”原则的深入人心 ,各国仲裁法均将当事人自愿和仲裁庭自治作为基本精神规定下来。在司法监督体制中表现为 :从法院的广泛监督转为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由对程序和实体的“双重监督”作为仅对程序性事项进行监督。⑨其中英国仲裁法的改革便很好地反映了这种趋势。随着监督权范围的受限 ,仲裁地法院很难用本国强行法来对国际商事仲裁的实体法律适用加以限制。“公共秩序”这最后一道“安全阀”的作用便突现了出来。仲裁地法院能否以“公共秩序”为由对包括法律适用在内的实体事项进行审查成为关系到国际商事仲裁命运和前途的重要问题。
笔者认为:如前所述 ,国际商事仲裁地的确立存在着很大的偶然性 ,仲裁的程序和实体法律适用也呈现出“非国内化”的趋势 ,仲裁的进行以及裁决的做出和仲裁地所在国的关联日益单薄。单纯以仲裁地国的法律秩序和法律观念去衡量仲裁裁决难以保证公平合理 ,是无疑是对国际商事仲裁体制的独立性的伤害。因此 ,在审查仲裁裁决的做出时 ,应对“公共秩序”作狭义解释。当然 ,这并不妨碍法院地法对正当程序(dueprocess) 和仲裁员行为道德作出规范。
其三 ,在执行地法院 ,一个国际商事裁决有可能因“公共秩序”的原因被拒绝承认或执行。《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二款明确规定:承认与执行地所在国之主管机关 ,认定承认或执行裁决由违该国公共政策的 ,可以拒绝予以承认及执行仲裁裁决。由于公约并未对“公共秩序”的涵义、范围及使用条件作具体的规定“。公共秩序”的使用完全依赖于执行机关的自由裁量。这个看似危险的漏洞实际并未给国际商事仲裁体制带来不良的影响。其实 ,从《纽约公约》对《日内瓦公约》在“公共秩序”上的改良 ③便能看出:各国在“公共秩序”的使用上从严解释、谨慎使用的态度。在实践中 ,各国法院较多接受了“国内公共秩序”与“国际公共秩序”的划分 ,在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中只承认国际公共秩序;在采用“公共秩序”时采取客观说 ,即以承认与执行的后果作为判定是否违反该国的“公共秩序”的标准 ,且是在具有极端的情节(extreme cases) 或无法容忍的场合(intolerable cases)才认定违反了公共政策。以上方法达到了严格适用“公共秩序”的目的 ,有效维护了争议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和仲裁庭的自主权。据范?登?伯格对140起拒绝执行仲裁协议和仲裁裁决的法院判决的统计 ,仅有5项是以公共政策为由做出的。④可见 ,公共政策作为拒绝承认与执行的理由是在极其狭窄的情况下才被援用的 ,而且往往是在当事人用尽其他抗辩理由后法院才考虑是否援用公共秩序的理由。⑤除非有极端的情况 ,执行地国的强行法制很难对仲裁的实体法律适用产生限制。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 ,特定国家的强行法制会给国际商事仲裁中的法律适用带来一定的限制 ,但其作用远不如在国际民事诉讼中来的那样明显。这种区别是由国际商事仲裁体制自治性的特点的决定的。首先 ,在起源上 ,国际商事仲裁是商人社会自律的产物 ,商人们为了规避诉讼程序的繁琐与不经济 ,追求个体利益的最大化 ,才发展出了仲裁这种自律性的冲突救济方式; ⑥其次 ,在价值取向上 ,国际商事仲裁首要追求的是效率。快速高效与公平正义 ,商人们似乎更注重前者。作为国内法部分的强行法制很难像在诉讼体制中那样 ,对仲裁发生有力的限制 ;其三 ,在与特定地域的联系上 ,国际商事仲裁与国际商事交往紧密相连 ,国际性、跨国性的特点十分显著。而且 ,仲裁地的选择完全基于当事人的合意 ,考虑到方便、中立等因素 ,仲裁地的确立有相当的随意性 ,仲裁庭没有国籍 ,它对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均无效忠义务 ,因此也没有一般意义上的“法院地法”。其四 ,在自主性上 ,国际商事仲裁的当事人显然要比国际民商事诉讼中的当事人要有更多的自由度和决定权 ,意思自治贯穿于国际商事仲裁的全过程。以上特点在国际商事仲裁的实体法律适用上表现为:当事人有选择的 ,应依据当事人选择的法律规则 ,即使选择与合同本身并无任何联系;当事人没有选择的 ,仲裁庭既可以依已有的冲突法规则确定实体法 ,也可以不依任何冲突规则之确定可使用的实体法 ,或者可以根据国际法、一般法律原则和国际商法(lex mercaria) 甚至“公平合理”原则(ex aeque atbono) 来审理案件。①这种趋势得到了一些开明学者的支持 ,也在新近的立法和实践中得到反映。仲裁庭在法律适用上受到特定国家强行法制的约束越来越小 ,有案例表明 ,虽然特定国家的强行法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确有限制 ,仲裁庭仍然绕开了相应规定而根据当事人选择的法律做出裁决。1989年国际商会仲裁院(ICC) 在德国科隆开庭审理一家意大利公司诉比利时公司的批发合同纠纷案。双方选择意大利法为合同准据法。而对于比利时法有关终止“批发合同”的强行法规定 ②,仲裁庭援引 G. Sperduti 的观点 ③和1980年《国
际合同义务法律适用的公约》《(罗马公约》)的相关规定 ④,认定比利时法的有关规定对当事人自行选择的法律不构成影响。⑤
仲裁的顺利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立法和法院的宽容和友善的态度。对仲裁宽容相待、法院于仲裁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大力支持仲裁(pro - arbitration)的发展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在对待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以及撤销问题上 ,大多数国家的法院尽量维持仲裁裁决的效力 ,如果仲裁裁决存在一定的瑕疵 ,法院一般行使自由裁量权仍然裁定承认予以执行或者不予撤销仲裁裁决。②法院的这种开明态度不仅有利于仲裁的独立发展 ,同时也有助于建立本国法制在现代商业社会中的良好形象。我国法院也应该顺应这样一种已经明朗的趋势 ,对我国强行法制在适用于国际商事仲裁时做出必要的限制。这不仅有助于仲裁事业在我国的独立发展 ,维护我国涉外仲裁在国际商事仲裁界的良好声誉 ;同时也有助于抑制地方保护主义 ,净化法院执法风气 ,为改革开放向纵深方向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