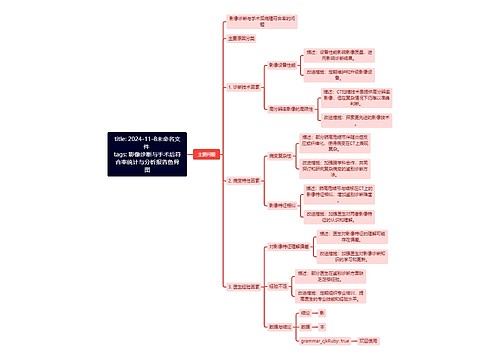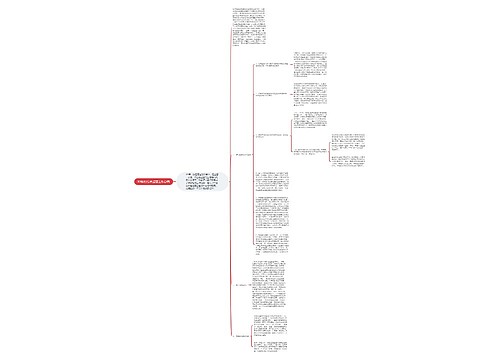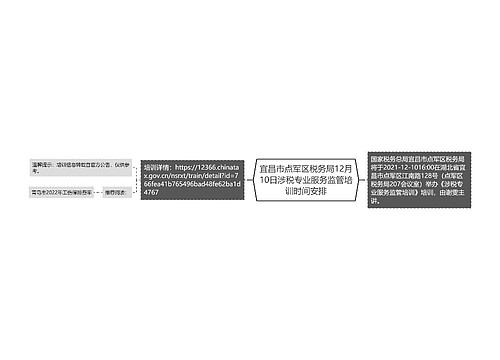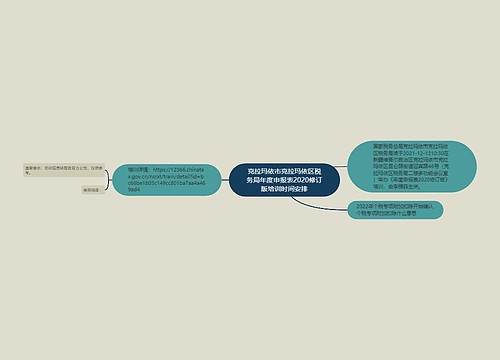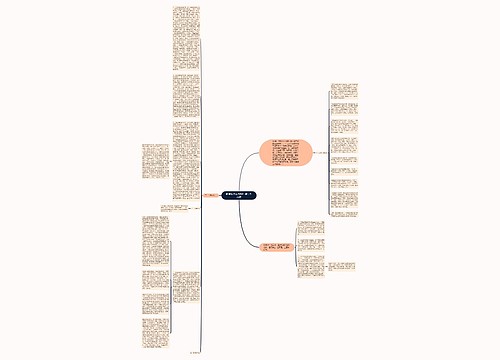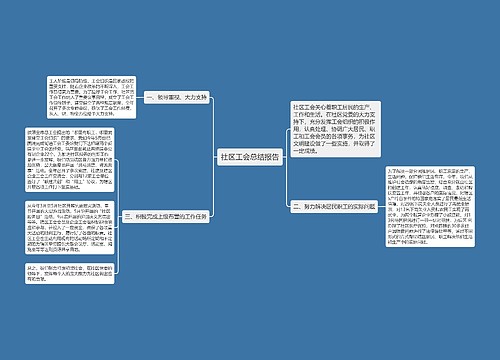综观本案,被告的抗辩亦有相当分量的事实基础,案涉货物铅封变动是福州海关的码头验货使然,而该批货物为塑料雨具,属低值易耗品,在码头监管森严的情况下,论理不易成为偷盗的主要目标。因而,本案货物原装短少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些,且被告提供福州海关第249号《作业流程表》为证,已尽举证义务,法院完全可以在被告举证的基础上认定货损属于原装短少,但法院最终判决保险公司胜诉!值得思量,其实这也正是本案的典型之处。
我国属大陆法系国家,受法制环境的限制法院不能应用法理判案,只能依据现有成文法律来判案,因此,法院在本案的判决中欲对保险公司的代位求偿予以保护,只能在判文上使用技巧,如:判决认定货物短少缘由的依据是目的港检验人的“推测原因为失窃”,并以此认为“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原告据此理赔并无不当”,对保险公司的代位求偿权予以保护。法院对货损发生的实际原因亦未查明,推测为失窃的模糊语言并不排除货物原装短少的可能性,而在此种情况下以“被告认为本案货损短少是发货人/托运人未将该部分货物装运,但不能举证”为由支持了保险公司的诉讼请求,无疑内在包含着保险人善意理赔的法律保护。
而法院对善意理赔的保险人利益予以保护的意图,从其对本案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上明显向原告倾斜亦可见一斑。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定,原告主张案涉货损是承运人责任期间发生失窃所致,依据是货柜铅封变动以及目的港检验人“推测为失窃”的结论。被告举证表明货柜在进入码头前是原铅封号,海关验货后更换新的封号,所换铅封号在整个航程中均未再发生任何变动,因此主张在码头并未发生失窃,货损是原装短少。客观分析双方举证责任完成情况,原告明显处于劣势,因为推测为失窃与事实发生了的失窃显然不同,唯有真实的失窃才属于保险事故应予理赔,原告在被保险人索赔时,没有相反证据表明货损短少是其他不属保险范围的事故造成,所为理赔无可厚非,符合保险法及时赔偿的立法宗旨,也维护了自身的商业形象。然而问题在于被告完成了“铅封变动是海关在码头验货使然”的举证责任后,主张在码头货物失窃的举证责任论理又应落到保险公司头上,而保险公司并没有进一步的证据支持该主张。但厦门海事法院则见仁见智,从被告主张“货损短少是发货人/托运人未将该部分货物装运但不举证”的角度判令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瓜果,究其原因,这显然是在自由裁量的范围内,倾向于保护善意理赔的保险人的利益。因此,本案判决中无疑昭示着保险人的善意理赔应获得法律保护的审判价值理念。
本案中保险人鉴于铅封变动及目的港检验人推测为失窃致使货损的结论下凭齐全的单证对货损予以理赔在主观上实无过错可言,但本案却属货物原装短少的可能性,却对传统的保险代位求偿权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若因循传统保险代位权理论,在前述情况下保险人理赔将由于此后的事实证明确属原装短少而被判不是保险事故,则无保险代位权可言,保险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法律上切实的保障。尤其是在海洋货运险业务中,收货人往往是处于法律环境大相径庭的异国他乡,向其追讨错误理赔款撇开事实上的困难不谈,还存在着可能由于具体法律规定的冲突(即依保险人所在国无代位权,但依收货人所在国法律在该种情况下则有代位权)而得不到保护。因此,本案的审判实践对保护保险人的善意理赔、对维护保险业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既然传统的代位追偿权理论使保险人在追偿时受到限制,促使我们思考代位求偿权深层定位的问题。返观我国的《保险法》与《海商法》均未对保险代位权作详尽的规定。《保险法》第44条第1款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海商法》第252条规定:“保险标的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是由第三者造成的,被保险人向第三者要求索赔的权利,自保险人支付赔偿之日起,相应转移给保险人。被保险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必要的文件和其所需知道的情况,并尽力协助保险人向第三者追偿”。从立法的内容看,两部法律条文对保险代位权的行使规定了一个前提两个要件,一个前提即所发生的事故应是承保范围内损失(保险事故),两个要件分别为支付保险理赔款以及追偿已赔付的保险金额为限、追回金额超过赔偿限额的应当归还给被保险人。就保险代位权的立法要旨看,上述规定实质上是要求保险代位权的行使应有保险合同上的依据。
然而,目前的立法实际仅是对保险代位权行使的依据作了规范,并没有回答到底什么是保险代位权,未对保险人在理赔时根据提交的齐全单证判断是保险事故,而在追偿时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明表明该损失并非保险事故时是否仍享有追偿权(本案假设的事实正符合这种情况)作出进一步的规定,甚至也未对保险人在承保责任外发生损失的自愿赔付时规定如何操作。这也是上述案例中保险公司在本案中的处境,而该保险公司的代位求偿权始终被对方质疑,这在诉讼程序上并不鲜见。保险人作为原告在此类诉讼中,其代位求偿权问题经常被被告方利用作为抗辩的手段,被告方总是选择在保险人的追偿前提出先发制人,以达到回避在实质性问题方面的举证义务,而他们往往能够达到目的的原因之一,恰恰是我国《保险法》关于保险代位权的性质、成立和行使要件、行使方法及其内容、代位权行使的保障和救济、代位权的行使限制等许多理论和实务问题没有提供完整的答案,法院的审判实务方面,也没有经典的判例可以援引。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79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第80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第81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力,但该从权力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除外;第82条规定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本文认为在保险合同中有关保险代位权的问题,同样涉及被保险人债权的转让,《合同法》中有关条款的规定,应当同样适用。亦即只要被保险人出具《收据及权益转让书》并将债权转让的事实有效通知第三方责任方,就意味着保险人取得的代位求偿权的有效性毋庸质疑。否则,保险人在赔付被保险人之后向责任方追偿时诉诸法庭,却首先面临的将是法官对“保险理赔是否符合保险合同条款”的审理,这对保险人不仅颇为不公而且会阻碍保险业的进一步发展。
我们不妨进一步设想,假如保险人在商业经营中从特殊的角度考虑(如保险条款不尽完善、政府部门的压力、与广大客户的关系等),对承保责任范围外的损失作了自愿赔付或通融一定比例的赔付,那么保险人取得在该自愿赔付或通融一定比例赔付的金融范围内的代位求偿权是否有效?答案是肯定的,上述《合同法》规定仍然适用自愿或通融赔付的情况,因为保险人的自愿或通融赔付并不排斥或否定其代位权的存在,理论上保险代位权为保险人依照法律规定所享有的权利,其因为保险合同的订立而当然发生;保险人放弃依照保险合同而享有的免于承担保险责任的利益,并不说明保险人放弃了保险代位权,造成被保险人损害的第三人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并不因保险人自愿或通融赔付保险赔偿金而受影响,第三人仍得以其对被保险人的一切抗辩对抗保险人。所以,保险人在保险合同约定无须承担保险责任时,仍然给予被保险人以赔偿的,可以对造成被保险人损害的第三人行使代位权。因此,不论保险人的赔偿是否基于保险合同的条款规定,在代位求偿权的问题上,只要被保险人的损害从保险人处得到补偿而因此将补偿范围内的代位求偿权转让给保险人,保险人因此获得的代位求偿权当然有效,这样既方便和满足了商业贸易发展的需要,最大限度内尊重了当事人合同自由的权利,也杜绝了被保险人的诉权转让后双重获利的可能,符合保险损害的补偿原则,又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在我国现行法律仅规定法定赔偿下的代位权的立法实践下,应当许可和保护甚至鼓励自愿或通融赔偿情况下的代位权的产生、存在和发展,而不能、同时也没有任何理由以前者来否定后者。

 U182637395
U182637395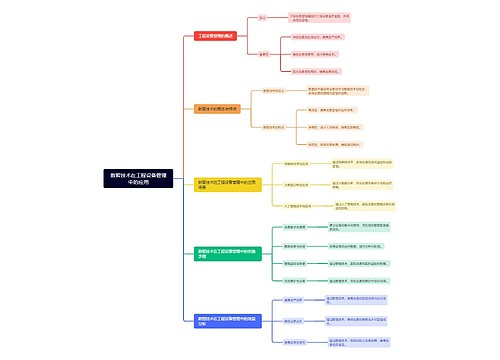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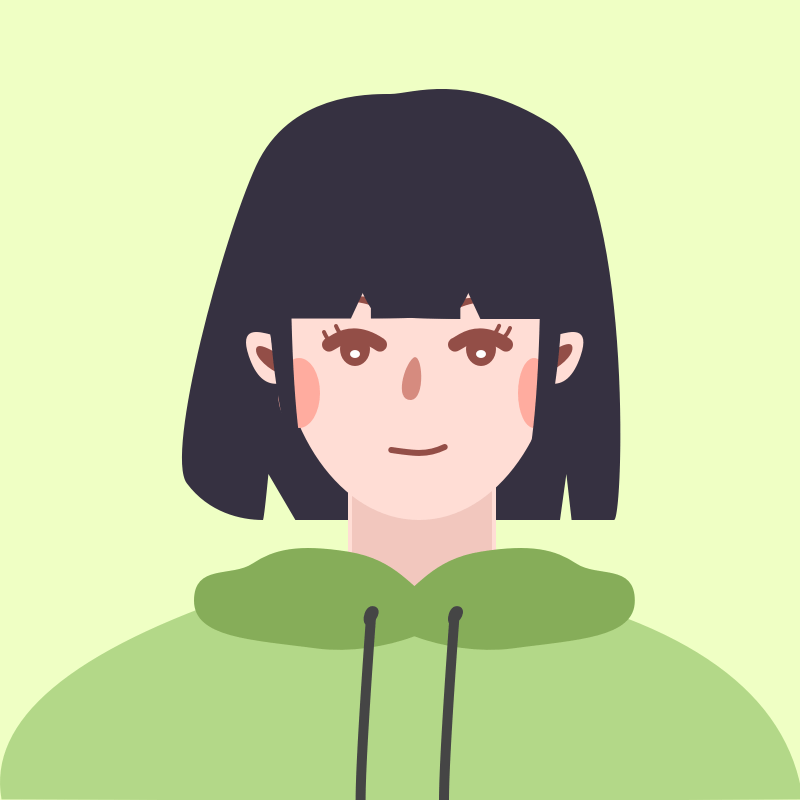 U880271396
U8802713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