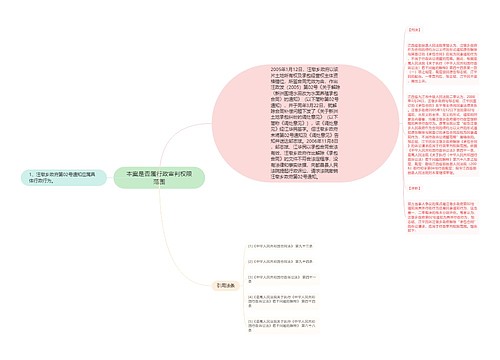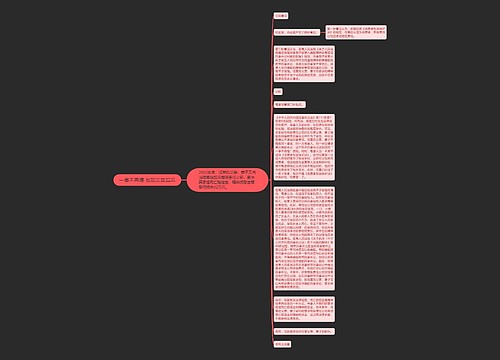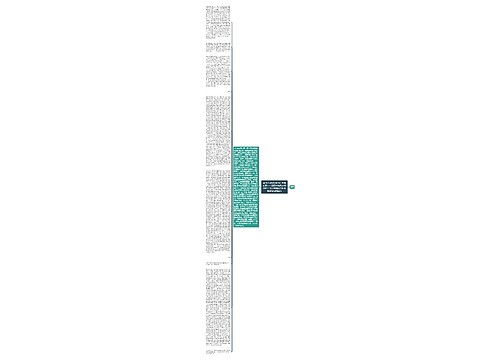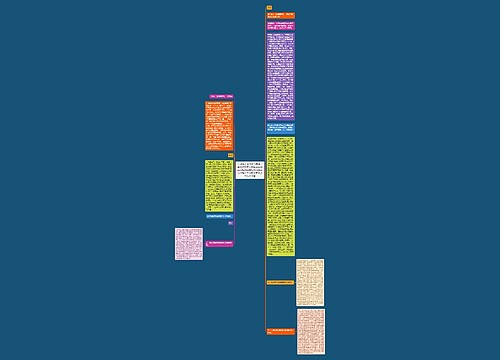朱玮诉襄樊学院教育行政处分案思维导图
自我孤立
2023-03-10

教育
学院
襄樊
处分
被告
规定
上诉
行政诉讼
学校
决定
民事诉讼法
民事诉讼法案例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树图思维导图提供《朱玮诉襄樊学院教育行政处分案》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朱玮诉襄樊学院教育行政处分案》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3579eec4b6933a64fb892c2a32cf887d
思维导图大纲
相关思维导图模版
朱玮诉襄樊学院教育行政处分案思维导图模板大纲
行政判决书
(2000)鄂行终字第4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玮,女,生于1980年5月4日,汉族,湖北省宜昌县人,襄樊学院学生,住宜昌县小溪塔镇梅子垭村。
委托代理人魏光奎,湖北法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襄樊学院。
法定代表人李树棠,副院长。
委托代理人张卫兵,湖北珞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丁国民,襄樊学院工作人员。
上诉人朱玮、襄樊学院因勒令退学处分一案,不服襄樊市中级人民法院(2000)襄中行初字第21号行政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安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0年9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朱玮的委托代理人魏光奎,上诉人襄樊学院的委托代理人张卫兵、丁国民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根据被告的举证并经庭审质证认定:1998年6月,湖北省人民政府根据原国家教委的批准,决定将原襄阳高等专科学校等三所院校合并组建为多科性本科院校的襄樊学院。朱玮于99年9月考入襄樊学院艺术系。2000年3月,襄樊学院组织《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补考时,原告朱玮替同学李向荣代考,被监考老师当场查出。后襄樊学院就朱玮的代考舞弊事实作了通报,并上报学校教务处。同年3月6日,襄樊学院教务处召开处长办公会,认为朱玮违纪事实清楚,建议按《襄樊学院学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第16条的规定处理,学院教务处以学院的名义草拟了对朱玮等人勒令退学的纪律处分决定后,经襄樊学院负责人批准,于2000年3月20日以院政发(2000)031号文件形式印发。3月27日,襄樊学院向朱玮及其亲属宣布了上述纪律处分决定。朱玮认为处分过重,于次日向襄樊学院递交了书面申请,要求襄樊学院重新处理。襄樊学院于同年4月1日用专车将朱玮送回家。朱玮不服该勒令退学的处分决定,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襄樊学院是国务院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高等院校。高等院校作为公共教育机构,虽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行政机关,但依据我国教育方面的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国家实行教育学业考试制度,对高等学校学生的学籍管理、奖励与处分,由国家批准的高等学校组织实施。因此,高等学校在行政这一国家行政职能时,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其应当具有行政诉讼的被告主体资格。被告襄樊学对原告所作的勒令退学处分决定,使原告丧失学籍资格,直接影响、限制和否定了原告的受教育权和大学生身份权。受教育者在学校处于一种被管理者的地位,学校对受教育者受教育权和身份权的处理,系特殊的外部行政管理关系,不属于内部管理行为。被告襄樊学院辩称其不是行政诉讼的适格被告,对原告朱玮的处分决定属于内部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理由不能成立根据我国教育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明确规定,受教育者在学校组织的学业考试中,必须履行严格遵守考试纪律的义务,学校对受教育者违反考试纪律的行为享有酌情给予不同处分的权利。原告朱玮在学校实施学业考试过程中,替人代考,被告襄樊学院据此认定原告严重违反考试纪律,并作出给予勒令退学的处分决定有充分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原告辩称被告襄樊学院和处分决定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被告襄樊学院在作出处分决定时,虽有程序瑕疵,但尚不足以影响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原审法院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28条第1款第(2)、(4)项、第42条第(4)项、第43条第(4)项、第53条、第5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1)项、第53条第1款,参照原国家教委发布实施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62条第1款、第63条第(5)的规定,判决维持了被告襄樊学院对原告朱玮作出的勒令退学处分决定。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负担。
上诉人朱玮上诉称:1、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勒令退学处分有充分的法律依据是完全错误的。被上诉人作出处分时直接适用了《襄樊学院学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并未直接适用国家的法律法规,属适用法律法规错误;2、一审法院认定襄樊学院在作出处分决定时,虽有程序瑕疵,但尚不足以影响其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是错误的。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履行了向上诉人宣布处分决定的法定义务以及对上诉人进行教育和帮助的义务,其行为违反了《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63条、第64条的规定,严重违反法定程序;3、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处分属于特殊的行政处罚,一审法院对此未予认定是不正确的。上诉人因此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维护上诉人的受教育权和大学生身份权。
上诉人襄樊学院上诉称:1、本案不属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应依法裁定驳回起诉。理由是襄樊学院属事业单位,本身无行政权,所作的纪律处分又是一种内部管理行为,并非行政行为。因此,一审法院认为“高等学校行使对学生的学籍管理奖励和处分是一种国家职能,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应当具有行政诉讼的被告主体资格”是错误的;我国法律并未赋予大学生享有基于大学生身份所享有的身份权,因此,原审判决所称的大学生身份权没有法律依据。而受教育权既非财产权,也非人身权,其受到侵犯只有在法律法规规定时,才能提起行政诉讼。2、襄樊学院对对朱玮的处分决定不存在程序瑕疵。襄樊学院在对朱玮作出处分决定时是完全按《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的规定办理的,原审判决认定其在程序上有瑕疵没有根据。同时,上诉人在提交本院的答辩状中认为,其作出的处分决定所依据的《襄樊学学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是根据《教育法》、国家教委和省教委的有关规定制定的,学校依该规定对违纪学生予以处分,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襄樊学院在一审时提供的第8号证据证实的是一个已发生的事实,且该事实已为对方当事人在相关材料中所承认,它与事后收集证据,并将其作为处分决定的依据的情况不相同,一审判决未并其作为有效证据采纳是错误的。
原审被告向原审法院提交的主要证据材料有:1、原国家教委和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组建襄樊学院的批准文件;2、襄樊学院1999-2000上学期中原路校区补考安排表;3、考场情况登记表;4、朱玮替李向荣代考及朱玮、李向荣自己考试的试卷;5、襄樊学院艺术系就原告违反考试纪律作出的“通报”和“情况说明”;6、襄樊学院教务处处长办公会议记录及该院负责人签发的处分决定书原件;7、襄樊学院院发(2000)031号文;8、襄樊学院教师刘俊杰等的证词;9、原告要求襄樊学院重新复查和处理的申请书;10、《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襄樊学院学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等规范性文件。
原审原告向原审法院提交的主要证据材料有:1、襄樊学院作出的院政发(2000)031号处分决定。
上述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经本院开庭质证并审查认定,原审被告襄樊学院在一审期间提供的襄樊学院教师刘俊杰等人的书面证词系其在诉讼期间自行搜集,不具备证据的合法性,依法不予采信。原审被告提供的其他证据有效,可以作出本案定案根据。本院经审理所认定的事实与原判无异。
本院认为,上诉人襄樊学院系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高等教育机构,其性属于国家教育事业性组织。该机构本身虽不具有国家行政机关的法律地位和职能,但是根据我国教育法律法规的授权性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有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并实施奖励和处分的职权,该职权属于一项特定的行政管理职权。学校依据法律授权对受教育者作出涉及其教育权的处分决定,是学校实施的特殊行政管理行为。本案中,上诉人襄樊学院对朱玮给予勒令退学处分,即为根据教育法律法规授权实施的行政管理行为。朱玮认为该处分决定中断自己的学业,对其受教育权的实现产生严重影响,并据此提起行政诉讼,符合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也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规定的受案排除范围,原审法院予以受理并作出裁判正确。襄樊学院认为其不是行政机关,不能成为行政诉讼适格被告及处分决定不属于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我国教育法规和规章均规定,受教育者有遵守所在学校管理制度的义务,对违反学校管理制度和纪律的受教育者,学校有权予以相应的处分。上诉人朱玮在学校组织的学业考试中替人代考,严重违反考试纪律。襄樊学院在查清朱玮违纪事实后,依照其制定的学籍管理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作出作出处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所给予的处分亦未超出有关法规规定的种类和幅度。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布施行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对学生的处分决定应当“允许本人申辩”、申诉和保留不同意见。对本人的申诉,学校有责任进行复查”。由于襄樊学院未严格执行上述程序规定,其处分决定亦未经校长办公会集体讨论研究,原判认定其处分决定存在程序瑕疵并无不当。《襄樊学院学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是根据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制定的,襄樊学院适用该细则的规定对违纪学生进行处分,并未违反法律法律规定。因此,对朱玮提出的襄樊学院在作出处分决定时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审双方当事人提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上诉人朱玮和襄樊学院各负担1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沈福元
代理审判员张玲
代理审判员周丽萍
二000年十一月十三日
书记员张辅伦
[评析]
本案是因学生不服学校的勒令退学处分而引起的行政诉讼。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社会各界对本案极为关注。在一般人的理解中,行政诉讼就是俗话说的“民告官”,而本案的被告襄樊学院属高等院校,并非行政机关,能否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与此相联系的一个问题是襄樊学院对所属学生的勒令退学处分行为能否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这就涉及到对勒令退学处分行为性质的认识问题。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很多,这里仅就上述两个问题予以点评。
一、襄樊学院是否本案的适格被告?即襄樊学院能否
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被告认为,襄樊学院属事业单位,本身无行政权,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一、二审法院并未采纳被告的答辩和上诉意见,因为在我国目前情况下,某些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虽然不具有行政机关的资格,但是法律赋予它们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职权。这些单位、团体与管理相对人之间不是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而是特殊的行政管理关系。它们之间因管理行为发生争议而引起的诉讼,不是民事诉讼,而是行政诉讼。尽管《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所指的被告是行政机关,但是为了维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监督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依法行使国家赋予的行政管理职权,《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同时规定,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该组织是被告。因此行政诉讼的被告既包括国家行政机关,也包括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将被赋予行政管理职权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列为行政诉讼的被告,适用行政诉讼法来解决它们与管理相对人之间的行政争议,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学校有权“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由此可见,奖励和处分是学校对受教育者实施的一项特殊的行政管理。由于《教育法》的授权,襄樊学院成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可以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当然,并非只要法律、法规规定了某一组织的权利义务就一概认定其为授权组织,能否成为授权组织,关键是看此类组织本身是否具有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从行政法的发展方向看,用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界定行政诉讼被告并非长久之计,因为只要是法律法规,必然会对相关单位或组织的权利义务作出规定,甚至公民个人也会被赋予一定的权利。借鉴外国行政法的理论与实践,可以用公务法人的概念取代具有公共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授权组织的概念。所有公务法人与其管理相对人之间发生的公共管理纠纷都应纳入行政诉讼范围,这是解决像学生与学校、公务员与行政机关、军人与军队、监狱服刑人员与监狱、村民与村民委员会等具有特别权力关系纠纷的最佳途径。就本案而言,将襄樊学院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适用行政诉讼法来调整襄樊学院与受处分学生之间的纠纷也是同样的道理。
二、 勒令退学处分是否属于可诉具体行政行为?即使襄樊学院可以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但相对人并非对襄樊学院的所有行为均可提起行政诉讼。也就是说,在襄樊学院成为行政诉讼被告的前提下,学生因勒令退学处分而与襄樊学院形成的关系是否行政法律关系?这种关系能否受行政诉讼法调整成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与关键问题。被告认为,襄樊学院对学生作出的勒令退学处分是一种纪律处分,属内部管理行为,不属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对此,原告并未提出过多反驳理由,一、二审法院亦未展开说明。笔者以为,学生因勒令退学处分而与襄樊学院形成的关系是行政法律关系,而且勒令退学行为不是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所排除的“内部行政行为”,这种关系理应受行政诉讼法调整。《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了四种类型的案件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其中第(三)项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而提起的诉讼,这一规定被普遍认为是行政机关的内部行政行为不属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的依据。就本案而言,学生与襄樊学院之间的关系显然不属《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三)项规定的内部行政行为的范围。因为该行为仅限于行政机关对内部工作人员公务员身份的影响,不能任意扩大解释。襄樊学院根据《教育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对学生进行处分,这种处分权是法律授予的,是一种单方面作出的教育管理行为,这种行为直接影响(剥夺)了学生受教育的权利,属《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
三、 学生与学校打官司的进步意义。学生因不服勒令退学处分而将襄樊学院推上行政诉讼的被告席,尽管此案最终以学生败诉而终结,但其影响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料,也远远超过了案件本身。其进步意义在于:第一,弱者的权利应当受到重视。《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对学生与学校之间的纠纷解决途径均未作出明确规定,没有一部有关教育的法律规定学生可以起诉学校。就学生与学校的关系而言,学生显然是弱者。对于弱者权利的保护,我国的教育立法是滞后的。这种滞后是客观存在的,但学校不能因此就无视对受教育者权利的尊重与保护。第二,是非曲直应由法院公断。在一个法治国家,当一个公民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他要有一个说理的地方。西方国家有这样一种理念叫做“司法最终解决”,我们国家还没有这样明确的提法,但最高法院肖扬院长曾经说,人民法院是人民群众说理的最后地方。从这个角度讲,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走了所有能走的路,而问题依然不能解决的时候,他就有到法院去说理的权利。仅从这个角度讲,法院受理此案是毫无问题的。第三,社会是一个统一的大家庭,学校也不能游离于这个大家庭之外。全社会共同遵守的规则,学校同样应当遵守。学校的规范(如《襄樊学院学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也是一种社会规范,它不可能超越法律。人民法院受理学生对学校的诉讼,可以将学校的某些规范纳入合法性审查的范围,促使人们意识到某些规范的不合法性,最终导致不合法规范的改变。司法的介入和正确的判决,使得规范更具权威性,这同时也将促使人们更自觉地去遵守正确、科学的规范。
作者:张辅伦
查看更多
《数字教育平台开发项目策划》思维导图
 U482242448
U482242448树图思维导图提供《《数字教育平台开发项目策划》》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数字教育平台开发项目策划》》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d6437326e3e07ecf1e5e178ba84d0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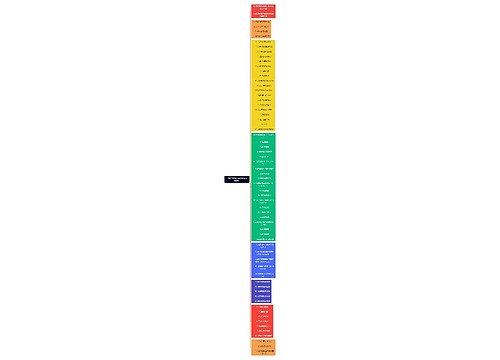
教育工作者AI场景思维导图
 U774656410
U774656410树图思维导图提供《教育工作者AI场景》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教育工作者AI场景》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d4b25376634866cb52221299e83913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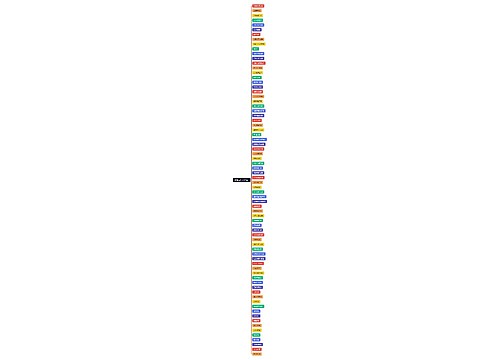
相似思维导图模版
首页
我的文件
我的团队
个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