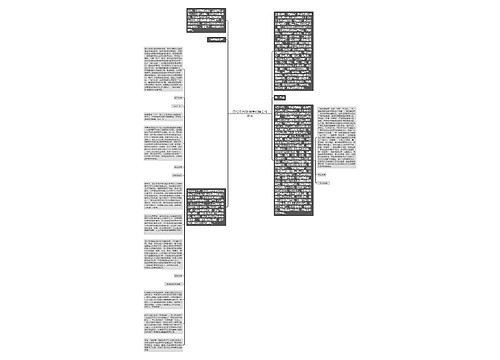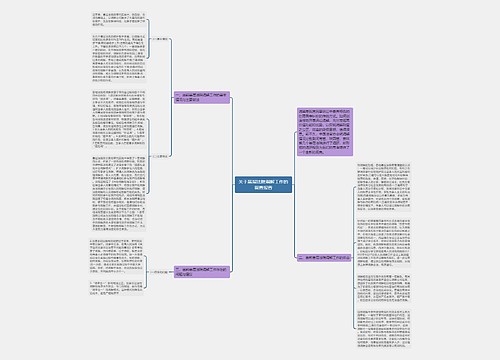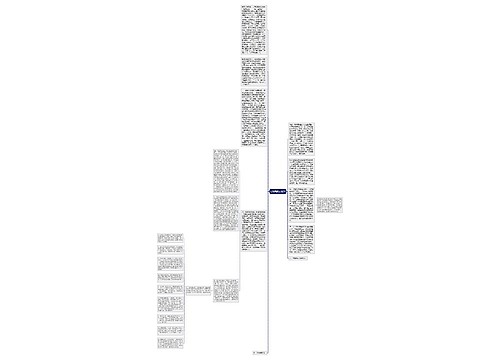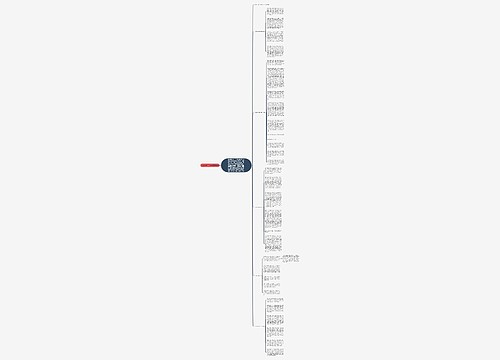虽然调解制度在人民法院担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捍卫者的进程中被赋予了相当重要的价值依赖,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实际运用中对于调解制度存在一些片面的、形式化的理解误区,背离了调解制度的初衷,影响了制度效用的发挥。
一是调解功能的泛化,将调解结案等同于“案结事了”。如前所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利益格局出现结构性调整,在新的社会结构尚未确立、稳定之前,社会矛盾处于高发期。社会矛盾的最终解决,有赖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政治经济体制的相应完善,而不仅仅是依靠某一项司法制度。将调解作为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其出发点是好的,但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不乏这样的例子:有些矛盾比较尖锐的纠纷,法官为了努力实现“案结事了”,想尽一切办法希望促成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出于各种原因当事人最终接受了调解,法官也松了一口气,却没想到有的当事人反过来投诉法官强制调解、违法办案,试图通过投诉、上访推翻调解协议。虽然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是无理上访,但却给本案的“案结事了”投下了些许阴影。对于调解功能的扩大理解,使得“案结事了”浮于表面,潜伏了更深层次的危机。
二是对调解工作评价标准的简单量化,将调解率等同于办案效果、业务能力。为了最直接地体现法院促进社会和谐的工作成效,人民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不得不将调解率作为评价业绩的一项考核指标。近年来,一些在诉讼调解方面走在前列的基层法院几乎是以每年5%以上甚至10%的幅度在提高诉讼调解的结案率,调解结案率已经超过60%,个别法院甚至已经超过70%,从而成为诉讼调解的“先进”(当然,有的法院调解结案率的提高不过是单纯统计数据上的变化而已)。在调解率实在没有更多上升空间的情况下,撤诉率也被作为调解工作的成效表现,并入调解率的统计,并称为“调撤率”。这种评价机制的合理性值得我们思考。一方面,法官苦于实现调解率指标,不可避免地强势介入调解,当事人的处分权事实上得不到充分行使,这样的调解仅在程序上看似体现了调解的效率价值,其在实体上实质是违背了调解的实质意义;另一方面,对调解率的过分要求,助长了法院之间相互攀比的不正之风,调解率虚高,脱离了诉讼调解工作的实际。
导致这种态势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对法院调解制度的价值期待,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诉讼调解的正确定位和运行轨道。笔者以为,应当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诉讼调解,使诉讼调解回归应有的定位。强调调解价值的回归,不是要弱化调解,而是要更有效地发挥其促进社会和谐的效用。强化调解,不在于无限扩大调解的功能和适用范围,而在于正确、规范适用调解。所谓用之有度,就是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只有和其他纠纷解决机制相互配合,相得益彰,才能共同担当起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使命。
因此,笔者以为,当前法院调解制度改革的出路还在于规范现有的诉讼调解机制,使之符合法律规定的实施原则,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多部门联动协调的大调解机制,而不能牺牲诉讼调解的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将法院调解作为包罗万象的一揽子解决方案。

 U633687664
U633687664
 U582679646
U582679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