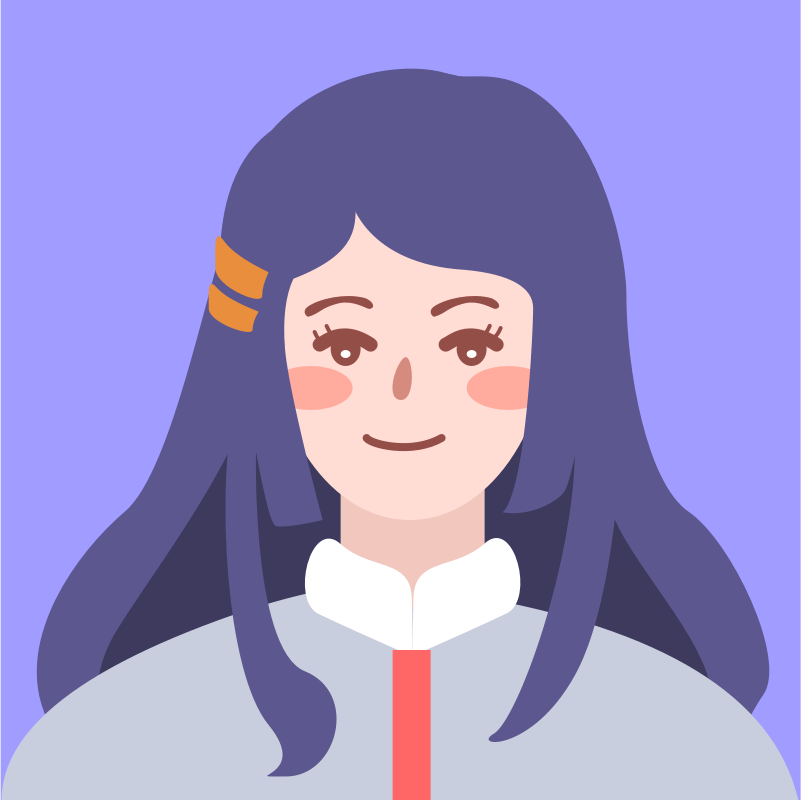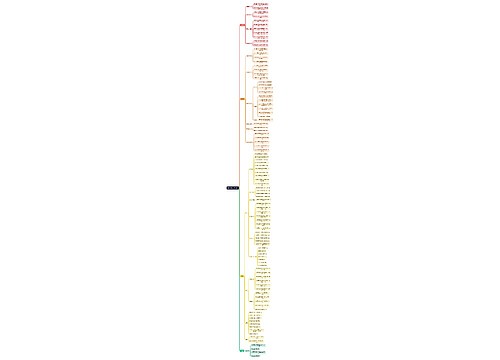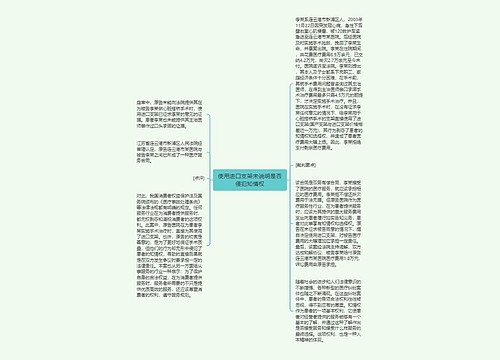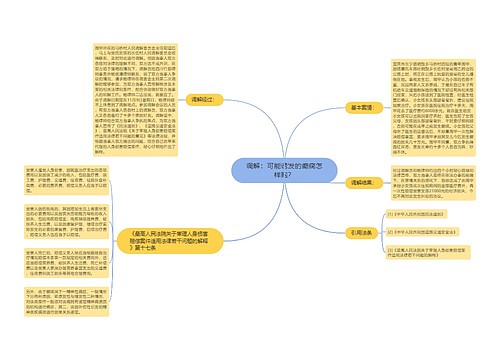关于不当出生之诉的概念,虽然表述各异,但基本上可以界定为“产妇在孕期到医疗机构进行产前胎儿健康检查,医疗机构未能发现异常,后产妇产下先天缺陷的婴儿,婴儿或其父母与医疗机构产生纠纷,向法院提起的诉讼”。
其实有关不当出生的纠纷,国外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经出现,并引起过法律界的争议。在美国实务中,因此而主张的此类索赔案通常被概括为“不当生命”之诉,即一个因被告过失生而具遗传缺陷的孩子所提出的诉讼请求。由孩子父母提起的该主张通常被冠以“不当出生”的称呼,这是由于被告的过失而致父母生出了一个具遗传病或其他先天缺陷的孩子,而为该父母所提起的诉讼。当然,也有法庭反对以上称谓。如审理Viccaro v. Milunsky(VICCARO V. Milunsky,Supreme Judicial Court of Massachusetts,1990.406 Mass.777,551 N.E.2d.)案的法庭认为,这些称谓并不具指导性。任何“非法性”不在于生命、出生、妊娠或怀孕本身,而在于医生的过失。如果有损害的话,也并非出生本身,而是由于医生的过失使父母得以决定是否生育一个孩子,或是否生育一个有遗传病或其他缺陷孩子的权利受到否定,从而给其带来身体、感情以及财状况上的不利影响。法庭主张应避免使用诸如“不当生命”、“不当出生”或“不当怀孕”之类的称谓。
在美国,承认“不当出生”的诉因是相对近期的成就。曾一度阻碍着这一诉因的是新泽西州最高法院审理的Gleitman v.Cosgrove[1]案中引起争议。这一案件中法庭判决被告不承担责任,理由之一是损害计算上的困难。为了决定对该案父母的损害赔偿数额,一个法官不得不估算基于成为父母而生的无形、不可计算、复杂的利益并将其与诉请的感情及金钱上的伤害相权衡。理由之二是,即使堕胎被实施而未触及刑事法律,在政策上仍禁止就拒绝获得怀孕机会所进行的侵权损害赔偿。但新泽西州法庭在Cleitman案判决12年后,声明仅仅因为损失难以精确计算便拒绝对父母伤害的赔偿是对司法基本原则的曲解。其他法院同样发觉对不同损害计算上的困难并非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这样,一度被认为在否决“不当出生”诉讼案中具说服力的理由逐渐失去了潜力。
欧洲侵权法不承认美国普通法中出现的上述“不当出生”的称谓。两条基本规则概括了欧洲的共同观点。其一,任何人都无权决定自己之不生存,这已被普遍接受。所以一个人被孕育或者堕胎这一事实不能对那个人构成一个诉因。同样,如果明知存在孕育或遗传方面的缺陷,但忽视这种影响而导致出生的孩子严重残障,也不构成一个诉因。第二,将一个残障的孩子在法律上与缺陷产品同等对待是对人格尊严的严重侵害。
新中国成立后,医疗事故纠纷的处理程序繁琐,特别是1987年《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实施,将医疗事故鉴定作为医疗纠纷诉讼的前置程序,没有进行医疗事故鉴定,直接到法院提起医疗纠纷诉讼,法院不予立案。直到本世纪初最高人民法院明确了意见,不经过医疗事故鉴定同样可以到法院起诉。但时至今日,在某些法院对此类案件仍然不予受理。2002年10月1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正式实施后,医疗纠纷开始出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医疗纠纷的立案在法律上已经没有障碍。只要患方提供了证明存在医患关系和患者损害后果的基本证据,法院即应予以立案受理。但“不当出生”之诉还是一个新事物,实践中并没有作为一个单独的案由,而是作为普通的医疗纠纷和其他案件一样进行立案。对于患方的诉讼请求是否予以支持以及支持的范围,更是众说纷纭,没有统一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