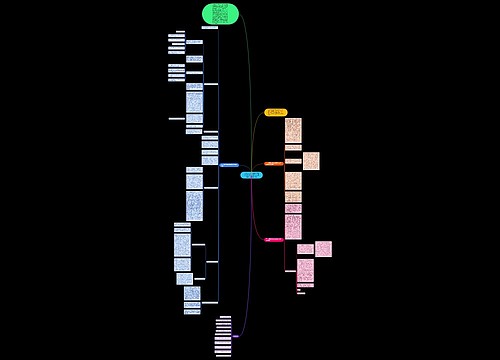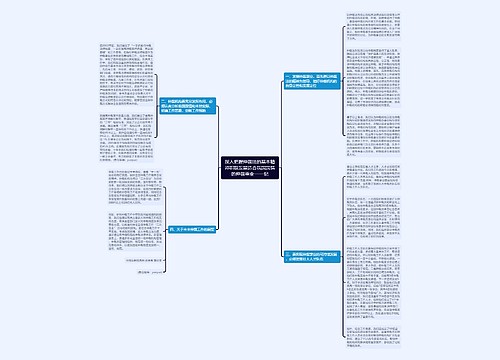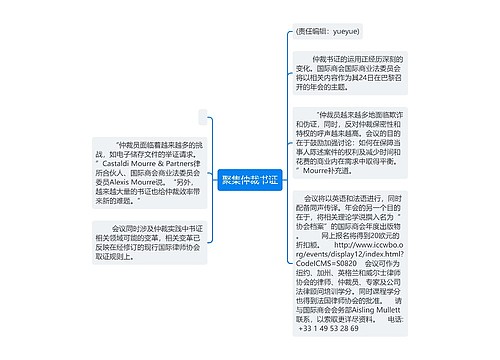纵观各国的仲裁立法,把仲裁机构的约定作为仲裁协议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是罕见的。一般来说,各国法律除对仲裁协议采用书面形式外,对仲裁协议的内容只强调其应表明当事人提交仲裁解决争议的意愿。例如,澳大利亚关于仲裁协议的要求就是仲裁协议应是书面的,只要将争议提交仲裁解决的意愿是明确的,仲裁协议便是有效的。比利时的《司法法典》第1677条规定:“仲裁协议应当由表明其仲裁意愿的经当事人签署的书面文件或其他对当事人有约束力的文件构成。”在法国,依其《民事诉讼法》第 144条的规定,仲裁协议的有效要件是:仲裁协议应为书面形式;仲裁协议中指定了仲裁员或约定了指定仲裁员的方式,如果仲裁协议关联到仲裁机构则另当别论。在判例法中,如果当事人实际参加了仲裁程序,视当事人以参加仲裁的行为有效地取代了无效的仲裁协议,仲裁是有效的。依《日本民事诉讼法》第786条规定,在当事人有权提交解决的争议的范围内,将争议提交一名或数名仲裁员解决的仲裁协议是有效的。日本法对仲裁协议的形式和内容没有规定具体的要求。美国 1950年《仲裁法》第32条规定,仲裁协议是指将现有争议或未来争议提交仲裁的书面协议,无论该仲裁协议中是否指定了仲裁员。(责任编辑:yueyue)
已有100多个国家加入的《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1958年在美国纽约签订,统称纽约公约)第二条一款规定,当事人以书面协定承允彼此间所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一切或任何争议,如涉及可以仲裁解决事项确定的法律关系,不论其契约性质如何,提交仲裁时,各缔约国应承认此项协定。纽约公约在关于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条款中列出了四项理由,其中之一为仲裁协议无效。按照纽约公约的规定,仲裁协议的双方当事人,根据对他们适用的法律,当时是处于某种无行为能力的状态下;或者根据双方当事人选定适用的法律,或在没有这种选定的时候,根据裁决作出地国的法律,仲裁协议是无效的,被请求承认和执行裁决的主管机关,可根据反对裁决当事人的请求,拒绝承认和执行该项裁决。不难看出,纽约公约本身所规定的关于仲裁协议有效性的认定标准有五条:1、仲裁协议是否采用了书面形式;2、协议是否表明了提请仲裁解决争议的意愿;3、仲裁协议中约定提请仲裁解决的争议事项是否属于可仲裁事项;4、当事人是否具有行为能力;5、根据可适用的法律,仲裁协议是否属于无效协议,而该第5条标准正是与本文讨论有关的问题。
如前所述,各国仲裁法多没有把仲裁机构的约定作为仲裁协议的一项有效要件,纽约公约也没有直接作出这种规定。而我国仲裁法中之所以作出这种规定,也许是在立法过程中,立法机关对临时仲裁尚不予认可或不想认可,而仅仅认可仲裁机构。所谓临时仲裁,是指不要常设仲裁机构的协助,直接由当事人指定的仲裁员组成仲裁庭进行的仲裁。仲裁庭处理完毕案件即自动解散。那么,在当事人约定以临时仲裁方式解决争议的情况下,临时仲裁协议中自然不会约定仲裁机构。显然,依照我国仲裁法的规定,由于临时仲裁协议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临时仲裁协议将无一例外地被认定为无效仲裁协议,除非双方当事人另就仲裁机构达成补充协议。换而言之,由于我国仲裁法没有对临时仲裁作出任何规定,加上仲裁法把仲裁机构的约定作为认定仲裁协议有效性的一项要件,所以可以说,在法律上,我国现行仲裁法对临时仲裁协议的有效性是不予认可的。
在经济文化往来如此广泛频繁、交通通讯如此迅捷发达的当今世界,各国的立法对当事人在经济交往中所表现出的共同意思或意愿普遍予以尊重和重视。这种尊重和重视体现在对当事人订立的合同条款,对当事人选择的可适用的法律、对当事人选择的解决争议的方式等诸多方面。当事人约定通过临时仲裁方式解决争议,在国际上已得到普遍的尊重。从各国立法实践看,大多数国家的仲裁法都不否定临时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在司法实践中,也都认可临时仲裁,承认临时仲裁协议的有效性。除非由于当事人的原因,临时仲裁协议是不可执行的。有的国家甚至在临时仲裁协议不可执行的情况下,仍通过法院以司法补救的方式使其成为可执行的协议。
此外,对以下问题应予以充分注意:
(一)纽约公约中所指的外国仲裁裁决以及我国与一些国家签订的双边司法协助协定中所指的仲裁裁决并非排除了临时仲裁裁决,而是既包括机构仲裁裁决,又包括临时仲裁裁决。纽约公约和这些双边司法协助协定都是既适用于机构仲裁裁决,也适用于临时仲裁裁决。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以下情况:面对同一项临时仲裁协议,一方当事人在我国大陆境外某地区或某国家(该地区或国家适用纽约公约或与我国签订司法协助协定)提起仲裁,该地区或国家是认可临时仲裁协议效力的,在该地区或国家所组成的仲裁裁决绝不会因仲裁协议中无仲裁机构的约定而被认定为无效,更不会因此否定仲裁协议的效力而不允许进行仲裁,也不会因此认定已进行的仲裁为非法仲裁而否定其裁决的效力。只要原程序符合有关公约或协定的要求,当事人到我国大陆境内申请执行在该地区或国家据该临时仲裁协议作出的裁决,我国法院是没有理由不予执行的(尽管作为裁决执行地法的我国法律不承认临时仲裁协议的效力)。否则,就是违反了本国在公约或协定中承担的条约义务;相反,如果一方当事人在我国大陆境内据该同一临时仲裁协议提请仲裁,则会因现行法律规定,不能提请仲裁,从根本上失去了据该仲裁协议作出裁决后到境外去申请强制执行的可能性。退一步讲,即使依临时仲裁协议在我国境内作出了裁决,也可以依据作为裁决作出地的我国法律规定,在我国法院或境外法院从否定临时仲裁协议效力的角度否定裁决的有效性。这种状况客观上形成了作为公约或协定缔结国的我国与承认临时仲裁协议的他国之间的不对等,对双方当事人也是极为不公平的。 (责任编辑:yueyue)
(二)由于仲裁所具有的当事人意思自治性、民间性、准司法性等特点,加之纽约公约的缔结国至今已有100多个国家,仲裁裁决在外国的执行情况是相当好的。而法院的判决要想在境外得到执行,由于没有全球性的公约可适用和法院属国家权力机关等多方面的原因,则要困难得多。我国现行仲裁法不认可临时仲裁协议的效力,客观上将迫使当事人不得不放弃临时仲裁协议的约定而诉诸法院,而通过法院最终作出了判决如需到境外执行,会困难重重,很可能无法得到强制执行。其结果是功亏一篑,判决书成为一纸空文,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最终实现。相反,如果尊重当事人仲裁的意愿,承认临时仲裁协议的效力,当事人的正当权益通过仲裁方式也许完全可以顺利实现,或者说,实现的可能性会大得多。实践表明,当事人在交易中,尤其在涉外交易中,之所以选择仲裁方式解决双方之间的争议,往往是出于多种考虑,除了仲裁员可以由当事人选择,仲裁的气氛比较宽松,仲裁的不公开性,仲裁裁决具有终局性等考虑外,仲裁裁决在境外便于得到承认和执行也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因素。如果在立法时忽视当事人的这一重要考虑,对当今世界仲裁的发展趋势和惯常做法缺少必要了解,对中国与世界各国经济往来的广泛性、密切性和不可分割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争议解决方式的利害相关性认识不足,那么,所制定的法律条款就难免有违立法初衷,无助于维护当事人的权益。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仲裁法没有必要将仲裁机构的约定作为仲裁协议是否有效的一项要件。在解释仲裁协议是否有效问题上,包括临时仲裁协议是否具有可执行性问题上,应留有必要的弹性和余地,使得那些虽未约定仲裁机构,但可以执行的仲裁协议得到执行。这样做,有利于在尊重双方当事人意愿的基础上解决有关争议,有利于促进和支持仲裁的发展,创造更良好的法制和投资环境,同时也较符合国际上的通常作法,有利于准确合理地适用有关国际公约或协定,增进经济交往。

 U682687144
U682687144
 U633687664
U6336876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