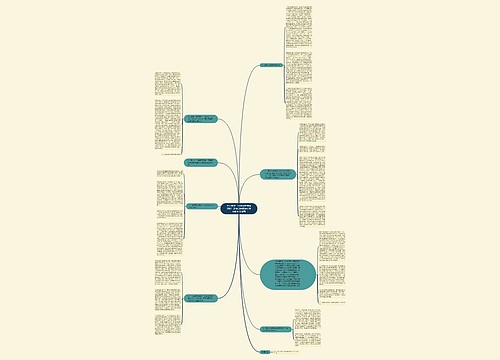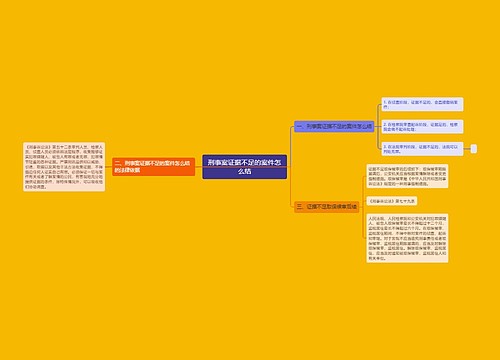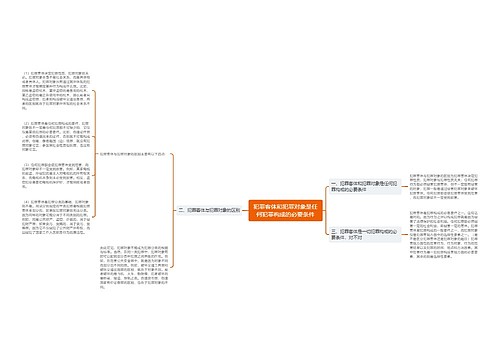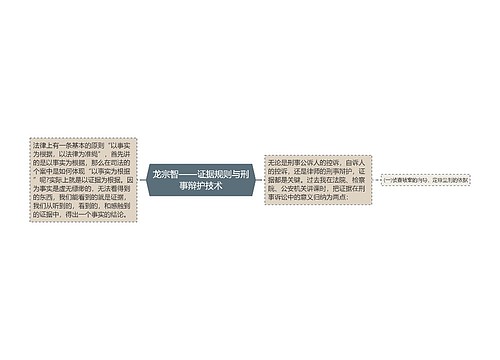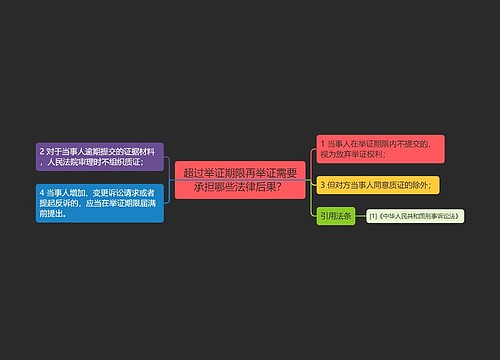起草证据法,首先要明确什么是证据,是否必须在法律中写出证据的概念。建议稿第3条写道:“凡当事人提出的用于证明或者有助于证明本方提出的关于事实的主张的材料,都是证据。”笔者认为,这个定义是不完整的。
在中国,证据不仅是当事人提出的,法院也可以依法收集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侦查机关也应当依法收集证据,而法院和侦查机关都不是当事人。
这个定义称证据是“材料”,这不能包括各种证据形态。我们知道,证据根据形态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为有形的,通常称为“物证”(tangibleevidence或physicalevidence),第二类为无形的,称为言词证据(testimony),包括证人证言和被告人的陈述。我们平常理解的“材料”,通常是一种有形的物质,不包括未形成文字的陈述。中国现在的“证人证言”和被告人陈述,通常是在审判之前所作陈述形成的书面文字,[1]这当然可以称为“材料”,但是,根据联合国的刑事司法国际准则,被告人有权当面与证人对质[2],这种在法庭上的对质本身就起到了证据作用,但这种对质显然不是“材料”。
这个定义可能来源于《布莱克法律字典》(BLACK‘SLAWDICTORY)。该词典证据(evidence)条第一句话说:“Anyspeciesofproof.orprobativematter,legallypresentedatthetrialoranissue,bytheactofthepartiesandthroughthemediumofwitnesses,recorded,documents,exhibits,concreteobjects,etc.,forthepurposeofinducingbeliefinthemindsofthecourtorjuryastotheircontention.”[3]译为中文可能是这样的:“由当事人提出的、以及通过以证人、记录、展示、和感知的任何证明的种类或证明材料”是证据。
但是,该词典接着还写道:“Testimony,writings,materialobjects,orotherthingspresentedtothesensesthatareofferedtoprovetheexistenceornonexistenceofafact.”笔者试译如下:“为了证明某件事情存在或不存在,而提出来让人感知的证人证言、书写物、材料或其他东西,”是证据。
该词典接下来还写道:“Allthemeansbywhichanyallegedmatteroffact,thetruthofwhichissubmittedtoinvestigation,isestablishedordisproved.Anymatteroffact,theeffect,tendency,ordesignofwhichistoproduceinthemindapersuasionoftheexistenceornonexistenceofsomematteroffact.Thatwhichdemonstrates,makesclear,orascertainsthetruthoftheveryfactorpointinissue,eitherontheonesideorontheother.Thatwhichtendstoproduceconvictioninthemindastoexistenceofafact.Themeanssanctionedbylawofascertaininginajudicialproceedingthetruthrespectingaquestionoffact.”这一段虽然比较长,但因为对理解何谓“证据”很重要,笔者再试译如下:“一切用于确立或否定提交侦查的任何声称的事情的真实性的方式。任何事项、意图或设想其被提出之目的是用于使人相信某事件存在或不存在,表明、澄清和肯定某事项,或某事项的任何一个方面,试图使人相信犯罪事实存在。法律所规定的用于在司法程序中确认某事项真实性的方式。”
这个定义确实比较长,而且文字很不好译,但我以为大意是不错的,反映了证据的含义。《建议稿》的作者可能怕麻烦,或认为太累赘,只取了其中一个意思。笔者认为,如果是这样,不如不写证据的定义,西方许多国家的证据法并不写证据定义;如果写了就应当写得全面,否则,该定义不能包含的事项就可能被排除在证据之外。证据其实就是证明的根据。这个问题在我国有关法律中一直有些不明白的地方。我国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31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该法还称证据有下列六种:“(一)物证、书证;(二)证人证言;(三)被害人陈述;(四)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五)鉴定结论;(六)勘验、检察笔录。”
证据本身可能是事实,可能不是事实。任何证据,都可能是虚假的,或部分错误的,这才需要对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如果宣称证据是事实,何必再审查判断?
也许立法者的本意是:已经审查判断过并被采纳的证据是事实。其实也不能这样说,已经审查判断过的证据也可能是虚假的,否则对证据和案件事实问题就没有上诉的余地。
采取列举的方法将证据限定为六种,更是形式主义的表现。世界上的事物是无限的,不确定的无数人,包括现在人和后来人的认识能力也是无限的,而某个时期某些确定的人们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怎么可以用当时立法者的认识程度限制无限的证据形态呢?这无疑将许多证据排除在证据之外。例如,该列举中有关被告人的证据只有“供述和辩解”两种形式,这两种都是言词性质的,从而把被告人的行为排除在证据之外。设想如果被告人用点头、摇头对某事项的某一个细节表示承认或不承认,这是否应当作为证据?这又是何种证据?
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42条照搬了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31条,只是在“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之前加上了“犯罪嫌疑人”,还加上了“视听资料”。但这个证据定义的缺陷问题依然存在,改进部分只是五十步和百步的关系。
证据按其形态可以分为有形的证据的证据和无形的证据,所谓有形的证据,是人们可以用视觉和触觉看见或触摸到的证据;所谓无形的证据,是人们不能以视觉和触觉感知,而必须以其他方式感知的证据。没有必要将其限定在六种或七种,事实上也是无限的。在这一点上《建议稿》有所改进,其中第四条列举了八种证据,并且说明,不限于这八种。既然如此,不如不列,法律条文贵在精确,不必画蛇添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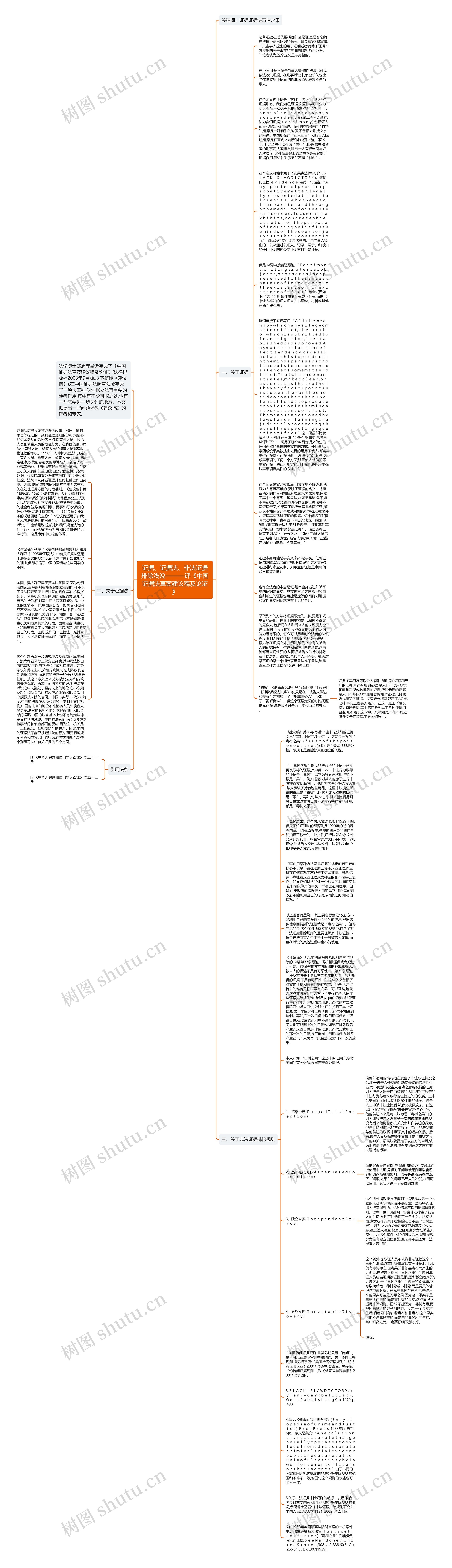
 U682687144
U682687144
 U633687664
U6336876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