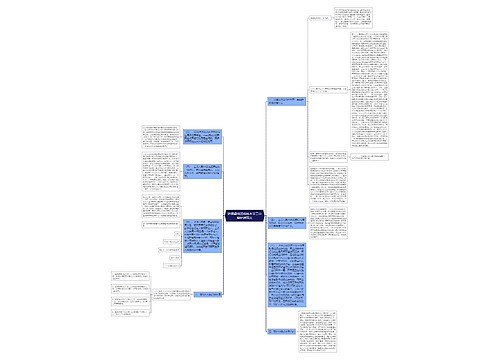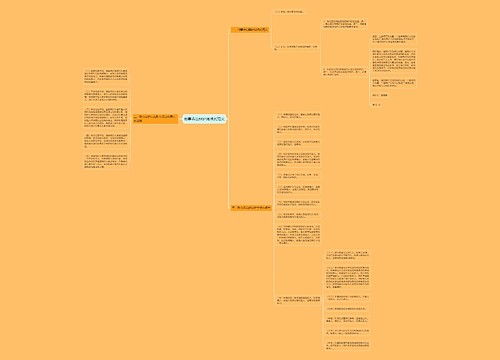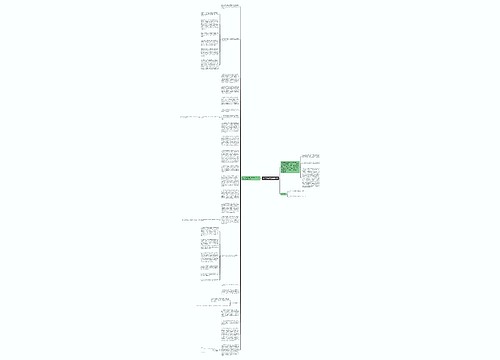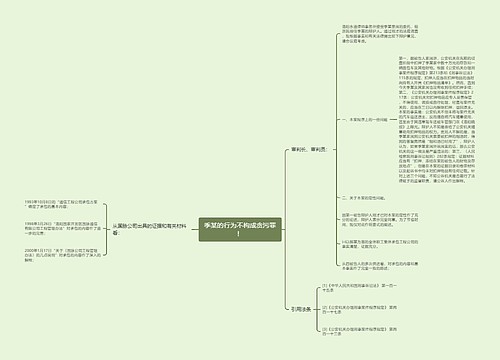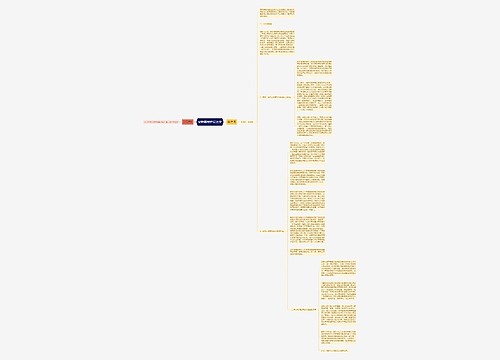涉嫌受贿案一审辩护词范本思维导图
感情愚钝
2023-03-09

辩护
一审
受贿
涉嫌
证据
被告人
证人
指控
证实
刑法
刑事辩护代理
辩护词
受贿罪辩护词
受贿罪辩护词格式范本是怎样的?下面树图网小编为您详细介绍涉嫌受贿案一审辩护词范本,仅供参考。
树图思维导图提供《涉嫌受贿案一审辩护词范本》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涉嫌受贿案一审辩护词范本》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e642402b2a333e13a211de4b3e1b2e10
思维导图大纲
相关思维导图模版
涉嫌受贿案一审辩护词范本思维导图模板大纲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我作为被告人杨多铭的一审辩护人,今天第二次出席法庭,为被告人杨多铭进行辩护。
通过两次开庭参加的法庭调查、举证、质证以及听取公诉人的公诉意见。我们更加坚信了在第一次开庭时对本案提出的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指控罪名不成立的辩护观点的正确性。相关事实和理由如下:
一、关于本案的证据体系
根据两次庭审的综合情况看,公诉机关为支持起诉,在事实方面,组织了包括被告人供述+证人(言词)证言+(谋利)客观证据相呼应的证据系统。然而,根据庭审质证以及查明的事实,控方的这一证据体系存在重大瑕疵,根本不符合刑事证据“三性”的基本要求。集中体现在:
首先,就被告人供述而言,从庭审调查证实,被告的供述只限于其刑事立案前的“双规”期间写有数份“交待材料”。材料中虽然曾承认收到了指控的钱财,但其在刑事立案以后的长期申辩以及法院根据辩护人的申请依法委托技术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证实并不是被告人真实意思表示。
1、被告人刑事立案前的自书“交待材料”属证据来源不合法依法不能作为刑事证据使用
根据被告人的当庭陈述,是被告人面对纪委工作人员的“教育”…“引导”,抱着重病的身体,抱着既不敢得罪纪委工作人员,又担心无原则的满足其工作人员的要求书写“交待”,将来一旦不按承诺兑现 “党纪、政纪处理”而形成自证其罪的刑事证据的特殊情况下,以无奈之举违心形成的产物。被告人在案前自书“交待材料”中留有无奈的痕迹是无奈的,再庭审中道破它是痛苦的。难道身处正厅级的被告人懂得这样做会得罪相关机构吗?他知道!他如果不懂得就不会步步后退直至退到了法庭辩论的最后阶段才说出真相?这就是公诉人在第一次开庭发言时疑问于被告人为什么不向公诉机关说明的原因。他没有在侦查、审查起诉、起诉阶段向检察机关说明不是不相信检察机关;而是在痛苦的身心折磨过程中坚守着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可以将有损组织形象的“秘密”公诸于众的信念!在法庭辩论的发言最后他倒出了这一“秘密”,那是无奈之上的无奈之举,因为,给他保密的机会已经完全用尽了。而倒出这一“秘密”他不仅不像本律师想象的应当轻松,相反的再庭后会见时得知,他感觉的更加痛苦,甚至后悔倒出了这一唯一可能洗刷自己清白的不应公开的残酷事实。
当然,我们大可忽略不计鉴定结果,退步而言,就算被告人自书的“交待材料”上没有其密写的痕迹,单从书写内容中涉及案件关键事实比如时间、钱的数额、钱的包装物等重要情节的描述上均各不相同之处,从形式上多处标注有“被教育…”等隐含无奈的文字表述以及结合控方在钱的来源、给付、谋利等方面的矛盾判断,其所谓的“供述”材料也不能完整的证明案件指控事实。更何况行为人在特定的环境中,在万般无奈的情势下以密写的方式注明的材料形成真实原因依法得到了科学检验的证实。
据此,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对该法的司法解释第六十一条之规定,被告人在刑事立案前所写材料以及建立在以此为基础之上的问话记录当然不能作为本案定罪的证据使用。从而,本案事实上形成了本案公诉机关证据系统中没有的被告人供述的适格证据。
2、刑事立案后被告人没有自证其罪的供述
而2005年2月5日被告人被刑事立案并宣布逮捕后至一审法庭,其在一直坚持纠正原来的不实“交待”的同时,始终否认收到过指控的钱财,从不同角度反复申辩没有任何亵渎权利的行为。就此得到了侦查机关、审查起诉、起诉阶段公诉机关先后数次问话记录充分的证实。
也就是说,被告人不仅在被刑事立案前没有自证其罪的供述,立案后更没有这方面的供述,此列证据显然不能支持起诉。
其二,就证人证言来看
按照公诉人的说法,此案即便是“零口供”起诉指控亦完全成立。而对此说法,本案中,在起诉之前就已经出现了。那么是什么样的证据在支持着这一明显有罪推定的控方断言呢?如果说在第一次开庭审理之前,有关部门将证据着眼点包含了被告人自书材料的话尚可以理解,因为此前没有人或都不愿意对“双规”期间形成的自书材料提出质疑。而此案经过第一次开庭后,尤其是今天二次复审法庭出示的科学鉴定结论完全否定了被告人自书材料的刑事证据价值后,恐怕『“零口供”也完全可以对被告人定罪』的说法就失去了最起码的证据基础;道理很简单,因为公诉证据根本不能支持对被告人的有罪指控。
◆就指控第一项因吴昌考案件收受11万的证人证言来看
1、指控第1笔――证人证言是否能够证明在跨世纪酒店被告人收受了包军给予的1万元?
对此,主要证据卷P95-97 2005、元、11黎华自书与包送杨钱经过中的/15-18证实:“2000、7说好送1万…由我做掩护…买完酒后回到车上包军从提包拿出1万元放进一个牛皮纸信封…”;而就同一事实,主要证据卷P69包军证实:“买好礼物后回到房间,我要准备出发到跨世纪大酒楼吃饭前……”P68/末1-2“是用桃园饭店的信封装好(1万元)… ”/P69-1。
2、指控第2笔――在梧州五丰大酒店证人证言是否能够证明被告人收受了包军给予的5万元?
3、指控第3笔――在北京邮电大厦证人证言是否能够证明被告人收受了包军给予的5万元?
对此,主要证据卷P90/末行黎华证实“包送杨5万时不在场,但我们回到邮电大厦房间时,(我和包同住)(P91/1-2 )包说“已经搞惦了…5万元人民币已送给杨多铭了…”。而就同一事实,主要证据卷P78包军在证实:在北京送给被告人5万元没有人在场的同时,对何时将次事告知黎华作证为“在王府井(买单时)将送杨5万事告诉了黎,没说具体数额。”同时,包、黎二人证实被告在邮电大厦只住了一个晚上。
而P99-111李应剑2005、3、21证实:P107 “…11月份包、黎去京看杨、饭后到邮电大厦,我和我女儿住一间”(倒3行)而P86/17-18 黎华 2005、3、17证实“当晚李应钊在我和包军住的房间加了一个铺位”,同时证明“被告人在邮电大厦住了两个晚上,次日陪逛王府井后的第二晚…我见包进了杨房间,包出来说“OK了,搞惦了…”
三个证人证言在给钱的时间、日期及去王府井时间甚至被告人究竟在邮电大厦住几个晚上等重要情节上,说法均各自不同,根本不能相互印证。
综合以上控方言词证据,就其指控第一项被告人杨多铭收受了指控的11万元而言,面对钱的包装物、钱的来源、钱给付时间等重要情节证人各自不同的说法,面对如此重大疑点,公诉人可以视而不见。坚持自己的指控主张是公诉人的权利;但当我们理解到公诉人的这一坚持是施罪过于被告人时,那么就有理由要求公诉人必须用你自己的证据来向法庭说明和排除上列重大证词疑点。因为经过两次法庭调查,在公诉人已经完成了的法庭举证、质证过程中,被告人、辩护人、旁听群众、甚至包括审理此案的合议庭成员,都没有看到控方有任何形式的证据排除或解决证人证言之间的上列重大分歧。
从而足以说明,证人证言不能支持对被告人的该项犯罪指控。
就指控第二项收受周某某3万元的证人证言来看
根据公诉人的举证,本项指控收钱事实的认定,共有两个证人,其中之一是在主要证据卷P196/17-18周建成2005、元、10 证实:“邝提出应意思一下,我问1、2总可以了吧,他说“不行,起码要2.3万”…”;显然,周的证言对犯意所指是另一证人邝云升。而就该问题,在主要证据卷P198-190 邝云升2005、元、15自书材料中证实(P198 )“…2001年中秋节…周提出让邝见杨时帮讲话,给邝一信封托其带给杨…中午…见杨…谈了周任用之事,临走放信封于茶几称“周建成叫我转给你的东西”。P198/末4 “信封是周封好的…具体多少钱不清楚,凭手感我估计约2万元…”
那么,如果认定被告人受到了该3万元且构成受贿罪,公诉机关必须通过有效的证据首先证明到底是谁提出的犯意?又究竟是多少数额?证人证言说法各异,到底是两万还是三万?连最起码的数额都没有搞清楚就以重罪而指控一个法院系统高级领导干部,显然过于草率。仅以邝云升的一句“凭手感我估计约2万元”之孤证就诉请法院认定被告人收受了3万元构成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即使公诉机关敢于承担错诉的责任,恐怕法院很难承担对一个厅级领导干部的错判后果。道理很清楚,不是官官相护;而是明显没有证据支持。
就指控第三项收受4.5万元的证人证言来看
1、第1笔2000年3、4月间的5000元究竟是什么时间?数额是多少?经手人究竟是给谁证人间说法各异。
2、第2笔2000年5月的1万元的给付地点以及钱的来源、数额证人证言含糊不清。
3、第3笔、第4、5笔各1万元数额究竟是多少?经手人是谁?给钱时间、地点及情景究竟是怎么样证人证言说法不同,钱的来源不清不楚(对此,钟律师将做证人证言的详细比对阐述)。
综合以上公诉机关举证的证人证言对此案重要情节的证明结果,证人证言对涉及确认请托人是否对被告人给付金钱事实的重要情节相互矛盾,根本不能相互印证。
其三,从其它相关证据上看:
经庭审调查表明,涉及本案的其它相关证据除主体及程序证据外,主要是被告人亵渎权利、为请托人施以“关照”类的证据,其中包括了:
1、广西高院对吴昌考案件由无期改判为十年的二审审判相关书证及证人证言。证据证明,本案被告人在吴昌考案件二审中,曾以主管副院长的身份阻止了合议庭第一次上报的“拟改判吴昌考缓刑”的合议庭意见,并明确坚持了其受贿罪应当定罪、处罚。而从法律上看,根据对吴犯罪情节,数额的确定,数罪量刑后合并执行其十年没有突破法定最低刑的界限,结合该案涉及“八达公司”的股东背景、承包关系等重要情节,这一处理是比较恰当的,根本体现不到任何对其施以“关照”的成分。
2、与此直接相关的公诉机关已经调取并举证的2003年5月24日广西高法以(2001)桂刑监字第8号驳回吴昌考申诉通知书以及相关审委会对此案的讨论记录等证据。
在这一组证据中,本辩护人丝毫看不到被告人给予了请托人什么“关照”;在审监庭提出的对吴昌考案拟“撤销原判、改判无罪”的情况下,证据证实的完全是被告人用刚正不阿,不畏权势,为了捍卫法律的尊严将可能招致报复置于身外,秉公办案的高风亮节。通过证据看到是身为高级法院副院长的被告人,三年前二审中推翻了请托人可能枉法得到的缓刑机会,三年后,再次阻止了其改判无罪的“艰苦努力”。进而看到的是今天此案案发的重要原因不是因为其他,正是来源于由于被告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对,吴昌考案在改判缓刑不能,在改判无罪更不能如愿之后,将盛怒归责于身为高级法院主管刑事审判工作的被告人杨多铭,开始了对被告人无休止的所谓“检举”而引发。
3、其它证据之高院对周某任用的相关材料,在本组证据中,本辩护人想提请合议庭注意的是,证据显示,不仅任用周某的程序完全正常,更为重要的是综合评定及提出任用意见的是高院政治部。同时,证据显示被告人除了在党组讨论时以一个主管副院长的身份提出同意的意见外,余无任何过问。
而在对经合法程序公开竞争名列在前,政治部综合考核同意并向党组提名推荐的干部任用问题上,作为主管领导据实表示同意显然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4、其它证据之钦州相关两个再审案件。公诉机关举证的两个再审案件反映出的是一个凭新的证据小有改判,一个是维持,完全是被告人正当履行工作义务。更何况证据显示,送钱的人竟包括了被告人明知而并不熟悉的银行纪检书记。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排除这些单位可能对中间人――控方证人邝云升给予了活动钱款,但中间人是否将钱款给了被告人则是我们在今天的案件中需要冷静思考、慎重确定的问题。对此,钟小慧律师将充分发表有针对性的分析意见。
综合以上,从公诉机关出示的认定被告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所列举的证据方面看,不仅不能证实被告人收了请托人的钱财;而相反的,反应出的不是职务犯罪的钱权交易,而是大公无私,不畏报复,依法秉公履行司法机关领导干部职责的客观事实。
二、关于指控涉案款项的来源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杨多铭共收受请托人18.5万元,而综合全案证据,证据不能证明指控认定款项的来源。
首先,就指控第一项被告人收受了11而言万元
1、证据不能证明包军从请托人方面取得资金的总额是27万元。对此,主要证据卷P123出钱人吴昌麟2005、元、18证实是“是25万元”;而收钱人包军P60-61 2000、6 等多次证实是“前后共给我27万元”。如果说收钱人出于因恶意占有而少报收取的数额似乎有情可说;然而出钱人硬是不承认多给了钱的奇怪现象不知公诉机关对此用什么证据做何解释?
2、就算是按请托人说的,证据也不能证明请托人所述给予包军25万元款项的真实来源。对此,首先是吴昌麟虽然在P123 证言中证实证实“第二笔(应为2000.6.7月)20万是向郑安仔借的(贺州个体),我写了借条给他”,但其同时证明:“到年底我与他人做生意赚些钱将借的20万还给了郑”;而就同一事实,主要证据卷P129郑安仔2005、元、19 证实:“吴案二审判决前,麟向其借20万(存折+现金+向陈振华借5万)――(/14)过了一年左右,吴昌麟将20万还给了我…”。
在第一次开庭时,本辩护人根据两个证人所证明的还款时间相差八个多月以及证人的说法没有借款凭证佐证,而对吴昌麟为此事是否向郑安仔借过钱提出了质疑?
事有巧合,在本案第一次开庭后,本律师投入经历承办由贵港市检察院侦查的原贺州市反贪局局长张建辉受贿一案中,该证人郑安仔又作为张建辉受贿一案的控方证人出现,其在2004年8月29日(对现在案件出证5个月之前)接受贵港市检察院反贪局调查时证实:为吴昌考的案件,吴昌麟等先后分数次向其“借款总额为15万元”(贵港市港南区检察院对张建辉起诉之主要证据卷P102),根本不存在此案中出证所说光因本案就一次性借给吴昌麟20万元的事实(相关证据本律师在刚才已经提交法庭)。
在这一基础上,综合考虑证人包军、黎华、李应钊证词证实包军曾两次否认收到过请托人钱的说法,对包军是否受到了请托人的钱财或如果有的话究竟是多少确实值得考究及慎重认定。
那么,公诉机关连请托人是否给了包军钱或者就算给了钱是否能够认定11万以上都没有搞清楚,所举证据连基本事实都不能证明的前提下就贸然的对被告人施以重罪起诉指控,是不是显得过于草率和不负责任了。
3、指控第二项3万元没有任何款项来源的证据;第三项4.5万元钱的来源之帐外凭证不仅数额不符,同时证据形式简单的让人匪夷所思。
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本案中,公诉机关的证据体系支离破碎。或根本没有,或自相矛盾,或证据来源不合法,在请托人是否给钱以及钱的来源、总额方面,在经手人是否给钱于被告人的给钱数额、时间、地点、包装物等重要情节上不能支持指控。在被告人是否收到钱以及是否给予了请托人帮助等定罪要件方面明显证据不足。
三、证人数量与证明效力
我们注意到,公诉人在两次开庭过程中始终以其证人数量达27人之多在说明其证据的充分与充实,我们还注意到,公诉人在两次开庭过程中始终以送钱经办人事先与他人协商,事后向他人通报送钱得手而否认本案实质上是“一对一”类贿赂犯罪案件的指控。对此,本辩护人认为,对学术上的、概念上的理解分歧、探讨是有益于丰富理论基础的,辩护人表示并不反对;但对案件的性质、对证据的质量决不能放纵不顾证据、不顾事实的夸夸其谈!因为证据的质量、对事实的认定不仅直接涉及司法形象,更重要的是直接涉及被告人的生死存亡。
因此,我们必须承认,证人数量不能决定证据质量,证据确凿与证人数量没有必然的联系。我们都不可以否认本案公诉机关的证据系列中没有可以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被告人供述,除包军外,没有证明被告人收到了他人给予指控认定现金的现场直接目击证人,没有足以说明被告为请托人施以了“关照”的充分证据的庭审客观事实。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尊敬的关注此案的机构、领导:作为被告人的辩护人,我期望公正的法院能够给予他以公正的判决结果。然而作为一名律师,我仍然要呼吁在反腐倡廉,净化干部队伍的同时,千万不可以忽视司法活动必须要依法保护干部。
综上所述,基于我们通过两次开庭越来越清晰的看到是公诉机关的证据不能支持指控,因此,出于对法律的尊重,出于对被告人基本人身权的尊重,我们除了仍然坚持认为公诉机关对被告人杨多铭构成受贿罪的起诉指控依法不能成立的辩护意见基础上,只能再一次的郑重建议一审法院,因证据不足,应对本案被告人杨多铭依法宣告被指控罪名不成立,以真正体现国家法律以及司法机关的严肃与公正。
上列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欧亚嘉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树国(签署)
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日
引用法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六十一条
查看更多
钟得成涉嫌受贿贪污罪一审辩护意见思维导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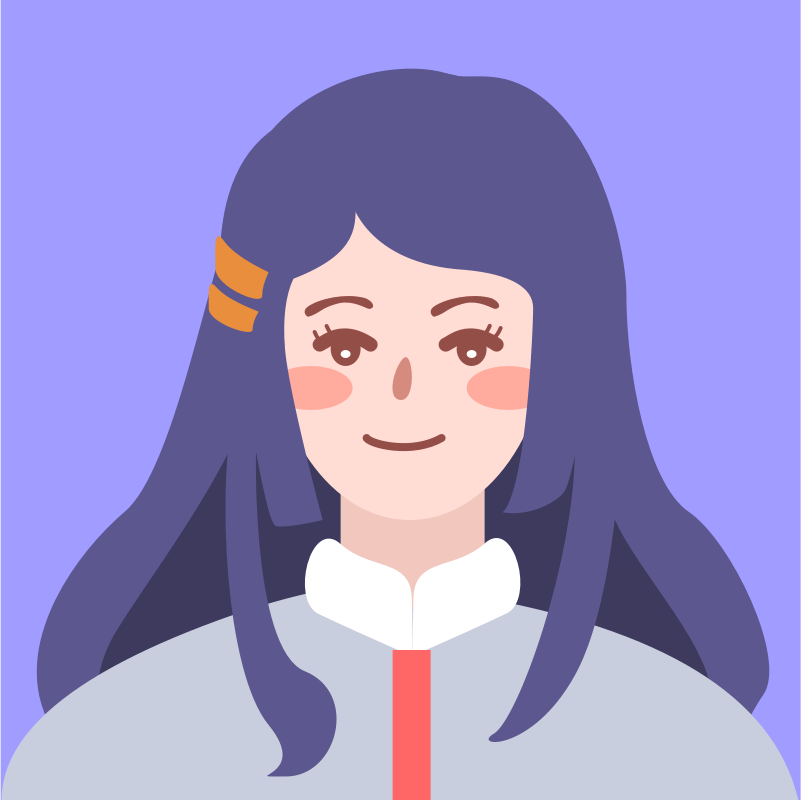 U853276520
U853276520树图思维导图提供《钟得成涉嫌受贿贪污罪一审辩护意见》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钟得成涉嫌受贿贪污罪一审辩护意见》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b23f22671a1941a2f95b905f91a946d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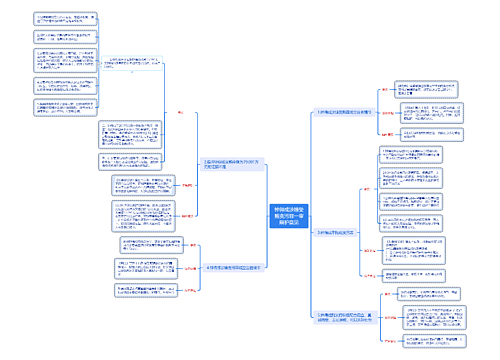
合同范本名称怎么标记(优选5篇)思维导图
 风雪夜人归
风雪夜人归树图思维导图提供《合同范本名称怎么标记(优选5篇)》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合同范本名称怎么标记(优选5篇)》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56e6d36afcb834e4ee1a184c857569e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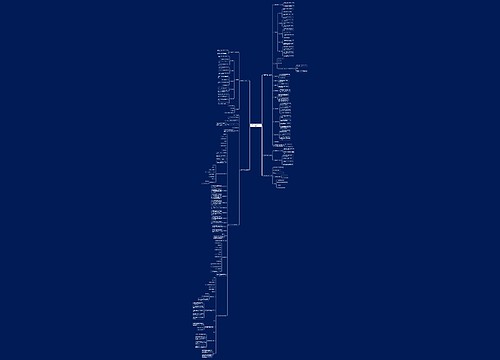
相似思维导图模版
首页
我的文件
我的团队
个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