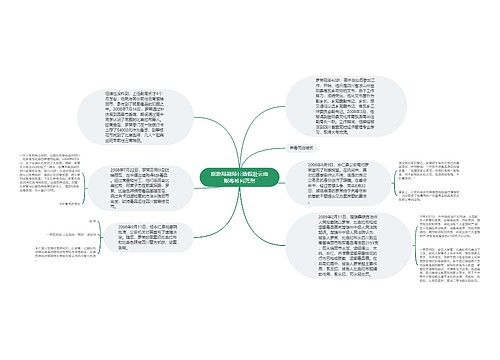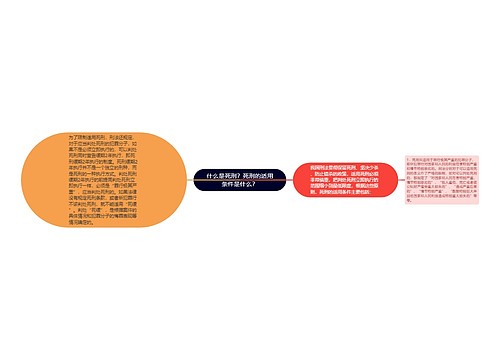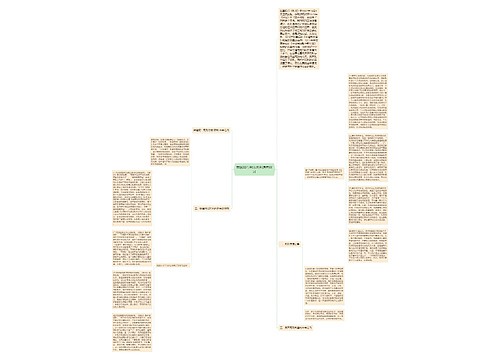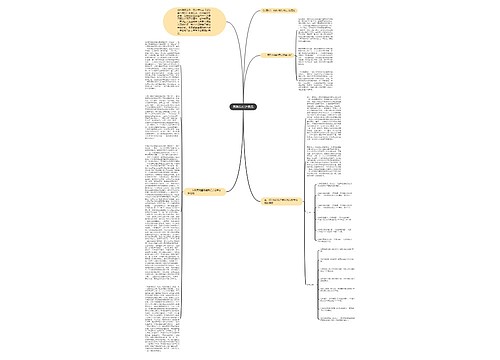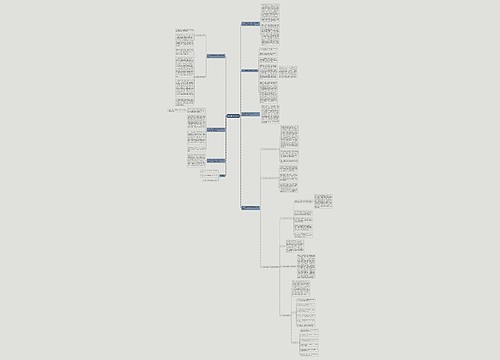试论死刑的存与废思维导图
草莓味的你
2023-03-08

死刑
刑罚
废除
功利
必要
预防
犯罪
保留
作为
卡利亚
刑法
刑罚种类
死刑
目 录
树图思维导图提供《试论死刑的存与废》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试论死刑的存与废》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baa4fdab1dae9543bd40b4ee710b6be8
思维导图大纲
相关思维导图模版
试论死刑的存与废思维导图模板大纲
一、 论文摘要••••••••••••••••••••••••••••••••••••••••••••1
二、试论死刑的存与废的正文••••••••••••••••••••••••••••••2
(一)死刑存废的历史之争••••••••••••••••••••••••••••••2
(二)死刑存废的功利之争••••••••••••••••••••••••••••••4
1、 死刑废除论的功利论基础••••••••••••••••••••••••4
(1) 伦理学的功利论基础••••••••••••••••••••••••••4
(2) 刑罚学的功利论基础••••••••••••••••••••••••••5
2、 死刑保留论的功利论基础••••••••••••••••••••••••6
(1) 伦理学的功利论基础••••••••••••••••••••••••••6
(2) 刑罚学的功利论基础••••••••••••••••••••••••••6
(三)死刑存废的人道之争•••••••••••••••••••••••••••••7
1、死刑废除论主要从以下三方面论证了死刑的非人道性••••••••7
(1) 死刑树立了野蛮的榜样••••••••••••••••••••••••7
(2) 死刑是野蛮时代复仇的遗风••••••••••••••••••••7
(3) 死刑助长人性的残忍••••••••••••••••••••••••••7
2、死刑保留论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论证了死刑的人道性••••••••8
(1) 死刑基于伦理正义的必然要求••••••••••••••••••8
(2) 死刑的适用是人道主义的要求••••••••••••••••••8
三、参考文献资料•••••••••••••••••••••••••••••••••••••••10
论文摘要
关于死刑的存与废,是世界各国刑法学界百年来争论不休的一个热门话题,近年来我国刑法学界对此已有所争议。本文对西方刑法史中对死刑存与废的功利之争和人道之争进行考察并进行粗浅的评价,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死刑 存废 刑罚 伦理
死刑,亦称生命刑、极刑,是以剥夺犯罪人的生命为内容的一种刑罚方法,也是最古老最严厉的一种刑罚。早在奴隶制国家产生的同时就产生了死刑,在之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死刑作为惩罚反对统治阶级行为的重要方法而存在,其执行的方法极端野蛮残酷。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一些资本主义启蒙运动思想家提出了废除死刑的主张。其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曾先后废除了死刑,但至今死刑仍然为世界上多数国家的立法所采用。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进程,死刑的存与废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是世界各国刑法学界百年来争论不休的一个热门话题。
一、死刑存废的历史之争
回顾死刑的发展史,我们不得不承认,死刑并非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更不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越来越发达的。相反,死刑作为人类从未开化时期继承下来的遗迹,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逐步走向没落或受规约之途的。马克思曾经清楚地揭示了死刑与原始社会以血复仇制度间的亲缘关系:“死刑是往古的以血还血、同态复仇的表现。”无数的传说和研究都证明,地球上的所有人种都在其发展的某一阶段依靠以血复仇制度。在人类原始社会里实行了几千年的以血复仇制度,也有过初期、盛期和终期之分。以血复仇制度的终结,便是作为国家刑罚制度的死刑的产生。自从死刑作为一种刑罚制度产生以来,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一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它是作为惩罚反对统治关系的行为的重要甚至是主要的刑罚方法存在的。公元前十八世纪古巴伦王国的汉穆拉比法典是保存至今奴隶制国家比较完整的一部成文法,其中死刑适用的范围广泛,直接处死的就有三十多条,而且处罚手段极其残酷,溺死、烧死、刺死、绞死是经常使用的。但是,自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提出了刑罚人道主义的思想后,死刑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开始受到了怀疑。率先对死刑予以全面抨击,并从理论上系统地提出废除死刑之主张的是被誉为“近代刑法之父”的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于1764年出版的《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贝卡利亚明确指出:“死刑并不是一种权利,我已经证明这是不可能的。”而且他认为:“用死刑来向人们证明法律的严峻是没有益处的。”贝卡利亚废除死刑的主张问世后,虽曾遭受到众多的异议,但拥护者也为数不少。法国哲学家伏尔泰曾满怀激情地接受贝卡利亚的学说,拥护其废除死刑的主张。英国著名伦理学家与法学家边沁则是废除死刑的杰出拥护者。他从功利主义的刑罚原理出发,首先假定一切刑罚都应该是预防犯罪的手段,据此提出重刑只有在能比轻刑收到更大的预防效果时才是正当的这一命题,在此基础上,他通过对死刑与终身监禁的优劣利弊进行对比分析,论证了死刑对犯罪的预防效果并不大于终身监禁的预防效果,从而得出了应该用终身监禁取代死刑的结论,形成了废止死刑的理论体系。应当说,贝卡利亚对于废除死刑的论证并非无懈可击。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就批评了贝卡利亚关于死刑不可能包括在最早的公民契约中、因为公民不会这样处置自己的生命的观点,认为贝卡利亚的这种说法完全是诡辩和对法的歪曲。德国另一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则从否定社会契约论出发,驳斥贝卡利亚的观点。黑格尔指出:“贝卡利亚否认国家有处死刑的权利,其理由,因为不能在社会契约论中包含着个人同意,听任他人把他处死;毋宁因该推定与此相反的情形。可是,国家根本不是一个契约,保护和保证作为单个人的个人的生命也未必就是国家的实体性的本质,反之,国家是比个人更高的东西,它甚至有权对这种生命财产本身提出要求,并要求其为国牺牲。”贝卡利亚与边沁对死刑的发难,宣告了作为一种系统的理论的死刑废除论的诞生。在此后的100多年中,他们的反对者众多,因而在死刑存废之争中二者的观点一直处于下风。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拥护者与日俱增。其中,以犯罪社会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菲利对废除死刑的拥护最为有力。在菲利看来,虽然死刑是公正的,而且,用死刑淘汰应当消除的反社会的和不适应社会的个人,并不违背适者生存、劣者淘汰的自然法则,但是,一方面,终身隔离或流放足以使社会免受犯罪人的再侵犯,死刑对于个别预防纯属多余;另一方面,死刑的适用量的增减与重罪率的升降的相关分析表明,其并未起到有效的一般威慑作用,因此,死刑对于一般预防也因是无效的而不是必要的。基于此,菲利认为,死刑是一种不必要的刑罚,因而主张以终身隔离或流放取代死刑。自此,在其发源地——意大利,死刑废除论在死刑存废之争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在英国,继边沁之后,主张废除死刑者也大有人在。著名法理学家哈特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哈特指出,死刑不只是给犯罪者本人而且给其他许多人造成痛苦;死刑之误判不可避免;为防止死刑误判而特设的审判程序扰乱了整个刑事审判体制,既加重国家的经济负担,又使公众对刑事审判产生不信任,因此,废除死刑理所当然。在日本,死刑废除论自问世至今也有一个世纪。泷川幸辰是最早系统地提出废除死刑的学者之一。他认为,死刑是野蛮时代的遗物;保留死刑不是民族确信;死刑不具有威慑力;20世纪的文化应该征服死刑这一野蛮时代的文明的最后抵抗者。
从死刑保留论方面来说,继早期保留论的代表康德、黑格尔、史蒂芬等之后,新派刑法学说的代表龙勃罗梭、加罗法洛等是主张保留死刑的最有力者。龙勃罗梭从保护社会不受侵犯的角度出发,认为有的犯罪人是不可矫治者,其存在不可避免地危及社会生存。对于此类危险性特大的犯罪人,只有动用死刑彻底剥夺其再犯罪的能力,才足以实现社会防卫的目的。在新派学者中,加罗法洛是主张保留死刑之最有力者,而且是从统计分析的结论中寻找保留死刑根据的第一人。他针对当时严格限制死刑的世界性趋势,以法国与意大利开始减少乃至废除死刑之适用后犯罪直线上升为例,证明死刑具有明显的一般预防功能。同时,针对贝卡利亚、边沁等提出的以终身监禁或流放取代死刑的主张,他提出,社会的发展已使罪犯不再存在使之与世隔绝的可流放之地,而且即使在终身监禁的情况下,罪犯也可能加害同监犯或监管人员,或者越狱脱逃。因此,死刑的彻底剥夺犯罪人的再犯能力功能是终身监禁所不可比拟的,唯有死刑才能使危险性极大的犯罪人永不再危害社会,实现社会防卫的目的。我认为,对西方刑法史上的死刑存废之争,可以从功利之争和人道之争两方面予以考察。
二、死刑存废的功利之争
(一)死刑废除论的功利论基础
1、伦理学的功利论基础
功利论的基本主张是,任何行为与制度,只有是有用的才是正当的。当某一行为或制度是作为实现某一目的的手段而存在时,其正当性便在于其对于实现该目的是有用的、必要的。如果该行为或制度包含有“恶”,那么,其正当性便不只在于其对于实现目的是有用的、必要的,而且还在于其所带来的合乎目的的“善”的余额,才可证明“恶”的正当性。不仅如此,当同时存在两种以上的“恶”可作为实现某一目的的手段时,如其所带来的“善”相同或相当,那么,只有最小的“恶”才具有作为手段的正当性。早期的死刑废除论者,无论是贝卡利亚、边沁、还是菲利,有关废除死刑的主张主要奠基于伦理学上的这种功利论之上。三者均因死刑剥夺人的生命而将其视为一种恶或代价,而将其所可能具有的合乎预防犯罪目的的作用作为一种善或收益,并立足于恶或代价与善或收益之间的轻重大小的权衡论证死刑的不正当性。其之所以均不否认死刑具有一般预防与个别预防的作用,但又均认为死刑是一种不必要的刑罚,这是因为其认为,在死刑之外还存在一种恶或代价小于死刑但作用不亚于甚至还大于死刑的选择,即终身监禁。因为死刑剥夺的是人的生命,终身监禁剥夺的只是人的自由,却可给人持续的畏惧,因此,死刑的代价大于、威慑作用小于终身监禁。另一方面,死刑剥夺人的生命,终身监禁只剥夺人的自由,而两者所收到的个别预防之效大致相同,既同样是使受刑人终身不再犯罪,相应地,死刑的代价大于但个别预防作用同于终身监禁。因此,死刑因在总体上代价大于而收益小于终身监禁而是一种不必要的刑罚。贝卡利亚之所以反复强调死刑是不必要的,菲利之所以称死刑是“不必需”的,原因便在于此。
当代废除论者关于死刑对于个别预防是不必要之刑、死刑不具有特别的一般威慑功能与死刑不经济等立论,虽然对早期的废除论者的主张有所发展,但总的来说,仍未超出功利论的理论框架。赛林等通过引入实证统计分析来证明死刑对于一般威慑无效,对于个别预防作用不大,但其立论的根据,仍然是无用的刑罚便是不必要的刑罚、不必要的刑罚便是不正当的刑罚这一功利论的命题。哈特等所提出的有死刑的刑事司法体制经济代价大于无死刑的刑事司法体制,更明显地是功利论的观点。
2、刑罚学的功利论基础
功利论是主张刑罚的理性在于功利的一种刑罚理论。据此,刑罚是为预防犯罪而存在,刑罚的创制以对犯罪的有效遏制性为基本理性,刑罚的发动以有必要以刑罚遏制的人为对象,刑罚的分配以足以遏制犯罪为必要与限度,刑罚的执行以遏制性、必要性、适度性、相应性与经济性等为理性。死刑废除论的某些重要立论均是功利论的派生物。死刑不具有特别的一般威慑功能与死刑不具有特别的个别预防功能之所以自死刑废除论一提出便始终是其中最重要的立论,便是因为死刑因不具有预防犯罪的特别效果而不符合制刑的遏制性规定;死刑误判难以纠正之所以被作为废除死刑的理由,是因为死刑因被适用于根本不具有犯罪可能性的人而不符合动刑的有效性规定;死刑因不具有可分性而不具有可变性之所以被列为废除死刑的根据,是因为其不符合配刑与行刑的适度性的规定,牺牲了作为刑罚之最重要功能的改造功能,造成刑罚浪费;死刑的不经济性之所以成为废除死刑的立论,是因为其代价过高而不符合行刑的经济性规定。
(二)死刑保留论的功利论基础
1、伦理学的功利论基础
保留论者关于死刑是防止私刑的必要手段、死刑具有最大威慑力、死刑是彻底剥夺再犯能力的必要之刑、不可避免的错杀与滥用是死刑之利的必要代价、死刑不如终身监禁残忍、死刑的不经济性不足以成为废除死刑的根据等立论,均极为明显地是以功利论为基础的立论。因为死刑是防止私刑的必要手段的立论根据是没有死刑便可能导致私刑,而私刑相对于作为公刑的死刑具有更大的随意性,其害更大,以死刑遏制私刑,是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死刑具有最大威慑力与死刑是彻底剥夺再犯罪能力的必要手段的立论旨在表明死刑的效益大于其他刑罚之效益而是正当的;不可避免的错杀与滥用是死刑之利的必要代价的立论旨在表明,死刑之利大于其害,以小害换取大利是一种正当的选择;死刑不如终身监禁残忍的立论旨在表明死刑符合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法则;死刑的不经济性不足以成为废除死刑的理由,旨在证明死刑之大于其他刑罚的经济代价因有大于其他刑罚的效益相对应而是正当的。显然,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效益的功利论原理,是死刑保留论的以上诸立论的渊源所在。
2、刑罚学的功利论基础
作为死刑保留论之重要立论的死刑是防止私刑的必要手段,死刑具有最大的威慑功能与死刑是剥夺再犯罪能力的必要手段,均是从预防犯罪的目的对作为手段的刑罚的要求出发得出的结论,其赖以立足者均是死刑之于预防犯罪的必要性。即是说,诸如此类的立论均是以凡为预防犯罪所必需的均是正当的这一刑罚功能论的基本命题为基石。因此,刑罚功利论也是死刑保留论的刑罚学基础之一。在死刑存废的功利之争上,死刑废除论者与死刑保留论者的观点可以说针锋相对,各执一词。但是,双方对于死刑是否必要的“非此即彼”的思想方法却是共同的,而恰恰在这一点上,双方都失之片面。实际上,死刑的存废问题,简单的肯定与简单的否定都是错误的。对于死刑的利弊应当有一个客观的、中肯的评价:一方面,死刑确实具有威慑作用。因为大多数犯罪人毕竟还是喜生厌死的。另一方面,死刑的威慑作用又是有限的,那种神化死刑的威慑力,把死刑视为对付犯罪的神丹妙药的观点也是缺乏实证根据的。
三、死刑存废的人道之争
(一)死刑废除论主要从以下三方面论证了死刑的非人道性
1、死刑树立了野蛮的榜样
在废除论的首倡者贝卡利亚看来,“体现公共意志的法律憎恶并惩罚谋杀行为,而自己却在做这种事情; 它阻止公民去做杀人犯,却安排一个公共的杀人犯。我认为这是一种荒谬的印象。”“酷刑的场面给予人们的常常是一付铁石心肠,而不是教人悔过。”根据贝卡利亚的这种认识,死刑的野蛮在于其公开树立了杀人的榜样,因而促成与助长了人们的残忍心理。贝卡利亚的这一立论,至今仍为众多的废除论者所主张,尤其是他关于死刑在惩罚杀人者的同时标榜“杀人”正当因而是“一种荒谬论的现象”的观点,更为当代废除论者所继承。现今广为流行的死刑是一种“合法化的谋杀”的说法,便只不过是贝氏这一观点的发展。
2、死刑是野蛮时代复仇的遗风
与贝卡利亚等一样,部分废除论者也认为死刑是一种野蛮之刑,但其并不立足于死刑树立了野蛮的榜样,而是从刑罚进化的角度论证死刑的野蛮性。其基本观点是,死刑产生于原始复仇习惯,因而是野蛮的标志,其在现实中的存在,是原始时代野蛮习惯的遗风。而这与现代文明社会不协调,有悖社会进化的趋势。日本学者泷川幸辰主张的“死刑是野蛮时代的遗物”,“20世纪的文化应该征服死刑这野蛮时代的文明的最后抗拒者”,便是这一观点的最明显的反映。这种说法因具有坚实的史实根据,因而颇具说服力,使反对者难以反驳。
3、死刑助长人性的残忍
与泷川幸辰等人的观点相似,不少废除论者也立足于死刑与复仇的关系来论证死刑的野蛮性。但其立证的基础不是进化论,而是人性。按照当今许多死刑废除论者的观点,复仇虽是人的一种本能,但其又是人性中的一种劣性,其促使人产生仇恨、杀戮、残忍。这种欲望,不符合社会的宽忍精神,毁灭仁慈的美德。而以死刑作为“杀人者死”式的报复手段,是对人的复仇心态的姑息、适应与宽容,因而必然助长人性中的野蛮与残忍因素,有碍善良、仁慈的人性的培养。因此,死刑虽能满足复仇欲望而貌似公正,但这种表象的背后掩盖着毁灭善良人性的真相。
(二)死刑保留论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论证了死刑的人道性
1、死刑基于伦理正义的必然要求
死刑保留论者认为,对于那些罪大恶极的人处以死刑,是除恶必致,是人伦道义、公平正义的具体体现。若不如此,不足以伸张正义,不足以维持法律的公平。杀人处死,罪所应得。如果杀人者不死,则意味着对一人的宽容而对大多数人的残忍,应杀而赦,遗患无穷。因此,保留死刑,实属天理昭然。
2、死刑的适用是人道主义的要求
如果对杀人者宽容,那么更多的善良公民的人身和民主权利就会丧失,这才是真正的不人道和反人道。针对废除论者所提出的死刑助长人性的残忍的立论,不少保留论者反唇相讥,认为对杀人者不处死刑是对杀人这野蛮行为的放任、姑息与迁就。在死刑是否人道这一问题上,死刑废除论者与死刑保留论者的观点同样是大相径庭的。在这一点上,存在一个立场问题:从社会防卫角度来说,对杀人者判处死刑,满足社会正义的要求,当然不能说是不人道。但从人权保障的角度来说,即使是罪犯,也还是公民,对其判处死刑,剥夺作为最基本人权的生命权,确有不正义之嫌。但是我认为,对死刑是否人道这一问题,应当从社会的与历史的这一层次进行考察,而不应避开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而去抽象地谈论这一问题。死刑作为一种刑罚制度,连同对待死刑的功利观念和正义观念,都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决定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因此,死刑的存废应当同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结合起来考察。在一定的国家,死刑的存废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第一,社会存在因素,这是死刑废除的物质基础。这里所谓的社会存在包括社会的物质文明程度和社会的物质生活水平。在社会的物质文明程度和社会的物质生活水平较高的社会,犯罪所造成的危害与人所创造的物质价值的反差大,人们比较看重人的生命价值。因此,死刑废除的物质条件较为具备。反之,在一个物质生活水平较低的社会,犯罪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大,人的生命价值相对低。因而,缺乏死刑废除的必要的物质条件。第二,社会意识的因素,这是死刑废除的精神基础。社会精神文明程度较高的社会,朴素的报应观念逐渐丧失市场,对待犯罪的态度较为理智。而且,由于人们的文化水平高,较为轻缓的刑罚就足以制止犯罪。因而,死刑废除的精神条件较为具备。反之,在一个文明程度较低的社会,人们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杀人偿命的观念十分浓厚,只有用较为严厉的刑罚才能制止犯罪行为。因而,缺乏死刑废除的必要的精神条件。事实说明,凡是不具备这两方面条件的,死刑即使废除了,还会重新恢复。而随着这两方面条件的逐渐具备,死刑的废除将成为现实。所以,笔者认为,就一个国家而言,如果达到上述两个条件,废除死刑或事实上废除死刑是迟早之事,但就全世界而言,要想废除死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资料
1、李云龙•《死刑专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死刑制度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贾宇•《死刑的理性思考与现实选择》•法学研究杂志
3、胡云腾•《死刑基本理论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
4、贝卡利亚(意)•《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5、邱兴隆•《边沁的功利主义死刑观》•外国法学研究杂志
《刑罚的正当性原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6、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7、黑格尔(德)•《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
8、菲利(意)•《犯罪社会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9、哈特(英)•《惩罚与责任》•华夏出版社
10、李海东•《日本刑事法学者》•法律出版社
11、龙勃罗梭•《犯罪人论》•中国法制出版社
12、加洛法罗•《犯罪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查看更多
904名中国成年人第三磨牙相关知识、态度、行为和病史的横断面调查思维导图
 U633687664
U633687664树图思维导图提供《904名中国成年人第三磨牙相关知识、态度、行为和病史的横断面调查》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904名中国成年人第三磨牙相关知识、态度、行为和病史的横断面调查》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10b9a8a2dd2fb4593f8130ef16c320fc

9.战斗的基督教思维导图
 U582679646
U582679646树图思维导图提供《9.战斗的基督教》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9.战斗的基督教》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33d168acd0cd9f767f809c7a5df86e3a

相似思维导图模版
首页
我的文件
我的团队
个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