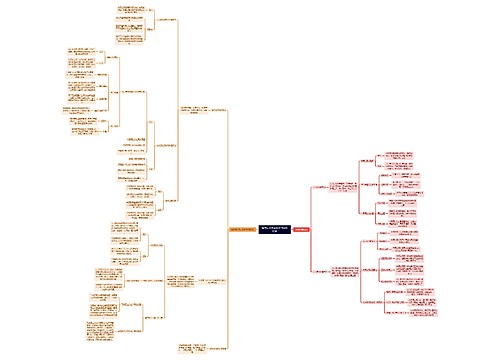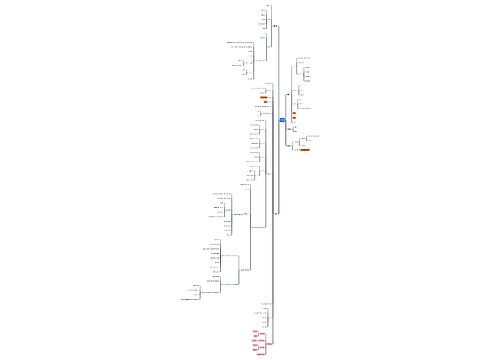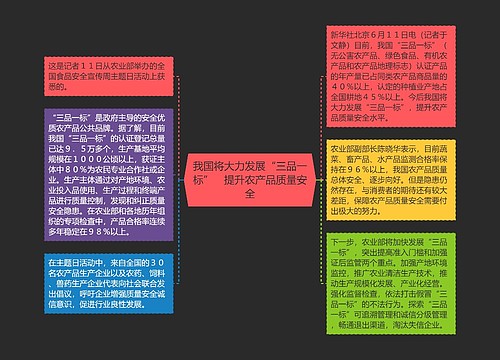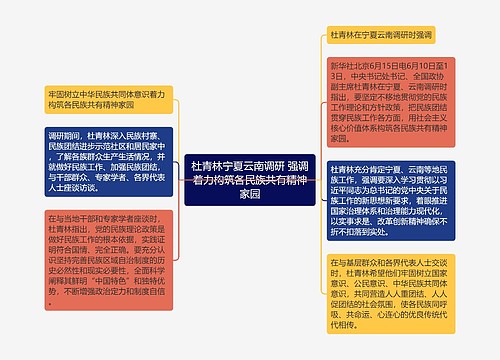近年来,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逐步得到人们的认可,疑罪从无被当做无罪推定的一部分也得以在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中有所反映。1989年1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一审判决宣告无罪的公诉案件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中指出:“对于因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经多次退查后,检察院仍未查清犯罪事实,法院自己调查也无法查证清楚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可直接宣告无罪。”这一重要批复,其实质就是吸收了无罪推定关于“疑罪从无”的处理观念。后来,最高人民法院在1994年《关于审理刑案件程序的具体规定》的批复中又规定,“人民法院对案件的主要事实不清、证据充分,而又确实无法查证清楚、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的,判决宣告被告人无罪”。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一条反映了无罪推定的部分内容,但是,该条并不是无罪推定的完整表述,因此,我国是否已经确立无罪推定的原则还是不能完全肯定的。另外,该条也没有说应疑罪从无。与无罪推定有关联的还有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该条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项规定也被作为是“疑罪从无”的法律根据。其实,疑罪从无在我国目前法律中是模糊不清的,在实践中也难以操作。
笔者认为,在我国的刑事司法改革中,亟须明确的是无罪推定原则,而“疑罪从无”的提法增加了确立无罪推定原则的困难,不宜作为无罪推定的必要条件提出。
对疑罪应当如何处理,这是古今中外刑事司法难以回避的问题。
中国古代的刑事司法对疑罪和疑罪的处理是有法律规定的。如《唐律》规定:“疑,谓虚实之证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傍无证见;或傍有闻证,事非疑似之类。即疑狱,法官执见不同者,得为异议,议不过三。”在我国古代,对疑案的处理基本上是采取“罪疑从赦”的原则,即身有疑罪的人犯虽可免徒刑之苦,但仍需根据疑罪的社会危害性轻重缴纳金额不等的赎金。我国古代对疑罪的处理在实质上是一种有罪处罚,不过是“罪疑惟轻”而已,而不是疑罪从无。
西方国家,如英美等国没有疑罪从无的说法,但有疑罪的提法。英美法系的刑事司法中,证明有罪的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排除合理怀疑”不等于没有怀疑,而是可以有各种怀疑,其中当然包含疑罪。即使存在怀疑,如果审判人员确信被告人有罪,则作有罪判决;不能肯定被告人有罪,则作无罪判决。可见疑罪并不一定要从无。不实行疑罪从无,也可能产生误判,特别是将无罪的人误判为有罪,这是任何国家的刑事司法都免不了的事。关键是要将误判减少到最低程度和发现误判后及时纠正并采取补救措施。
对疑罪的判决应当根据怀疑的程度、怀疑的种类分别处理,具体案件具体分析。但是,也不能没有总的原则。笔者认为,判决有罪无罪的总原则应当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方式。以判决有罪为例,主观上审判人员应当在确信被告人有罪的情况下才能作有罪判决,而这个确信的客观根据则是证据,以及对证据的判断。这就要求审判人员有较高的水平和责任心。
为了减少误判,增强审判人员的责任心,并且增加司法的透明度,笔者建议,审判人员在判决书上说明判决理由。我国现在的情况是,法院作出的判决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是说理简单甚至没有,在一个判决书中只是列出控方指控的内容、提交的证据,辩方提出的意见、提交的证据,法院自己查证的事实,再加上“本院认为”、“依据某某法某某条之规定”等格式化、机械化的语言。法院作出这样判决的各种证据、审判人员的思维和推理过程都没有。这样的判决书不要说有时候当事人自己不明白,就是法官自己也可能不清楚。在实践中,甚至有一、二审法院作出判决的理由是一样的,但结果不一样。因此,有必要在立法上建立判决说理制度,要求法官对证据的采信、事实的认定、法律的适用理由与过程都必须详细地记载于判决书中。对疑罪判决来说,判决说理制度要求法官在对疑案作出有罪、从轻判决时必须有充分的、可见于书面的理由,在案件存疑时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判断也要有理由。这样,一方面可以强化法官适用法律的责任心,避免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的随意性,防止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草率作出一些违法判决。另一方面可以让当事人容易明白、接受法院的裁判,从而增强其权威性。

 U633687664
U633687664
 海沙
海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