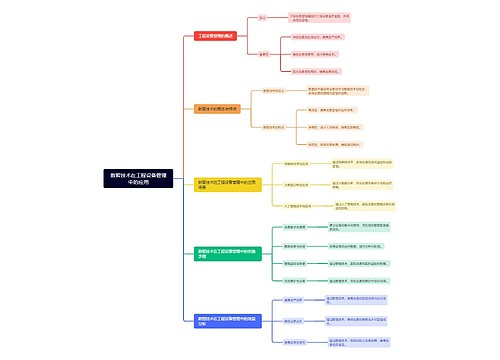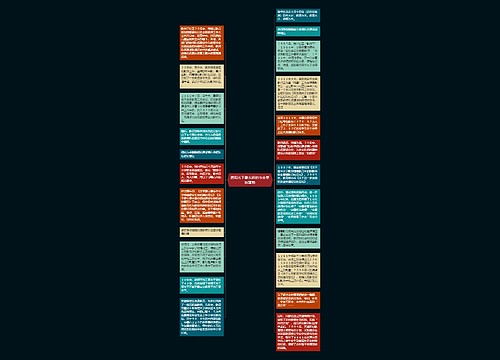要正确理解特殊防卫权,必须从根本上理清修订刑法第20条第2款和第3款的关系问题。笔者认为,从立法本意分析,修订刑法第20条第2款关于正当防卫必要限度的规定,应当视为一项原则,它对所有正当防卫行为(包括特殊防卫行为)都是适用的,并具有指导意义;而第3款关于特殊防卫权的规定,乃是对第2款的补充,其立法宗旨在于使第2款更具有透明度和可操作性,以便司法部门在处理特殊防卫案件时,更准确地把握第2款关于正当防卫必要限度的规定。明确了即使是防卫行为致不法侵害人重伤、死亡的,也不认为是“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综上,刑法第20条第2款和第3款之间的关系应是一般与个别,普遍和特殊的关系,而不是相互对立、排斥的关系。
特殊防卫权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所谓“有限”,是指特殊防卫权的客体范围,只有对正在进行的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才可以行使特殊防卫权;所谓“无限”,是指对上述特定的犯罪的防卫行为的强度没有限制,即使防卫行为的强度激烈致不法侵害人重伤、死亡的程度,也不属于防卫过当。这是因为新刑法有关特殊防卫权的规定“考虑到不法侵害的紧迫性特征,带有暴力性质的不法侵害对于防卫人来说是紧迫的,即一方面暴力侵害刻不容缓,如不及时制止,便马上会给合法利益者造成损害。另一方面暴力侵害破坏性大,如不加以有效反击,就会给合法利益者造成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不法侵害的这种紧迫性决定了正当防卫行为实施的必要性,更决定了防卫人防卫行为的匆忙性。防卫人在人身权遭受暴力行为侵害的情况下,可能慌不择路,无法准确判断防卫行为的强度,此时防卫人致不法侵害人重伤、死亡的,均不是防卫过当。防卫人行为的强度应当说是与侵害行为的强度相适应的,即所谓以暴制暴”②。总之,特殊防卫权是“有限性”和“无限性”的有机结合,辩证统一,两者是相互联系,缺一不可的。
要正确理解新刑法关于特殊防卫权的规定,还必须改变将特殊防卫权的有限性与无限性割裂开来的片面观点。
第一,“特殊防卫权无限说”片面强调特殊防卫权无限性的一面,忽略其有限性的一面。
第二,“特殊防卫权有限说”片面强调特殊防卫权有限性的一面,忽略其无限性的一面。
这种观点主要依据有两条:一是特殊防卫权可能被滥用,公民私力救济侵入国家公权的运作领域和可能被罪犯歪曲利用。二是特殊防卫权缺乏强度限制,损害了刑法的公正性。对于其第一个理由,笔者认为,这种想法未免有过虑之嫌。因为在“已经超过足以制止不法侵害的限度或犯罪人已无力再实施侵害”的情况下继续进行的“防卫”行为,已经不是正当防卫。在这种情况下,不法侵害人已经被制服,或者已经丧失了继续侵害的能力。按照正当防卫的构成条件来分析,此种情况属于不法侵害已经结束后的所谓“防卫”,是事后防卫,为防卫不适时。而不适时的“防卫”不是正当防卫,行为人应对其所造成的危害后果自负刑事责任,与特殊防卫权无关,怎么能张冠李戴、李代桃僵呢?担心歪曲利用特殊防卫权以达到杀死、伤害他人的目的,这是不法分子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其性质或属于防卫挑拨,或属于互相斗殴,由于其不具有正当防卫的意图,所以也不是正当防卫。总之对于这类问题,根本解决方法不是靠因噎废食地取消特殊防卫权,而是要靠司法人员广泛深入地调查取证,认真仔细地审查判断证据,查明案情,由表及里,去伪存真,剔除隐藏在正当防卫背后的防卫不适时、防卫挑拨、互相斗殴,还特殊防卫权的本来面目和清白之身。
特殊防卫有限说的第二个理由,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还是要加强对新刑法第20条第3款的全面理解。经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该条款所列之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的犯罪,必须具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性质。由于规定有“正在进行的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所以防卫的只可能是对人身安全具有现实紧迫性的严重危害,而不是抽象可能性的危害。所以采取投毒、对哺乳期婴儿断乳等手段杀人,采取麻醉手段抢劫、强奸、绑架,采取“半推半就”的方式和利用优势地位强奸的,因对人身安全不构成现实紧迫性的严重危害,不法侵害人也未使用暴力,行为人自然不可以也不必要行使特殊防卫权,而只能行使“一般防卫权”,即采用非将不法侵害人杀死、致伤的较为缓和的方式制止不法侵害行为,当然不能防卫过当。至于使用以暴力相威胁的手段进行抢劫、强奸、绑架,则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不是对人身安全构成现实紧迫性的严重威胁,如仅用语言威吓,则不能行使特殊防卫权。但如果以刀架在脖子上,枪口顶在脑袋上的方法相威胁的,由于这种威胁对人身的危险已迫在眉睫,一触即发,随时有可能转变为现实的暴力侵害并极有可能致人伤亡,具有正在进行的严重危及人身?
参考书目:
①范忠性:《刑法典应力求垂范久远》、《法学》,1997年第10期
②赵秉志主编:《新刑法全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80面页

 U482683014
U482683014
 U182637395
U1826373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