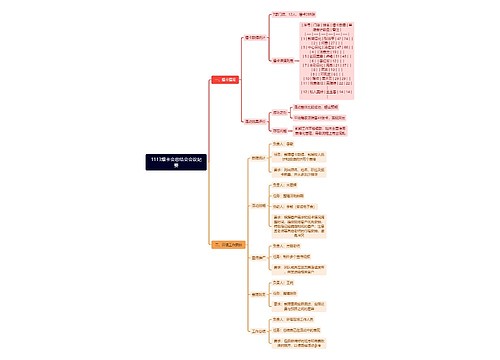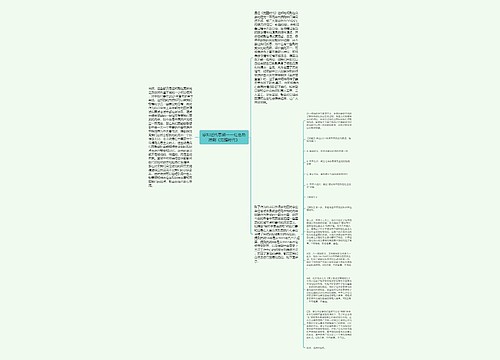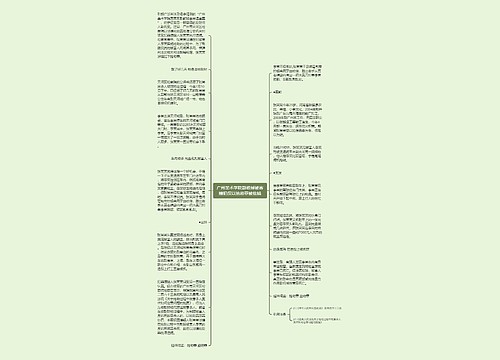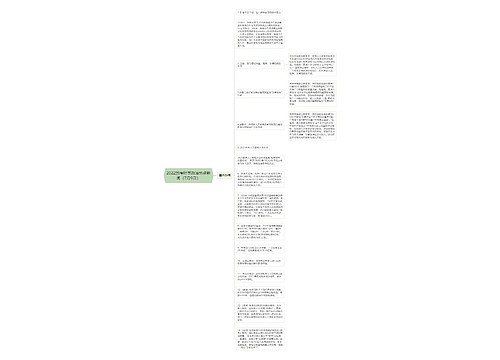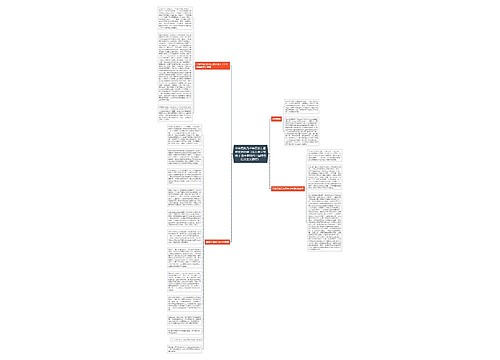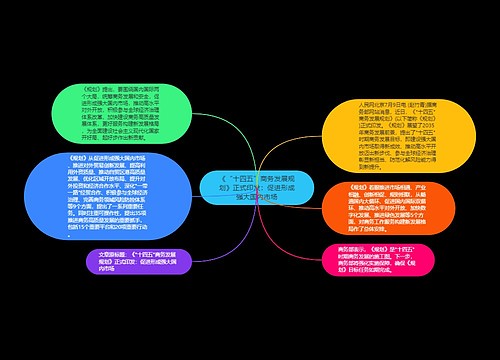由于父母尚在,聂某还不算正式下葬,不能入祖坟,只能在七八十米外浅浅地堆成一个简陋的坟头。张某扑在上面哭得死去活来的一张照片被全国众多媒体刊登过。她说,每一年清明节都哭成这样。
“也有人劝我,忘了他(聂某)吧。我也想忘,可就是忘不了。我也不知道,是一点母爱呢,还是一点思念。”她给儿子的坟头拔着草,一把一把地,异常坚决地嘟囔着诸如在阴间要挺住、要跟坏人斗之类的话。
转折出现的那一天———2005年初,家里一天来了两拨记者采访,起初老两口以为是采访农村生活话题,结果发现对方的问话全部与此无关,觉得蹊跷了。接下来,他们从越来越多的记者口中,得知了一个叫王书金的囚犯。他对警察说:那起强奸杀人案是他犯的。
而那起案子,导致他们的儿子聂某被抓、被审、被枪决,已经十年了。
供出那起导致聂某被枪决的强奸杀人案时,王书金还背着另外数起同类案件,一审被判处死刑。
王提起了上诉。他本人讲,这是因为当地检察院未起诉他犯下的这起案子,“死要死得良心无愧”、“不想让好人替自己背黑锅”。据内部人士透露,王记忆力极强,对十年前自己强奸杀人的细节记得极其清晰,甚至一串钥匙的摆放位置,都记得清清楚楚。
如果不是这个恶人最后的良心发现和超强的记忆力,聂某一案将与聂某本人一起,就此死去,被世间遗忘。正如他被枪决后12年,母亲才第一次看到判决书。
判决书的缺失,让法院从2005年-2007年里,多次理直气壮地拒绝过张某的上诉。这让她气结梗喉:当初聂某被一审、二审判处死刑后,石家庄市中法、河北省高法根本就没有给过她判决书。
聂案之所以有今天成功上诉的局面,核心的程序因素就在于这两份判决书的神奇出现。
时为2007年4月,《南方周末》对此曾有如下描写:
“如有神助,今年4月的一天中午,为寻得判决书精神近乎崩溃的张某拿到一封特快专递,没有寄件人信息。撕开一看,‘判决书!’这是1995年3月15日石家庄中院对聂某作出的一审判决。张某惊喜又悲凉———这是儿子被处决12年后,她第一次看到判决书的模样,这也是她奔走两年经受无数屈辱苦求不得的东西……一个多月之后,张某又以同样神秘的方式收到了河北高院的终审判决书。”
这个寄来判决书的神秘人物,马上被众多媒体评价为“体制内良心”的一点微弱仅存,并为他画出一副相貌:工作于河北尤其是石家庄的政法系统,与聂案有直接或间接关联,职位不会太高……
当着记者的面与老伴激烈争论后,张某仍然坚持这样的观点: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应该不至于有人因此受到侵害。“你写吧,没事。”
这个曾温暖无数人内心的真相,事实上异常冷酷:两份判决书,是她家当时委托的律师去被害女子康某的父亲手里借来,复印的。那一点微弱的“体制内良心”,纯属子虚乌有。
张某回忆,起初她去要,康父常以此话回应:“这个东西(判决书)我没有义务给你,你应该去朝河北高院要”。她推测,康父是对给“杀女凶手”平反,有本能的反感。
之后,律师多次上门苦口婆心做工作,终于如愿。至于当初为何隐瞒,张某透露,是她自己要求《南方周末》保密的,怕给律师找麻烦。“毕竟,他还要在河北做律师。”
这么多年来,从省、市、县、乡直至村,各级行政和政法机关没有给过她任何一点物质帮助,或精神鼓励。正因为帮助太少,她才对律师,对那些帮助过她而素昧平生的记者、学者记得清清楚楚。
张某、律师和全国舆论所苦苦求索的,不过是一个程序正义———争取再审,重新审视16年前那起杀人案。事实上这种再审的难度极大。1994年,河北省还没有D N A检验等先进刑侦技术,认定聂某为凶手的依据主要是口供。基本上,再审就等于要用王书金本人的口供,去推翻聂某当年在公安机关作出的口供。
而王书金本人,则为这种最后的良心发现,而多活了4年。早在2007年他就被河北高院二审,但4年后的今天,他仍然被拘押在看守所内。在聂某案尚未重新盖棺论定之前,他这个信息的源头暂时是安全的。“我佩服他这个勇气”,张某思索了一会儿,“可要不是他干下这起事,我儿子也不会冤死……”
每个月,张某都要步行两公里,再坐两个小时的车去一趟河北高院,问儿子的案件何时能够再审。女儿聂树慧在石家庄做小学教师,女婿是个司机,都忙。这桩活儿只有落在她身上。
每一次都是千篇一律的信访大厅、一个法官会见,态度非常和蔼。“你回去吧,再等等”。至今,为张某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都没有得到该院的许可,翻阅聂某案当年的案卷。
她只能日复一日地与时间赛跑。既要一趟一趟地赶时间去法院催促,又要提醒自己一定要坚持到时间后面———再审的那一天。她明白,自己是为儿子洗冤的主力,不能倒下。时间既是她的敌人,又是她的珍宝。接待来访的记者,她表现得极其专业,几分钟就能进入话题讲述,不浪费一点时间。尽管这种讲述———讲述儿子如何被抓、被杀、被烧掉,甚或还要带他们去看儿子的墓,在墓前哭上一场,对一个母亲而言,是世间最大的残忍。
讲述也曾经惹来麻烦。有一年,来了三个人,自称“检察院的”。他们问她:知不知道凤凰卫视能放到半个地球?你怎么能接受他们的采访,这样影响太大了!
“我当时真是气昏了。”眼泪再一次从张某颤动的脸上滑下来。“他们要是再敢来,我一定问问他们:那我儿子被冤死了,这影响大不大?你们怎么就不管管呢?”
每年的年三十,她都要在桌上摆一双筷子、一个空碗,在里面放几个饺子。聂一问起,她就说:这是多余的。她既希望儿子的灵魂能回到家中团聚,又不敢刺激到老伴的病情。她已经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男人,不敢再因此失去另一个。
这个问题,张某反应极快,显然已想过无数遍。她的脸立刻扭曲出一个温暖的笑容,抬头望向阳光:“听说过。”

 U633687664
U6336876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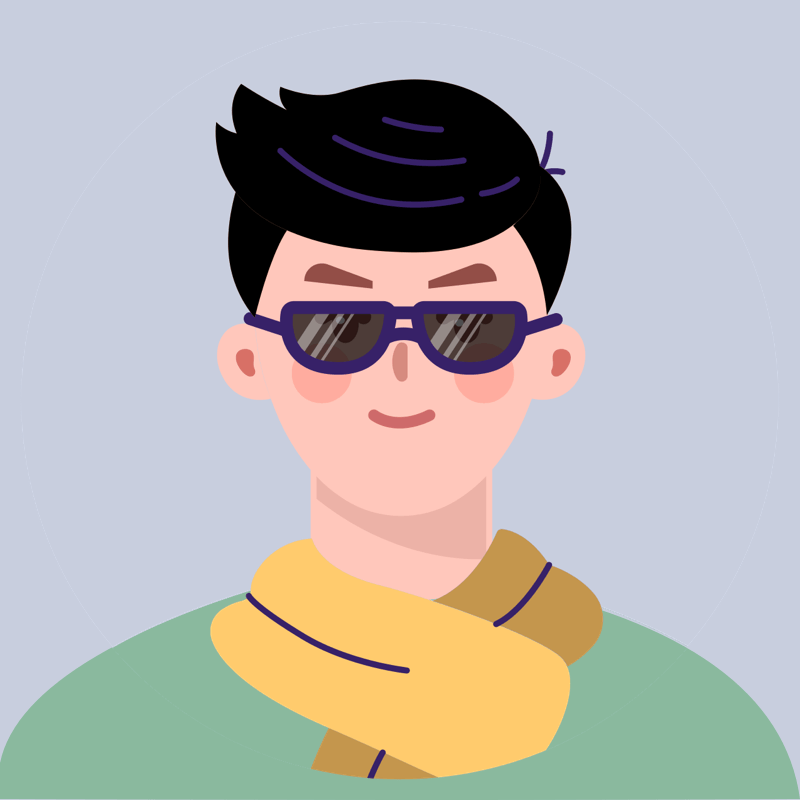 U245265618
U245265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