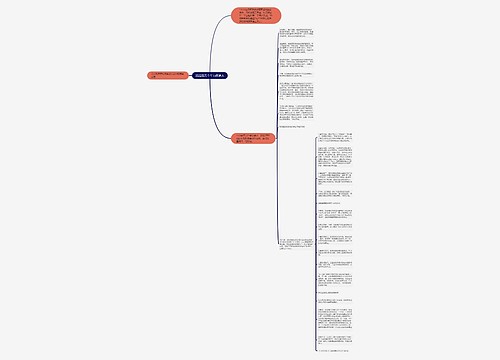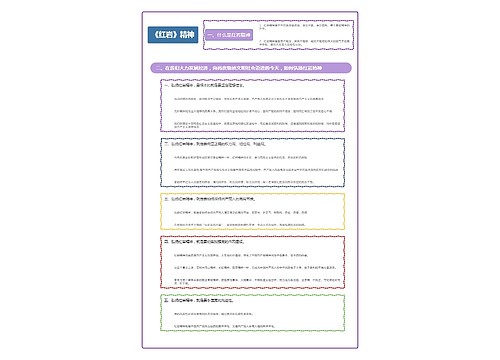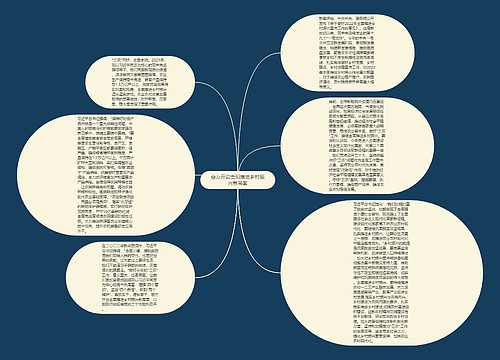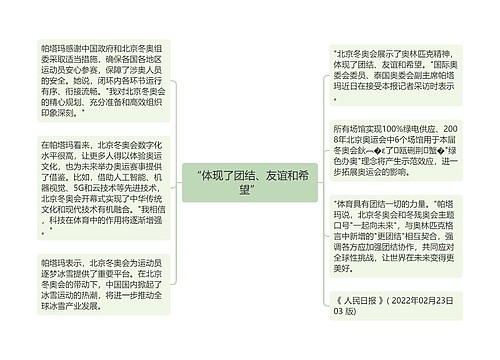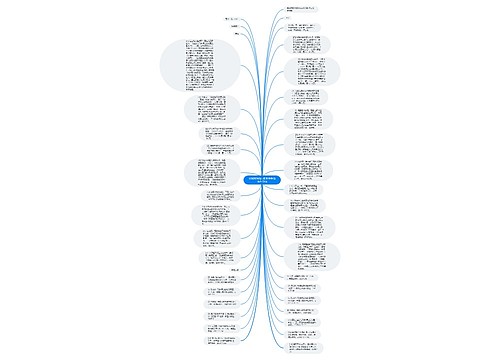学者关于宪法与刑法关系效力之维的观点,可以分为三种:其一是“母法说”,通常是在论及宪法的特征之效力位阶时及宪法与法律的关系时会涉及到宪法与刑法的关系,认为刑法规范是宪法的具体化,各部门法都是从宪法出发,并且是对宪法原则的引申,把宪法称为“母法”、“最高法”,把普通法律称为“子法”。其二是“依据说”,认为宪法是刑法规范的依据和指导。在宪政社会中,刑法是依据宪法制定的。刑法的基本原则都能从宪法中找到依据,包括直接作为宪法规范出现在宪法中和隐含在宪法中的原则;刑法的“分则”部分都贯彻了宪法的基本原则,并可能实现宪法某些规则的具体化。其三是“不抵触说”,一般是在论及宪法的效力特征和合宪性解释的要求里涉及到,认为刑法应受宪法限制,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以上的几种观点都建立在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基础之上,并不是严格独立的,毋宁是相互影响和包容的。比如采用“母法说”的应有之意便是宪法是作为部门法的刑法的依据,同时作为部门法的刑法不得与宪法相抵触。所以有些学者在论述时并没有严格区分它们的意义。但笔者认为尽管在使用中通常三者之间没有严格区分,但三者之间依然有微妙的差别,反映了对宪法规范的不同认识。以上三种学说表现出宪法对作为部门法的刑法服从其最高法律效力的刚性和具体要求是依次递减的,作为部门法的刑法立法的灵活性是递增的。
“母法说”十分形象地反映了宪法与法律的先后、上下位阶的位阶和序列,突出了宪法的根本法地位和最高效力。然而,仅仅用生物学上的母子关系来比喻,容易僵化地处理两者的关系,从而造成宪法法律体系的封闭性和停滞性。这一机械的观点将法律的依据局限于宪法条文。凡是立法必须依据现有的宪法规范,凡是宪法没有规定的,就不能立法。于是,社会对法律的需求就转化为对宪法的需求;宪法应当是一部百科全书或者法律大纲。只要是各社会生活领域的重要问题,都应当在宪法中得到原则体现,然后再由各原则细化为具体的法律;倘若宪法无规定而社会又迫切需要的立法必须先修宪后立法。[1]考察各国的法治实践时会发现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从立法实践看,现代社会发展中新问题层出不穷,调整这些新问题的法律也不断被制定出来,而宪法文本修改的次数却远低于普通立法的频率,即使在宪法修改最频繁的国家也是如此。从法律文本看,并不是法律文本的每一个条文都可以回溯到具体的宪法条文,尤其是专业技术性较强的具体法律条文。因此“母法说”会让我们对宪法与刑法的关系产生误解,这种误解常常造成我们对宪法效力的怀疑。
“依据说”能较好体现宪法作为根本大法对作为部门法的刑法的基础和立法指导作用,说明宪法对部门法产生规制效力的方式。比“母法说”的观点更为灵活和切合实际。但对于“依据”的具体含义还有待进一步的说明,以避免由于学者使用语境的不同,而引起歧义。凯尔森在其关于法律秩序的效力位阶理论中认为,法律效力的理由是基础规范,宪法作为某一国内法秩序的基础规范是国内法的效力理由,并认为,“一个法律秩序的基础规范则规定一个人应当像宪法的“缔造者”和由宪法——直接地或间接地——授权(委托)的那些人所命令的那样来行为”。“规范之所以是有效力的法律规范就是由于,并且也只是由于,它已根据特定的规则而被创造出来。法律秩序的基础规范就是这样一个被假设的最终规则,根据该规则这一秩序的规范才被创造和被废除、才取得并丧失其效力”。[2]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我们可以得出宪法作为部门法“依据”的两种形式意义上的含义:其一是部门法是由宪法授权的立法机关依据特定程序制定出来的;其二是在宪法规范之中存在具体的授权规范,部门法是依据该授权规范制定的。“宪法确定某一规范的细节问题由普通法具体规定,这是十分必要而又为世界各国所普遍采用的。”[3]实际上在现代宪政国家一般还对法律有着实体上的要求,比如立法机关不得制定违反宪法人权保障原则的法律和危害国体政体的法律等,对立法权本身也加以了限制,而且宪法规则本身也不局限于授权性的规范,也有与部门法相关的实体性的规范,而这些规范都会称为立法的依据,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得出“依据”的实体意义上的含义,即部门法受宪法规范具体内容的限制,否则即使是由法定机关依据法定程序制定的形式要件完备的规范性文件,也因违反宪法而不具有法律的效力。因此刑法以宪法作为立法依据,必须同时满足形式与实体两方面的要求。由于刑法是一个具有高度技术性法律,且深受社会伦理及现状的影响,虽然对“依据”的含义做了说明,但“依据说”仍然存在这样一个未决问题,即在满足形式依据的要求之后,刑法可否根据具体情况的要求规定作为实体依据的宪法规范之外的内容?
“不抵触说”则能够解决“依据说”的这一困惑,法律由宪法授权或者宪法授权制定的法律授权的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制定,并且不同宪法规范包括宪法原则及规则相抵触即是有效的法律,否则即无效。因此在不同宪法规范抵触的情形下,立法机关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的要求制定刑法规范,即便这些规范所涉及的内容在宪法规范中没有规定。“不抵触说”是“对宪法性质、地位、功能的积极把握,只禁止对宪法的抵触和违法,开放性的对待宪法的内容及其释义,从而使宪法成为‘活的母法’。其关键在于对宪法态度的科学性和灵活性。这有赖于对宪法精神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4]这样反倒是对宪法规范坚守的最好方式。

 U633687664
U633687664
 U582679646
U582679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