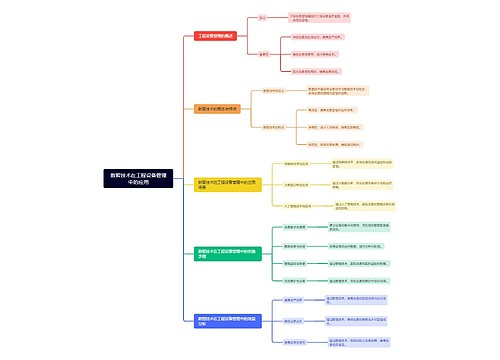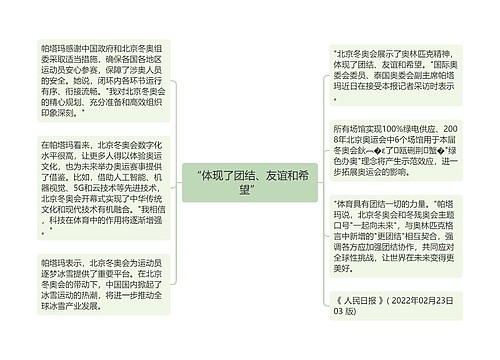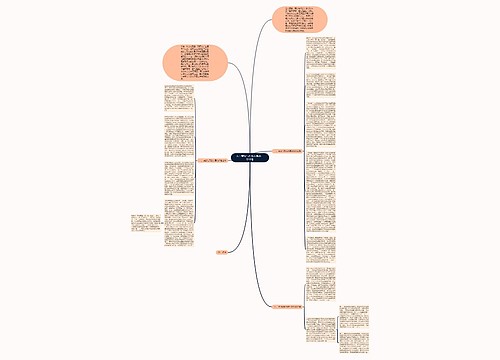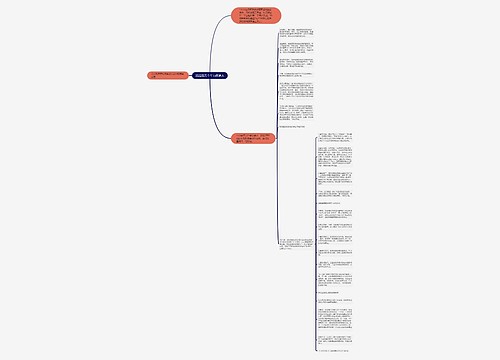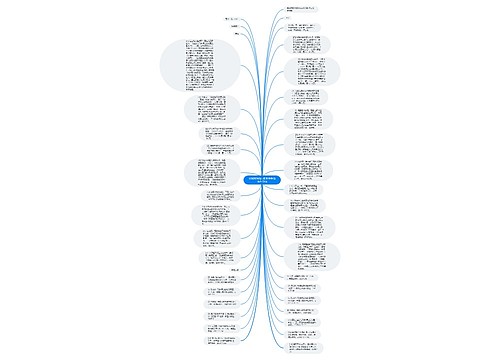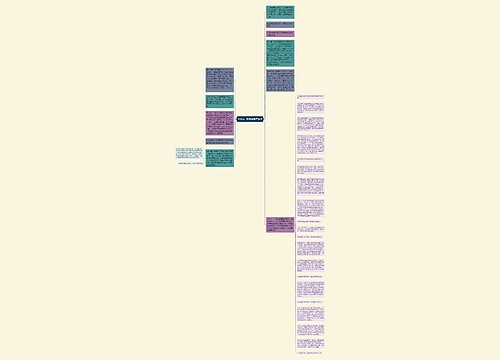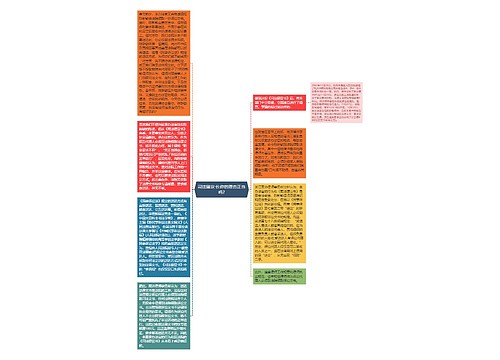在我国,理论上最早研究持有行为和持有型犯罪的是储槐植教授,他认为持有是与作为、不作为并列的第三种行为形式。持有型犯罪则是从行为的特征出发加以分类形成的一类犯罪。我并不倾向于认为持有是介于作为与不作为之间的状态,持有中仍存在行为要素,没有必要在作为与不作为之间寻找第三种行为类型。但是,从理论上研究持有行为和持有型犯罪是有意义的,对于司法实践中认定这一类犯罪具有现实意义。
蒋:看来,您是大陆法系刑法理论否定持有行为论者。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对持有行为和持有型犯罪的分析。持有型犯罪,作为刑法规定的行为人因某种客观不法状态而承担刑事责任的犯罪,在刑事立法中表现为一定特征,值得我们专门提出来研究。从目前的刑事立法来看,刑法规定持有型犯罪的方式有两种:一是直接规定“持有”;一是间接规定“持有”。前者在条文表述上包含“持有”,如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款的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第二百八十二条第二款的非法持有国家绝密、机密文件、资料、物品罪,第三百四十八条的非法持有毒品罪,第三百五十二条的非法持有毒品原植物种子、幼苗罪。后者如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黄:是否承认持有行为作为介于作为与不作为之间的第三种行为,的确不影响我们对持有行为和持有型犯罪专门进行研究。持有行为类似于我们在罪数中探讨的继续犯,行为与状态同在。举例而言,继续犯中的非法拘禁罪,便兼有作为与不作为的性质。比如,一人事先不知道有人处在荒郊野外的密室中而关闭房屋,事后知道有人被关闭在密室中,是否有义务恢复他人自由,如果不恢复,先前的关闭房屋和后续的拘禁状态便结合在一起构成非法拘禁罪。在这一意义上,形成持有行为中的客观不法状态的先前行为和客观不法状态本身都应当在持有行为中结合在一起理解,故,持有行为同样具有行为的要素,而不仅仅是一种客观不法状态。在我国1997年刑法中,持有型犯罪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拒不说明型,即第二百八十二条第二款和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犯罪。基本条件是主体持有特定物品作为前提,拒不说明来源才构成犯罪。一是单纯持有型,即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百四十八条和第三百五十二条规定的犯罪。立法上规定客观持有法定禁止持有的物品便可认定为犯罪。这些犯罪中的持有行为,无一例外地都可以从形成持有中客观不法状态的行为和不法客观状态来加以理解。
蒋:通过同继续犯类比来理解持有,的确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但是,持有中行为性质并不明显。比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强调的是超出合法来源的财产,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强调的是非法持有枪支、弹药。
黄:我们不应当静态地去理解持有。在赞成将持有作为第三种行为形式的论者看来,持有是一种状态。的确,持有超出对行为的评价而偏重对状态的评价,但是将持有解释为第三种行为形式与法律调整内容有偏差,法律调整的是人的行为,但客观的事实与状态并不在法律调整之列。这是我不赞成将持有作为第三种行为形式的出发点。反过来,不管你前面所讲的直接持有和间接持有,都是行为与状态同在,可以在作为与不作为的框架中解释持有。
蒋:但是,持有应当在作为与不作为之间有一个落脚点。行为包括作为与不作为,持有究竟是作为还是不作为,必须为持有在作为与不作为之间寻找一个归宿。
黄:我们需要明确的是,作为与不作为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比如,非法拘禁是作为犯还是不作为犯,很难有一个准确的答案。非法拘禁行为兼有作为与不作为的性质。从持有的表现形式来看,更多地表现为作为,持有指向的对象要么是违禁品,要么是法律禁止持有的物品,比如,国家禁止持有的枪支、毒品、假币,法律禁止为之而为之,这便是作为。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故意是一种推定的故意。规定推定的故意,是因为对持有型犯罪主观方面难以认定。
蒋:由持有特定物品的不法状态推断,必然存在一种取得特定物品的先前行为。为何不对先前行为予以惩治,一是因为先前行为合法与否不好判断,一是司法机关难以收集到证据查证先前行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一书中,曾经对非法持有毒品罪解释为:“考虑到一些非法持有毒品者,虽然是具有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可能性,但并未掌握这种证据,同时还存在为他人窝藏毒品等其他的可能性。只有在确实难以查实犯罪分子走私、贩卖毒品证据的情况下,才能适用本条规定对犯罪分子进行处罚。”由此可推知持有行为立法的本意。
黄:结合持有的先前行为来分析持有,这是一种动态的方法。在犯罪学中,往往表现为上游犯罪和下游犯罪的关系。我们可以将所有的持有型犯罪解释为下游犯罪。在刑事立法上,大量设定下游犯罪的基本法律背景是便利诉讼、严密刑事法网,在无法收集到证据的情况下合理地通过下游犯罪追诉犯罪人。如果没有设立下游犯罪,则上游犯罪造成的是一种状态——事后不可罚行为,如自己持有盗窃获得的赃物。如果规定了下游犯罪,比如偷来枪支藏匿、制造贩卖的毒品自己持有,证据没有突破按照下游犯罪认定,证据一旦突破则认定为上游犯罪。下游犯罪独立成罪,存在独立的规范评价,我们不能从下游犯罪依附于上游犯罪存在的关系上去评判。司法实践中,下游犯罪中真正的持有人与上游犯罪可能并无联系。比如,持有毒品的为吸毒者,他并无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的行为,规定为下游犯罪表明国家禁止个人拥有一定数量的麻醉性精神药品。因此,在刑法解释上,我们不要将持有型犯罪总是同上游犯罪相联系,解释为一种状态,而应当将其理解为一种独立的犯罪,因证据的变化罪名认定发生变化。
蒋:规定持有型犯罪是严密刑事法网的一种方式,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是否会导致对犯罪的轻纵呢?针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批评多聚焦于此。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确立的新罪,1997年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吸纳了补充规定的条文,确认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司法实践中,许多贪污贿赂犯罪中,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往往为最后查实的贪污贿赂犯罪数额的数倍,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较贪污罪、受贿罪的刑罚幅度相差巨大。以两起较为有名的贪污案件为例:湖南省的欧阳松,家庭财产价值人民币389万多元,其中所谓的“灰色收入”就有334万元,占全部财产的85.6%,其中有147万多元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占灰色收入的44%;又如安徽省阜阳市的肖作新夫妇,共有财产1962万元,其中竟有1300多万元属于来源不明的财产。只要行为人坚不吐实,司法机关在无法收集证据情况下便只能按照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论处。客观上,这便是一种轻纵。
黄:司法实践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规定导致轻纵犯罪是客观的,也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该罪的主要批评之一。从严格的罪刑法定而言,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规定是有利于被告人的,它设置了较高的起刑点,即达到30万元才予以追诉。但从我国反贪污贿赂犯罪的实际出发,规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适宜的。我们前面提到规定下游犯罪可以严密刑事法网,这仅仅是其中的一项功能,通过保留对刑事犯罪的永远追诉权来完善刑事法网是规定下游犯罪(包括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等持有型犯罪)的另一项重要功能。举例而言,行为人非法制造、买卖枪支,如果没有对下游犯罪(非法持有枪支罪)的判决,一旦超过非法制造、买卖枪支罪的追诉时效,便无法再予以追诉。但是,如果认定为非法持有枪支罪,则只要掌握证据便可以随时以上游犯罪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加以处罚。
蒋:您的意思是,国家通过规定持有型犯罪(下游犯罪)保留对上游犯罪的永久追诉权。实体立法上对追诉时效作了严格的限制,即按照法定最高刑规定各罪的最长追诉时效。但程序立法上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为追诉时效的延长提供了渠道。比如:刑法第八十八条规定: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既然立案侦查的都可以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实际上已经追诉的行为,审判监督程序更没有任何时间的限制。
黄:纠正错误判决是审判监督程序的一项重要功能。从诉讼法的角度来看,刑事审判监督程序任何时候都可以提起。试举一例:假定一人被判持有毒品,最后发现为制造、运输毒品,20年后还可以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也就是,先按轻罪(持有型犯罪等)来处刑,如果证据突破则按审判监督程序来启动。通过这样一种设置保留了国家司法权的权威,同时完善了刑事法网。
蒋:持有型犯罪的构成明确而易于认定,棘手的是持有型犯罪涉及的罪数问题。一般而言,先前的对持有对象的取得行为属于非法性质,它同后置的不法状态之间不存在“结果牵连犯”的关系,仅仅是一种行为造成的事后状态。这种事后的状态与先前的取得行为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如果对先前的取得行为定罪,便不能再考虑对事后的状态定罪。反之亦然。正是因为先前的取得行为与后续的持有行为成立两个相对独立的行为,如果原审判决已经认定为持有行为和持有型犯罪,一旦发现该持有状态为某种犯罪造成,必须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
黄:持有型犯罪也不能完全与罪数没有关系。如果查清上游犯罪,且持有的对象全部来自某种犯罪,比如以前认定为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后被认定为贪污所得,非法持有的枪支为买卖或制造形成,则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认定为贪污罪或制造、贩卖枪支罪。但司法实践中并不如此简单,举例而言,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1000万元,通过司法机关查证:200万为贪污所得,300万为受贿所得,通过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定罪,应当认定为贪污罪、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实施并罚。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黄京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博士 蒋熙辉

 U633687664
U633687664
 U182637395
U1826373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