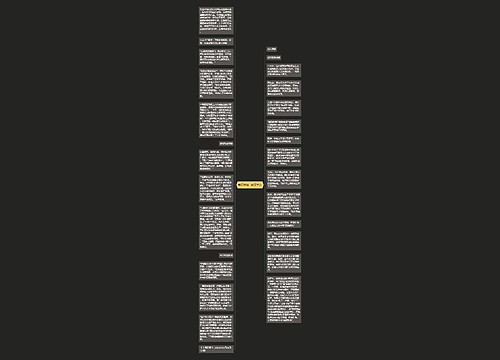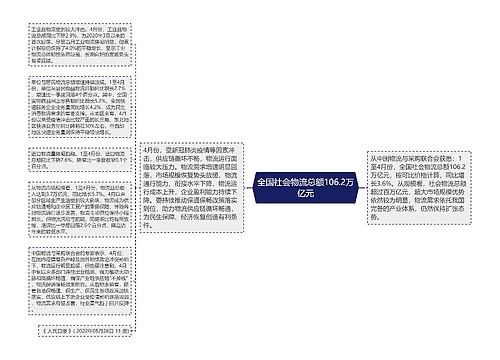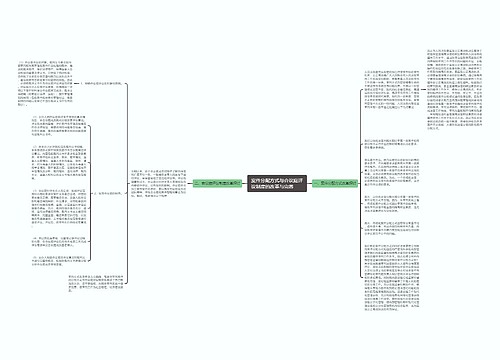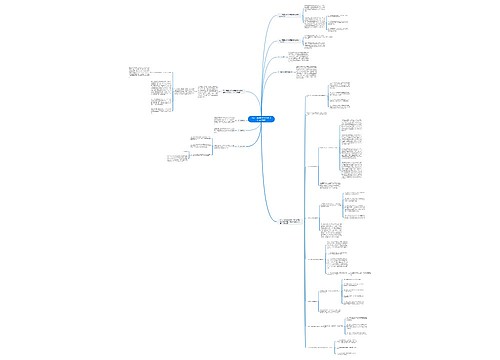[①] 包括律师和其他辩护人,在司法实践中主要是律师。国内已经有因为会见限制被推上被告席的案例。某律师在接受侦查阶段委托后,该侦查办案的公安机关拒绝安排律师会见,律师找到人大、政法委及公安局的领导,其会见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出于无奈以该公安机关行政不作为为由起诉到法院。参见吉林王海云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海云撰文《凄言苦语话刑辩》:《中国律师》2000年第11期,P47.据报刊载,2002年3、4月份该案经二审以某律师胜诉告终。笔者在对律师会见的问题进行调查时,也曾听介绍因审查起诉阶段的会见限制也有律师声言要告诉的情形。会见限制在辩护律师心中的地位可见一斑。笔者在撰写本文的过程中以及在撰文遇到阻力-当然主要是基于对法律和实践的结合点的思考阻力时,也不禁想,仔细考问自己的司法理念的话(排除掉检察本位思想的妨碍)检察官们会有何感念呢?
[②] 可参见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p101.
[③] 在美国,律师也有着各种褒贬不一的外号,如hired guns、shysters、professional knife throwers、limited purpose friends、social engineers、champions for social justice等。
[④] 不从程序上开放,不从骨子里制约,任何枝节的改革只是事倍功半。看不到程序设计的抵御权力滥用方面的作用,认识不到程序是具有抵制恣意的人治的干扰而在分权方向上保持司法良性动作的安全阀,看不到程序是决定法治和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正是程序设计方面的根本缺陷。参见王圣扬、孙世岗《侦查阶段律师辩护工作的理性思考》,政法论坛,2000年第2期p95-96.
[⑤] 参见马贵翔:《刑事诉讼对控辩平等的追求》,中国法学,1998年第2期,P103.
[⑥] 参见马贵翔:《刑事诉讼对控辩平等的追求》,中国法学,1998年第2期,P102.
[⑦] 参见熊秋红著:《刑事辩护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P285.
[⑧] 有意思的是,辩护律师即便要向案件的承办人反映其对于案件应做不起诉的意见也是困难的,为了避免办案人员与律师有“私下交易”,有的检察院规定了案件承办人与该案辩护律师不得接触,辩护律师只能与接待人员交谈,而接待人员相对于案件是超然的,只起居中转达的作用,辩护律师的意见则在转达中反映,其意见可以起到的效果可想而见。更有意思的是,被害人委托的代理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应与公诉机关是一体的、均是控方-与案件承办人的会见与交换意见也是困难的,其面临的待遇是与作为敌人的辩方-嫌疑人委托的辩护人尤其是律师-大致相仿,让人感觉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律师接待制度本身应当是为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取得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而建立的,倘若中间夹杂一些地方土政策则变成了有意阻挠刁难制造控辩双方误解或相排斥的罪魁祸首,失去了其存在的最基本意义。
[⑨] 在有些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已经十分明确,证据也是确实充分的,其也一直供认不讳。即便是这样的案件,进行辩护也是必要的,绝不能因为胜算渺茫就剥夺了一个公民获得辩护的权利。在如山铁证中发现漏洞并非绝无可能,实践中也不乏这样的成功案例。获得辩护,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只有不加区别地保障这项权利,才能最终维护我们自己及至整个人类的自身价值、尊严和自信。控辩双方从各自的立场出发,针锋相对地提出各自的证据和理由,表明自己的观点和意见,这样能够弥补漏洞,纠正错误,使案件的事实真相逐渐显露,依此形成正确的判断。参见甄贞等著:《程序的力量:刑事诉讼法学研究随想》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p82.
[⑩] 1990年9月7日通过,第8条规定:遭逮捕、拘留或监禁的所有的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不迟延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这种协商可在执法人员能看得见但听不到的范围内进行。
[11] 检察机关自行侦查的案件在押犯罪嫌疑人家属聘请的律师受到以犯罪嫌疑人无聘请要求为由的会见限制处遇较为突出。事实上,很多会见限制的原因都是从某个自侦案件的处理结果上延伸出的“地方政策”。在调查时,笔者惊异地发现“判例法”的痕迹。
[12] 现代刑事诉讼理论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国家的司法机关一样,也具有刑事诉讼的主体地位,二者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所担任的诉讼角色不同。人性中包含着天赋的尊严,任何人都无权把别人当作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不能把罪犯看作纯粹的客体,而应该认识到,他也是具有同样的尊严的,自我决定的人。被告人有权以主体身份参与诉讼,在辩护人的帮助下,尽其所能地防御控方的攻击,从而积极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尊严与权益。参见甄贞等著:《程序的力量:刑事诉讼法学研究随想》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p81.
[13] 即便是在押犯罪嫌疑人不聘请律师为其辩护,如家属已聘请也应有确认程序,而如何确认、确认时间、地点也是存在诸多争议,但至少检察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确认委托,而检察机关单方确认也被认为欠妥。如将委托告知程序当作委托确认程序则更是不妥当的。笔者认为,律师单方径行到看守所进行确认也是可行的。
[15] 在笔者对文章进行修改的过程中,在本人工作的机关门口的法律宣传栏欣喜地看到一篇宣传文章-《刑事官司怎么打》,文章介绍了刑事诉讼中几个阶段聘请律师的问题。宣传部门在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方面大做文章,另人欣慰。笔者不禁想,现在是法制张扬的时代,如果司法机关的执法机构、执法人员把点子用于提高工作能力、用于解决办案质量的问题上,而不是在限制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方面做文章的话,其意义绝不仅仅在于有效地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更在于其有利于法治的实践和推进。

 U633687664
U633687664
 U582679646
U582679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