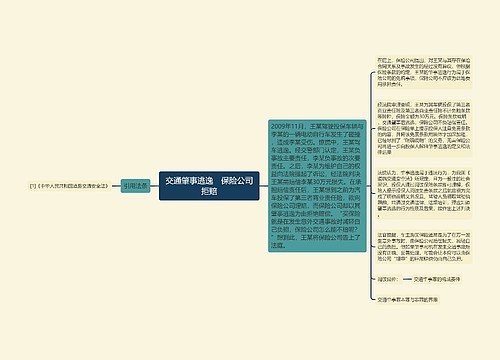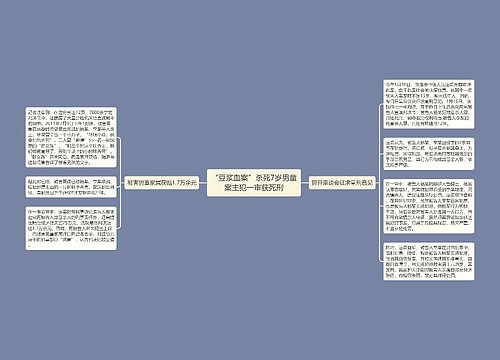从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来看,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的转化型抢劫罪构成要件有三:其一,本罪的前提条件是行为人先有实施盗窃、诈骗、抢夺罪而非他罪的犯罪行为。在转化型抢劫罪的情形下,先行实施的盗窃、诈骗、抢夺行为,不论其既遂、未遂或取得财物数额的大小。其二,本罪的客观条件是行为人在先行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后,还必须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其所包含的手段条件即暴力或暴力威胁行为;时空条件即这种暴力或暴力威胁行为是当场实施。这里的“当场”一般指行为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的现场以及被人追捕的整个过程和现场,即本罪的暴力或威胁行为,与先行的盗窃等行为在时空上具有连续性和关联性。其三,本罪的主观条件指暴力或暴力威胁的目的是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其含义分别指:行为人为保护已经到手的赃物不被追回;抗拒对行为人的抓捕、扭送;毁灭作案现场上遗留的痕迹、物品等,以免被提取成为罪证。如果在盗窃、抢劫、抢夺过程中并非出于上述目的,而是出于强行非法占有目的,则符合一般抢劫罪的构成要件,不应按转化型抢劫罪论处。然而在转化型抢劫罪中,如何理解“窝藏赃物”容易引起歧义。笔者认为,我们应当跳出原刑法窝藏赃物罪中的“窝藏赃物”理解上的局限性,不仅关注其通常或形式上的“为赃物提供隐藏处所”之内涵,更要看到其实质意义上对“对赃物的继续控制、占有和支配”。
高法《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抢劫案件解释)明确规定,“对于入户盗窃,因被发现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入户抢劫”。这一规定包含了本案中行为人在卧室内窃得财物后进入客厅但仍属户内,没有离开作案现场的情形,因此,本案中黄某的行为具备“当场施暴”的客观要件。考虑到本案定性上的分歧,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假设余某的暴力行为是在被发现后实施的,则依抢劫案件解释定性为入户抢劫没有疑问。本案的问题就转化为:余某因担心被发现但客观上并没有被发现时采取的故意伤害行为,是否也属于入户抢劫。质言之,抢劫案件解释是否意味入户盗窃转化为入户抢劫,只在“被发现”后当场施暴成立,而未被发现,如本案受害人还处于熟睡状态下的当场施暴时则不成立呢?从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来看,这一问题显然不在立法者的考虑之中,抢劫案件解释也并没有作此限缩性解释。该解释的意旨,在于明确窃取被人发现时行为人犯意的转化,并在新犯意的支配下采取过限行为(即抢劫),这同时也是对“窃取不限于秘密窃取”实践及其理论的回应。另者,相对于本案中的情形,对常态和典型的行为而不是非常态和非典型的行为作出规定,本身是立法的一般规律。在本案情形下,我们要重点考量的是施暴是否当场和窝赃目的的有无,分歧主要集中在对后者的认定上。笔者认为,依日常生活经验,行为人“因担心余某醒来后发现被盗的情况”并决意采取故意伤害行为,其最终维护对赃物的非法控制与占有的主观心态是显而易见的。从另一角度看,抢劫案件解释也没有着眼于对行为人主观方面的探究,只要入户盗窃满足“因被发现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就构成入户抢劫。应当明确的是,该解释对入户抢劫的认定,包括直接构成入户抢劫和转化型入户抢劫两种情形。在后一情形下,其客观方面包括财物已窃得后被发现,行为人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情况。该客观方面所对应的主观方面则表现为由盗窃向抗拒抓捕和(或)窝藏赃物的犯意转化。就已窃得财物后的转化情形而言,从“被发现”到本案中的“担心被发现”,情节虽有别,但行为人在窝藏赃物的最终主观目的上则无二致。客观情节上的这一差别,不影响对该行为的刑法定性与评价。
回到本案,黄某在窃得财物后由于担心被害人醒来发现被盗的情况,出于保护已经到手的赃物不被追回,维持其对赃物的继续控制、占有与支配,实施进一步的伤害行为,其窝藏赃物的主观目的不言自明。需要说明的是,对体现黄某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性的这一转化行为的认定,不受被害人是否或可能有抓捕与追回的意图或行为的影响。换言之,本案中的余某虽然处于熟睡状态,不可能实施抓捕并危及黄某对赃物的控制、占有和支配,但黄某此时的暴力行为所体现的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性,与抢劫案件解释中的入户盗窃被发现后,随即发生或可能发生的抓捕与追回意图或行为下的当场施暴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且其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整体来看,黄某的行为具备转化型抢劫罪的三个构成要件,符合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

 U633687664
U633687664
 U582679646
U582679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