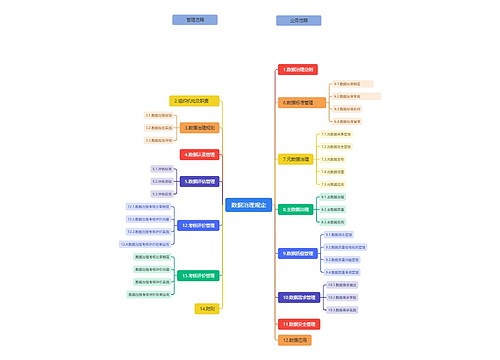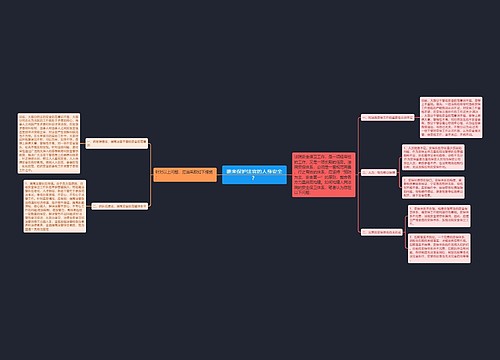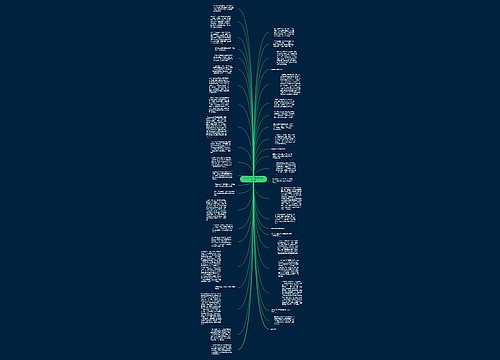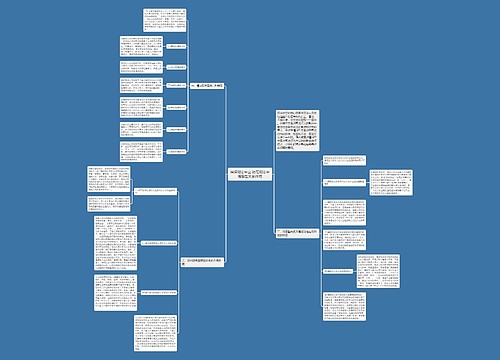学界期盼已久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终于确立了,而且直指刑讯逼供和冤假错案。新规的出台意在遏制刑讯逼供、杜绝冤假错案,然而仔细推敲《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就不难发现,新规开出的药方,能够“治疗”冤假错案,但是对刑讯逼供的“疗效”却不得不让人产生怀疑。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能打击刑讯逼供,它是以权利保护为中心的立体预防机制,目的在于遏制非法取证行为。说它以权利保护为中心,是因为任何种类非法证据的排除依据最终都是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中关于公民权利的规定;说它是立体的预防机制,是因为它不是单一的规则,是涵盖各项被追诉人权利的多个规则,而且这些规则之间互相补充,连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以美国为例,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情形包括:非法搜查、扣押的证据,非法监听的证据,非法获取的供述,违反正当法律程序取得的证据,侵犯被告获得律师帮助权而取得的证据,除了以上这些直接侵犯被追诉人权利取得的证据之外,还包括衍生证据,即“毒树之果”。
欧洲的情形与此相差不大,它是以《欧洲人权公约》规定的权利为基础,以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为补充建立起来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保护被追诉人的权利为中心,各类别非法证据的排除为主要架构,衍生证据的排除为外围措施,形成一个完整的、立体的防御体,保护被追诉人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其目的在于根除侦查人员的非法取证行为。美国联邦法院1914年在首次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WeeksvUS案中指出,只有采用激进且务实的手段,即从根本上将违法所取之证据予以排除,方能彻底铲除侦查人员违法取证的诱因,使人民的宪法权利获得切实保障。
非法证据排除的所有规则自成一个体系,如有一处缺失,则会为人权保障留下漏洞。举例来说,如果“毒树之果”可以被采纳为证据,那么侦查人员就能达到其目的——成功结案,完成工作任务,这就为侦查人员的违法取证行为开了一道口子,因为只要能够从非法获取的证据中找到其他证据——这往往很容易——就能够“一个证据倒下去,千万个证据站起来”。
《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就缺失了保护某些权利的措施和某些保护权利的措施。根据这一规定,就被告人一方而言,只有刑讯逼供取得的供述在排除之列,与美国和欧洲的保障机制比较起来,充其量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侵犯其他权利而取得的证据和衍生证据都不在排除之列,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措施,其功效显然比不上成体系的保障机制。
在这一规则之下,我们可以假设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通过刑讯逼供得到的供述是假的。根据口供的内容找不到其他相印证的实物证据、证人证言,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那么供述可能在批捕阶段、审查起诉阶段或者审判阶段被排除,这能够减少错捕、错判。而且只要不造成错判,通常就不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也就不会追究取证人员的责任;第二种情形是通过刑讯逼供得到的供述是真的。根据嫌疑人的供述找到了相应的实物证据,那么供述可能被排除。可是即使口供被排除了,但实物证据也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在第二种情形中,只要不发生重伤或死亡,实施暴力的人员通常也不会受到处罚,根据修订后的国家赔偿法,这种情形下没有发生错案,追究机制不会启动。即使当事人依据国家赔偿法申请赔偿,也很难举证。因为在判断证据是否排除时,公诉方承担着大部分举证责任;但在申请国家赔偿时,通常认为举证责任由申请人承担。
从以上分析来看,刑讯逼供的动因并没有被铲除,两个规定的出台对抵制冤假错案,尤其是死刑案件中的冤假错案有很大帮助,但是在遏制刑讯逼供方面却力不从心。世界主要国家都已经采用“立体战”的技术来铲除包括刑讯逼供在内的违法取证行为了,而我们今天却还端着“汉阳造”来对付刑讯逼供,其效果就不容乐观了。
刑讯逼供的发生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有罪推定观念继续主宰,用于侦查设备配置和人员培训的经费不足,整体侦查技术水平偏低,侦查人员整体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犯罪高发地区警力配备不够,命案破案压力极大,侦查阶段辩护律师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以及法律规定存在疏漏等等,所以我们也不可能指望一两个规定的出台就能扭转乾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