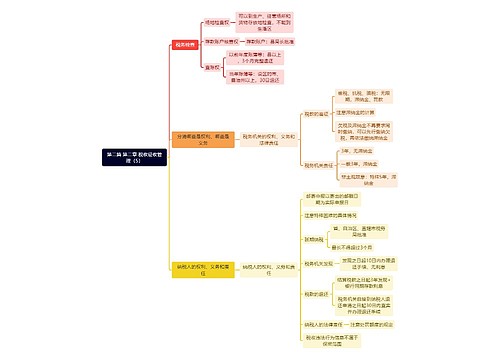人们对《征收条例》所抱的期望是约束地方政府侵害城市居民和农民权益之手,缓解社会冲突。而征收条例要收到这样的效果,就必须通过条文规定,通过制度设计,确保征收仅是一种例外。
这一点十分重要。长沙早就通过地方法规,把政府获得土地的方法从“拆迁”改成了“征收”。但在长沙,民众的土地流转之权益与其他地方一样脆弱,征收所引起的纷争、冲突,一点也不比其他地方少。
这是因为,政府与土地发生关系的基本制度框架没有发生变化,政府运用强制力进行征收,仍然是土地流转的基本形态。不管是政府改造旧城区,还是在乡村地区进行城镇化、工业化,土地的流转基本上是通过征收的方式进行的。而只要政府的强制力进入流转过程中,又缺乏必要约束,它就必然随时可能表现出暴力的一面。
从这个角度看,废除拆迁条例,制定征收条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字游戏,背后涉及的乃是土地流转形态的一个根本变化。
回顾一下拆迁一词的起源,就不难明白这一点。笔者印象中,上世纪80年代就有拆迁。当时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一切要素归政府:干部工人是国家的终身雇员,政府负责解决干部工人的住房问题。房屋是单位分配的,因而也属于政府,所用土地也是国家的。当房屋破旧无法居住,或者城市建设需要让路时,政府会组织拆迁,自然会解决干部工人的居住问题。当时,民众对什么都没有确定的产权,政府对土地、房屋的强制性权力之祸害无从表现。
现行拆迁制度是一个晚生的怪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土地已经开始货币交易,人们开始拥有对诸多物品的产权,包括城市居民对房屋、农民对土地已经拥有相当明确的产权。拆迁制度不顾这一现实,不承认民众的这些产权,而让政府的强制性权力主宰土地流转过程。它规定,城市中居民与政府之间发生的土地流转,均以拆迁方式进行,拆迁的终极主角就是政府。
随后,中国进入快速城镇化、工业化阶段,城市土地开始大规模流转,拆迁因之遍地开花。近两年来,拆迁也被地方政府扩大运用到城市近郊区。由此出现了世界上最为奇怪的现象:大多数土地流转是商业之需,但这些土地流转大多数却是借助政府的强制力进行的。总是有人说,中国的市场化已经达到多高程度,但中国真的有一个土地“市场”么?一个东西,人们用货币交易它,并不等于这个领域就有了市场。
或许可以说,中国模式的优势在此,致命的问题也在此。拆迁制度的优势在于,政府可以廉价拿到土地,可以在最短时间内拿到土地,因而可以快速推动城镇化、工业化。问题则在于,土地收益的分配严重不公,土地流转过程中伴随着广泛的冲突,同时,土地的利用效率十分低下,长期大规模的土地经营、土地财政,让政府的行为模式日趋严重扭曲。也就是说,拆迁制度已经成为治理秩序的最大麻烦制造者。因此,拆迁制度必须废除。这也正是有关立法部门冲破土地既得利益集团的重重阻力,两次就征收条例向公众公开征求意见的用意所在。
而废除拆迁制度的关键,就是把政府的强制力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出场的机会,限制在最小的合理范围。征收条例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也即,只有当公共利益需用土地的时候,才可以启动以政府强制力为依托的征收程序。这一规定的言外之意是,正常的商业性的城镇化、工业化用地,必须以正常的市场交易的方式流转。这个言外之意才是征收条例的要害所在。我已撰文《制订一个统一的征收条例》(12月18日)提出,为醒目起见,征收条例应当在总则中加上一条确定土地流转中自愿交易优先的原则。
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甚至普通民众可能立刻提出一个问题:市场怎么交易土地?其实,《物权法》、农村土地的相关法律等已经解决了土地交易的前提:市民对城市土地拥有建设使用权,农民对宅基地和承包地拥有永久或者长期使用权。人们有权交易这些产权,城镇化和工业化过程中需用土地的人,应当就此产权与持有人进行谈判,双方定价交易。除了用途管制、征税和交易监管外,这些交易与政府根本无关,政府没有资格充当交易主体。
从这个意义上说,征收条例只是对《物权法》一个小小的补充。拆迁条例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征收条例的前提是,《物权法》真正发挥作用,它所确定的民众的土地权利,民众可以自由地支配,在合乎规划和用途管制的情况下可以自由交易。即便公共利益所需的土地,也应当首先在这些法律框架内解决,征收只是最后的手段。
因此,在讨论征收条例的时候,人们不能不思考,民众的土地权利如何在更大范围内获得更为有效的保障。否则,征收条例即便出台,也不能改变什么。

 U280380801
U280380801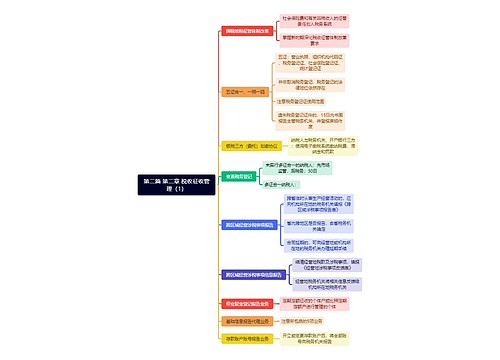
 U280380801
U280380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