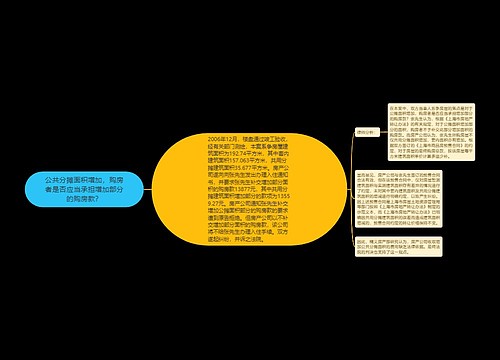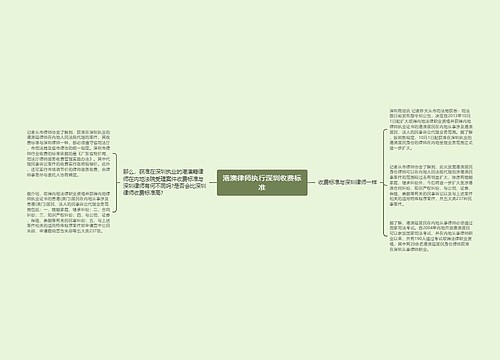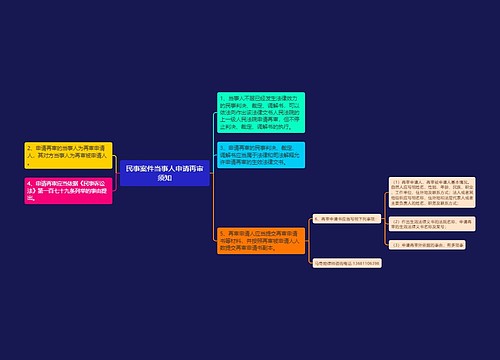律师的权利大致可以分为具体执业权利与职业保障权,两者相互配合,共同支持着律师有效地履行各种法定职责。所谓执业权利,即会见权、调查取证权、发表意见权等律师在诉讼中实施的权能。而职业保障权,则是指保障律师顺利执业的法定权利,包括独立自由执业权、拒证权、拒绝搜查与扣押权、执业言论豁免权等。律师法的本质应当是一种职务法,既应当体现律师资格、执业管理、行业管理等方面的管理内容,也应当体现确保律师依法履行律师职责的职业保障方面的内容。因而,职业保障权由其来加以规范是再合适不过的。至于执业权利,涉及到具体程序中的诉讼行为,由刑诉法的辩护制度一章来规范,无疑是最好的“归宿”。
然而在2007年修订律师法之时,这种职能的合理分工未能得到体现,条文中出现了大量辩护律师执业的直接授权,包括会见权、阅卷权等重要的辩护人权利。很显然,律师法“越界”了,这种做法混淆了律师法与刑诉法基本的立法功能,也为今日两者之间的尴尬局面埋下了伏笔。当刑诉法再修改完成之日,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两者的关系,而对于矛盾、冲突之处,只能通过再次修正律师法的内容来加以协调。故而,为了使辩护制度顺畅运转,必须对律师法再动个“小手术”,其基本前提是正确认识律师法与刑诉法之间的分工关系。
在《中华人民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辩护制度的修改大量吸收了2007年律师法中涉及执业权利的内容。例如,辩护律师提前至侦查阶段介入诉讼程序;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可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坦率地讲,律师法中对于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在内容上是值得肯定的,对于保护已然“岌岌可危”的律师辩护权,也是大有裨益的。因而,刑诉法将这些内容移植过来,是一种节省立法资源的明智之举。
不仅如此,刑诉法还对辩护制度作了一些调整和突破。例如,对于辩护人涉嫌犯罪的情形,刑诉法更进一步地要求承办其辩护案件的侦查机关必须回避,以防止对律师的职业报复。而对于阅卷范围,“案卷材料”的说法较之律师法中的“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更加明确,而较之“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也更具可操作性。这些都是刑诉法在借鉴律师法的同时,加以补充、完善的结果,体现了辩护理论的持续发展。
当然,刑诉法中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第46条关于“律师保密权利”的规定,这个条款压根就不该出现在刑诉法中,因为这个条款是以维系律师与客户间的信任关系作为存在基础,是典型的职业保障权利。由刑诉法来规定显然不及律师法作统一规范划算。该条款的存在表明,律师法与刑诉法依然没有实现合理的分工与衔接,对于两者分工的认识依然存在误区,两部法律依然在“各干各的、自说自话”,理论界与实务界依然未能统一思想。
两部法律之间的不协调不能一直维持下去,必须尽快予以调整,而在刑诉法的修改工作完成后,律师法也应当有所“动作”。
首先,使律师法回归其功能本义,删除涉及具体执业权利的内容,从而化解两部法律的矛盾之处。对于这部分权利,律师法可以做出概括性的授权,即明确规定律师在辩护活动中享有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发表意见权、出席法庭活动等权利,且上述权利不得受到非法妨碍。而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操作,律师们只需完全遵从刑诉法的规定即可。
其次,借助刑诉法再修改的契机,强化对律师执业的保障。例如,尽管在调查取证权利上,刑诉法并未作出调整,但是律师法可以从职业保障的角度去加以完善,明确要求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单位及个人对于律师的调查取证予以配合和协助,从而保障调查取证权的行使。这种规定不仅仅有利于刑事辩护活动,对于律师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等活动中有效开展业务也不无好处,由律师法“出面”规定可谓“实至名归”的。
上述步骤看似行云流水,推行过程中也不免会阻力重重,稍有不慎便会走歪了路径,阻碍了辩护制度的发展与进步。因而,对于律师法与刑诉法的衔接工作,需要有正确的理论认知作指引,方能走向通途。

 U633687664
U633687664
 U482683014
U482683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