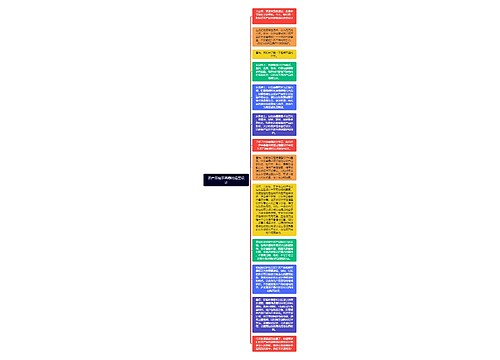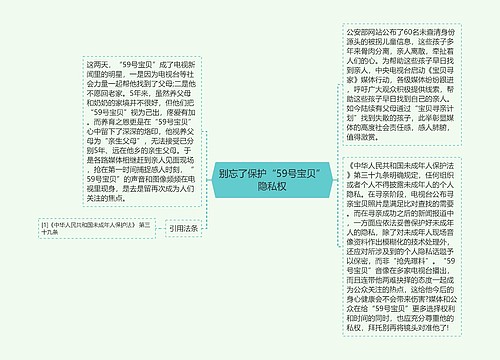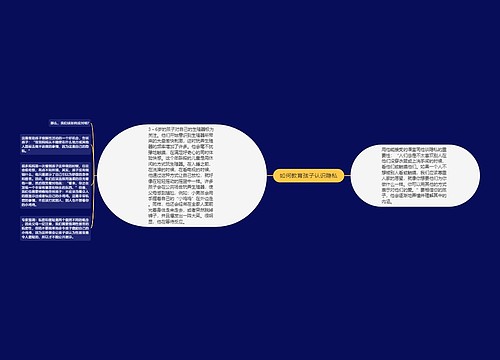日本上性教育课时,采用人偶做教具、修改传统儿歌的方式来讲解和传授性知识。
近年来,荷兰国家健康研究所决定推出幼儿性启蒙教育,这个计划安排在万物回春的季节,号称“春之痒”计划。在学校老师发给家中的“春之痒”行动倡议书中写道:“我们会和孩子谈到春天的动物和植物,会去农场喂养新生的小羊。我们也将谈到男孩和女孩的区别,谈到什么样的身体接触才是愉快的;还会谈到小孩的出生。请您尽快将有关他们出生的照片带来学校。这是非常重要的话题,需要学校和家庭共同完成。”
性知识是义务教育阶段必修课,课时一学期。瑞典是世界上最早开展性教育的国家之一,上世纪30年代就成立了全国性教育组织。从1955年起,性知识成为义务教育中的必修课。在幼儿园时代,老师就会教孩子用避孕套吹气球,中学还会为学生免费提供避孕套。为期一学期的性教育课内容,包括新生命如何出现、避孕套如何使用、怎样发现早孕等;老师还会和学生探讨怎样与异性相处。瑞典是世界上刑事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也是未婚少女妈妈最少的国家。
记者调查中发现,小月家人在遇到困难后,不得已向当地的一些媒体求助。而这些媒体为了能让小月的事更广泛地引起社会关注,也为了尽快地为她募到一些救治款,把她的住院地址甚至病床号等信息都在电视上公之于众了。
据悉,这种做法的确引起了当地市民和读者的关注,一些人带着钱财、水果、玩具等到医院看望小月,给小月及其家人送去很多温暖和关爱。小月的姑姑告诉记者,每当小月看到有人到医院病房看她时,她就会表现得很高兴,甚至每天都在盼望着;如果一时没有人来,她就会显得很失落。
此种情况令人担忧。据了解,性伤害案件的当事人会因为他们的事件引起社会的关注和人们对他们的同情,使得他们陶醉于糖果、礼物、花朵、补偿金等之中。他们误以为这一切是由“性”所带来的,往往会影响其成人后的性观念。很多人走上了再次用“性”换取所需的道路。如果说首次是被动的性侵害引起了社会的关注,这第二次,就是他们主动地以性去做交易了。在国外,人们往往刻意淡化对性伤害案件当事人表现出特殊的关注,以免他们得出错误的结论。
媒体不恰当的宣传报道可能导致对当事人不经意间的伤害,这是被称作“儿童性伤害中的‘二次伤害’”的一部分;“二次伤害”已经成为一个专有名词,特指在儿童性伤害案件发生后,来自社会、司法、媒体等各方面的以对孩子关心、爱护的名义,在新的层面上给孩子带来的又一次伤害。
比如,在处理相关案件的过程中,警方人员会多次穿着警服、开着警车、亮着警灯,去受害者家中调查取证。又比如,为了尽快地抓住侵害者,有关人员会向受害孩子反复发问,以求得更多的细节,从中搜寻到破案线索。殊不知,这每一次发问引发的回忆,对当事人而言,都是又一次犯罪情境的加深。
在记者接触到的大量案例中,这样的“二次伤害”几乎随处可见;甚至包括学校和医院会在不经意间暴露孩子的隐私。
作为中华全国律协刑事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律协刑诉法专业委员会主任钱列阳说在办案过程中经常遇到此类案件。他最担心的就是,由于家长和媒体的认知与导向问题,让孩子从反面获得了教训,或者造成更进一步的心理伤害。
西方国家的一系列研究显示,儿童性侵犯受害者中占20%至40%的人,没有出现性侵犯所带来的精神症状。而修复创伤的关键,则是受害儿童能否从家庭成员,特别是父母那里获得更多支持。
他说生活中很多案例揭示,父母或者监护人一旦面对孩子在生活中遭受侵害,首先想到和做到的就是追究责任、讨要说法、索要赔偿……至于孩子在受到侵害后的心理需要、处理问题时带给孩子的心理感受,统统没有想到。我们的家长并不知晓,首先是要保护孩子,一切以把对孩子的伤害降到最小最低为终极目标。这其中也包括对那些未成年的所谓“加害人”的保护。
记者在调查中得知,在事发之初,小月奶奶带着孙女去“邻居哥哥”家核实情况时,小男孩还是承认自己做法的;而且他的家人也拿出了3000多元治疗费给小月;然而随着事态的发展,随着小月病情的加剧,特别是随着后来媒体的介入,巨额医疗费加上负面的社会评价,“邻居哥哥”已经开始否认曾经的作为……
钱列阳分析说:“其实类似的幼儿探查性器官事件在幼儿园、小学常常出现,我们不应对此类事件大惊小怪。‘邻居哥哥’的变化不管是他自己被吓怕了,还是出于家长的授意,这都是很可悲的。要知道,一个事件出现后,我们面对的不仅是弄清事实、搞清责任、索要赔偿;对于一个孩子的诚实、守信、真诚等的教育,也是一个孩子健康成长环境中不可或缺的。”
钱列阳再三强调并且请求媒体在介入此类事件的报道时,一定要从专业角度,很理性地探讨深层次的问题,千万不能以情绪化的态度,通过描写女孩的惨状、渲染男孩手段的残忍,将读者引入歧途。
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召开的妇女儿童维权工作国际研讨会上,人们对儿童遭受性侵犯后在侦查、起诉及审判等司法和执法过程中,有可能遭受的来自多环节的“二次伤害”展开了讨论。专家指出,正是由于各种不良做法和心态为长时间犯罪提供了机会,因此,必须直面“二次伤害”,才有可能减少对青少年的性侵犯事件。
从1998年至2002年,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妇儿心理法律咨询服务中心共受理儿童性侵犯个案29起,受害人数达32人。被害儿童中,年龄最大的16岁,最小的只有3岁。29起个案中,有两起是数名女童同时被害。29起个案中寻求司法救助的有13起;“私了”不成又转公力救助的有7起;为孩子名声以及今后生活不愿控告的有9起。在29起个案中,证据保全完整,犯罪人得到刑罚的有7起;证据被毁或犯罪嫌疑人逃走的有22起。而在前来寻求帮助的当事人中,不少人感到在寻求公力救助过程中的“二次伤害”。
“我们的法律能否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增加些对受害儿童的司法保护条款呢?因为在受害儿童司法保护程序的立法上,还存在一个空白点。要知道惩治罪犯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如果为了追求抓住歹徒这一结果,而忽视了整个过程中对受害方的司法保护,也许在追讨嫌犯的同时,就会造成对受害人的二度甚至三度的伤害。”龙思海在工作日记中这样写道。
1991年,香港的儿童性侵犯案件,仅占整个儿童虐待个案的2.6%,但1998年,这个数字飙升到30.7%。针对日益严重的事态,香港以儿童最大利益为准绳,在立法、行政、司法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实践。
从那时起,香港成立了专门的儿童保护机构:在政府的社会福利处设立了儿童保护科及临床心理服务科,对受害儿童提供服务;在警务处内部设有专门的儿童保护科,承办儿童性侵犯等案件。
在香港,有一张针对儿童性侵害发生过后的集家长、政府社工、警员、教师、医务人员等于一体的高效运转团队的保护网络。一旦程序启动,这个团队像八爪鱼一样获取并汇总受害儿童的各方面信息——身高、体重、血型、家庭状况、性格、爱好甚至日常学习成绩,然后在经验丰富的社工主持下,协商如何回应受害儿童及其家人的需要。在接受调查前,社工会告诉儿童及其家人,接下来将发生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
每一名受害儿童,都由这些受过专门训练、具有儿童心理专业知识背景的社工和警员进行询问和记录。对于年龄较小,还不能准确进行语言表达的儿童,警员们会向其提供一些人体玩具模型,模型身上的衣服可穿脱,受害儿童可通过模型,指点自己被触摸或被侵犯的部位。这些过程,都在专门的小密室中进行,密室内设有单面镜,背后有专门的录影设备,可以录下儿童讲述的全过程。
为保障孩子的身心不受伤害,法律规定,孩子不需要连续不断地遭到询问,第一次询问过程的电视录像就可作为证据在各个程序中加以运用,而且孩子不用直接出庭作证。孩子在接受调查中有家长、政府社工、教师、医务人员陪伴,以克服孩子的不适和恐惧感。
香港社会福利署还聘用专门的临床心理学医生,为受害儿童提供心理治疗。在验伤和治疗过程中,如果家长不同意,医生没有权利把结果透露给包括调查小组在内的任何人。
另一方面,从立法上为受害儿童设立特别的保护程序:为体现儿童的最大利益,香港立法院1995年颁布了一个法例,改变了以往10岁以下的孩子不能做证人和进行诉讼的状况,规定孩子不仅可以作证,而且孩子的证言不需要其他旁证材料就可以作为呈堂证供。
而如孩子需要出庭,在开庭之前,社工事先要陪伴孩子参观法庭,并用各种图片让孩子熟悉在法庭上将要见到的人如法官等,以降低孩子的恐惧心理。
中华女子学院社工系李洪涛主任,曾到瑞典和美国的法院进行过实地考察。李洪涛发现,在这些国家,对儿童性伤害案的审理、问讯,都在专门的小密室进行。房间内设有单面镜,背后有专门的录影设备,可以录下孩子讲述的全过程。
对于年龄较小的孩子,还会被提供一些人体玩具模型和标有人体器官的图纸。模型身上的衣服可穿脱,而且有人体的生殖器官。受害儿童可通过模型指点自己被触摸或侵犯的部位,也可在图纸上指点受侵犯部位。每一名受害女童,都有专门的女警或女工作人员接待、讯问、记录。
除法院之外,医院、警局等相关机构,都建有类似的密室设置,且全部采取“一站式”服务规则,即由最初接报的机构录下孩子的完整口供,供以后有关单位全程使用,以避免多机构反复询问,造成“二次伤害”。
2007年6月1日正式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6条:“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其他成年公民的共同责任。”
第8条:“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工会、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少年先锋队以及其他有关社会团体协助各级人民政府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参照上面两条,对儿童承担有法律保护责任的机构和组织加起来约有十几家,但是小月事件发生后,这个家庭所感受到的却是孤立无援。
小月现在的实际监护人姑妈何女士告诉记者,事情发生后,他们曾带着小月走访过许多部门寻求帮助,派出所、妇联和司法部门以及政府机关他们都跑过,但始终没有结果。
由于“邻居哥哥”家的态度前后发生180度大转变,即男孩的妈妈称,他们询问过自己的儿子是否对小月做过报道上说的事,孩子摇头表示“没有”。因此,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是儿子做的一切,他们在初期拿出三四千元后,开始拒绝再为小月提供任何医疗费用。据悉,此前村中一个男孩曾经目睹小月受伤害的整个过程,但后来该男孩也不肯再作证了。
小月的姑妈何女士哭着问记者:“我想不明白,我的小侄女被害成了这样,难道就只能干看着没有办法吗?难道就没有一家机构和组织应该帮助我们吗?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之后才求助媒体的。”
截稿前,记者又和何女士通了一次电话,她告诉记者目前快崩溃了,由于当地医院说没有合适的模具,小月即使现在做手术打通阴道,仍会粘连,最后只能把手术定在她十多岁发育后。要等上10年,何女士担心会把孩子耽误了,因为直到现在,小月每天仍然还有少量阴道流脓现象。
另外,当初在当地募捐来的12000元,几次手术全花光了。对于何女士来说,一方面要抚养自己10岁的儿子,另一方面还要抚养小月。她觉得,再怎么操劳也筹不起这笔医疗巨款。通话中,总有童音传过来,原来何女士是靠摆摊卖粽子、馄饨和米粉来过活。在她去给顾客打饭的间歇,小月和记者直接通了话,她说她想来北京、想看天安门,最后她用稚嫩的童声说:“做手术疼我也不怕。”

 U230224119
U230224119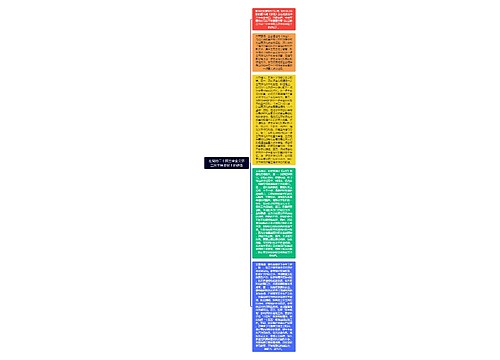
 yanice
yan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