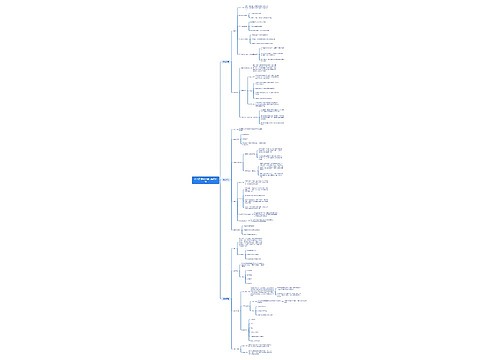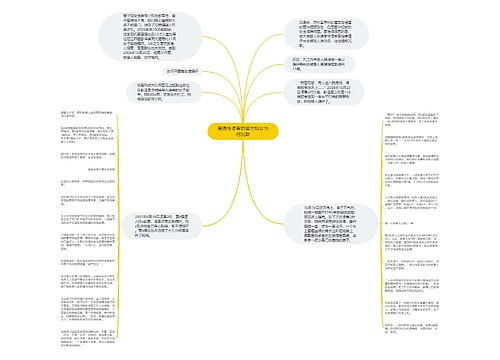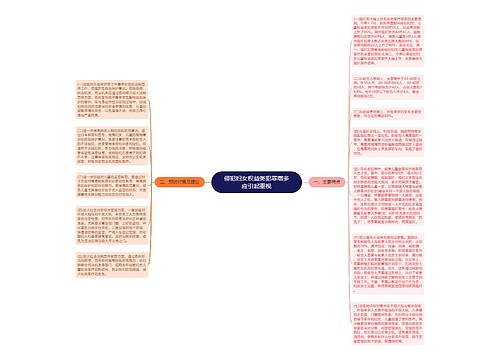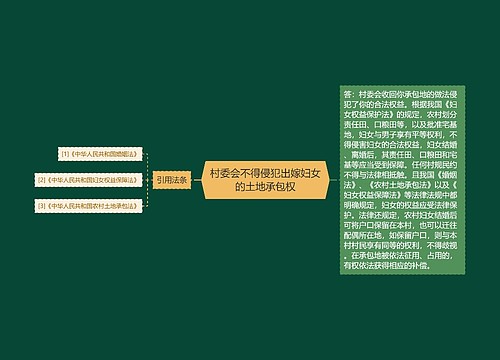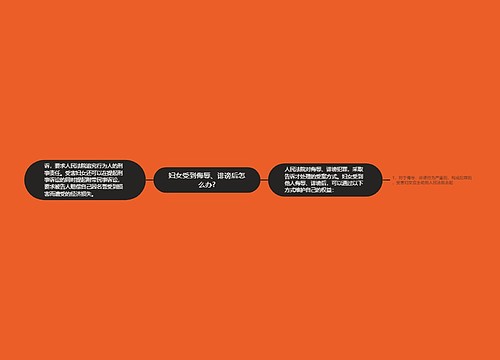关于陈某行为的定性,应当说,第一种意见是我国目前刑法理论上的通行观点;但是,通说并不必然正确,所谓的通说,如果经不起逻辑和实践的拷问,就应当接受被淘汰的命运;同时,结合社会现实对理论上的通说进行深刻的反思,刑法学说总体上才能不断向前发展,趋于完善。笔者总体上同意第二种观点,认为陈某的行为构成了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理由如下:
首先,从犯罪客体上看,侮辱罪侵犯的是他人的名誉,即采用不正当的方式降低一个人本该享有的正常的、来自社会的价值评判;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犯罪,虽然也可能会损害他人的名誉,但是,必然遭受侵犯的只是妇女性的自决权,必然令受害人产生性的羞耻心。所谓妇女的性的自决权,从狭义上说,仅指与他人发生性关系的自由;从广义上而言,还包括与性有关的其他权利。例如,在没有第三者在场的时候,对妇女实施鸡奸的行为,一般就不会侵犯妇女的名誉,但是,毫无疑问,这种行为属于典型的强制猥亵行为。可以说,是否侵犯了妇女性的自决权、是否让受害妇女产生了性的羞耻心,就构成了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和刑法第236条所规定的以妇女为侵害对象的普通侮辱罪之间的分水岭。本案陈某当众扯下李某的全身衣服,显然损害了李某正常的性的羞耻心,而不仅仅是名誉上的损害。
其次,从犯罪的客观方面看,根据多数学者的描述,针对妇女的普通侮辱罪,行为方式往往表现为言词上的诋毁、谩骂;通过书写、张贴、传阅有损他人名誉的大字报、小字报、漫画、标语;使用暴力逼迫妇女做难堪的动作,往妇女身上泼粪便等等。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的行为方式往往表现为:1.向妇女显露生殖器,并强迫妇女观看;2.强迫妇女手淫,为他人手淫,或强迫妇女观看手淫;3.在公共场所故意用生殖器顶擦妇女身体;4.针对妇女实施的抠摸、舌舔、吸吮、亲吻、搂抱、鸡奸等等其他行为。虽然两罪的行为方式林林总总,不可穷尽,但是,仔细分析不难看出,两类行为之间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界限:即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的行为带有浓厚的性的色彩,往往令人自然而然产生性方面的联想和刺激;而单纯以损害名誉为目的的侮辱妇女的行为并不具有这样的特征。正如张明楷先生所说的那样: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和目的,不管在什么场所,强行剥光妇女衣裤的行为,都属于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笔者对此深以为然,因为“强行剥光妇女的衣裤”,难免不令人产生性的联想,难免不让被害人产生性的羞耻心,这种行为已经不是普通侮辱罪中类型化的“侮辱”行为;这种行为所带来的社会危害,也已经超出了普通侮辱罪犯罪构成所预设的“危害结果”,其所侵犯的法意——妇女性的自决权,也要重于侮辱罪所保护的法意——名誉权。
再次,从犯罪的主观方面看,侮辱罪和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都属于故意犯罪,当然都需要具有犯罪的故意;最具争议的问题在于,除了犯罪的故意之外,在主观上,要成立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是否必须要求行为人还具有“出于刺激或满足性欲的内心倾向”?置换成法言法语来表述就是: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是否是倾向犯?所谓倾向犯,是指行为必须表现出行为人的特定内心倾向的犯罪,只有当这种内心倾向被发现时,才能认为其行为具有构成要件符合性。笔者认为,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不是倾向犯,不需要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追求刺激、满足性欲的内心倾向”。虽然,典型的强制猥亵、侮辱行为,事实上往往都表现出行为人具有“寻求性的满足和下流无耻的精神刺激”的动机,但是刑法学是规范学而不是事实学,什么样的因素是构成要件,只能根据刑法的规定来确定,而不能根据已经发生的事实来确定,也不能根据所谓的“人之常情”来确定。例如,强奸犯罪,行为人往往都是出于发泄性欲的动机而使然,但是,即使行为人是出于报复的心理而对他人实施奸淫,也没有理由否认此种情形下强奸罪的成立。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成立,之所以不要求主观上具有刺激或者满足性欲的倾向,其原因就在于,即使缺乏这样的主观动机,某种行为也完全可能侵犯了妇女的性的不可侵犯权,也完全可能导致被害人产生性的羞耻心,易言之,刑法所保护的妇女的性的自决权依然受到了侵犯。如果成立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一定要以“具有刺激或者满足性欲的倾向”为必要,在司法实践中就可能造成罪与刑的严重失衡。现在来比较一下这样两种情形:(1)某甲出于满足性欲的动机,在房间里将妇女衣服剥光;(2)某乙不具有满足性欲的动机,在大庭广众之下,将妇女的衣服剥光。试问:上述两种行为,哪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更严重?显然应该是第(2)种情形。可是,如果认为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是倾向犯,则第(2)种情形只能成立普通侮辱罪,根据刑法第246条之规定,最高也只能处三年有期徒刑。相比之下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第(1)种情形反而有可能面临更重的处罚,因为根据刑法第237条第一款之规定:这种情形最高可处五年有期徒刑,这明显是不合理的。由于法律语言的高度抽象和概括,在具体运用法律时势必要对法律条文进行恰当的解释,解释的方法有多种,但是无论何种解释,解释的结论恰当与否,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看通过解释,能否使得各条文之间相互协调一致。那种不顾罪与刑的协调而生硬地墨守“通说”之成规,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 表面上是在遵循刑法之规定,实际上是对刑法公正精神的彻底背离,也是一种十分僵硬的教条主义,因此必须要予以摈弃。要实现普通侮辱罪与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二者的罪刑协调,就必须要将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解释为不是倾向犯,该罪的成立不需要特定的动机和目的。
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陈某的行为不构成侮辱罪,而是构成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这一罪名,究竟是否需要分解,如何分解。其中涉及到两个问题:其一,猥亵和侮辱有无本质上的区别?其二,“强制”一词是仅仅修饰限定“猥亵”,还是也修饰限定“侮辱”?笔者赞同下面的观点:(1)必须承认《刑法》第237条的猥亵行为与侮辱行为没有区别,从司法实践来看,区分猥亵和侮辱也是不可能的;刑法第237条之所以要将猥亵和侮辱并列起来规定,其主要原因在于保持刑法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因为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是从旧刑法第160条流氓罪中的“侮辱妇女”移植过来的,本来新刑法第237条第1款仅规定强制猥亵行为就足够了,之所以仍然保留旧刑法第160条的“侮辱妇女”的表述,一方面是为了保持刑法的连续性;另一方面是为了防止人们的误解,以免人们认为旧刑法第160条中的侮辱妇女不再是犯罪行为。(2)即使要将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进行分解,也只能分解成强制猥亵妇女罪、强制侮辱妇女罪,而不是分解成强制猥亵妇女罪和侮辱妇女罪。道理很简单,只有在对妇女实施强力侮辱时,其社会危害性程度才能与强制猥亵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大体相当,才能规定在同一刑法条文之中。鉴于本文的主旨所在,对此问题不再展开论述。

 U633687664
U633687664
 U882673919
U882673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