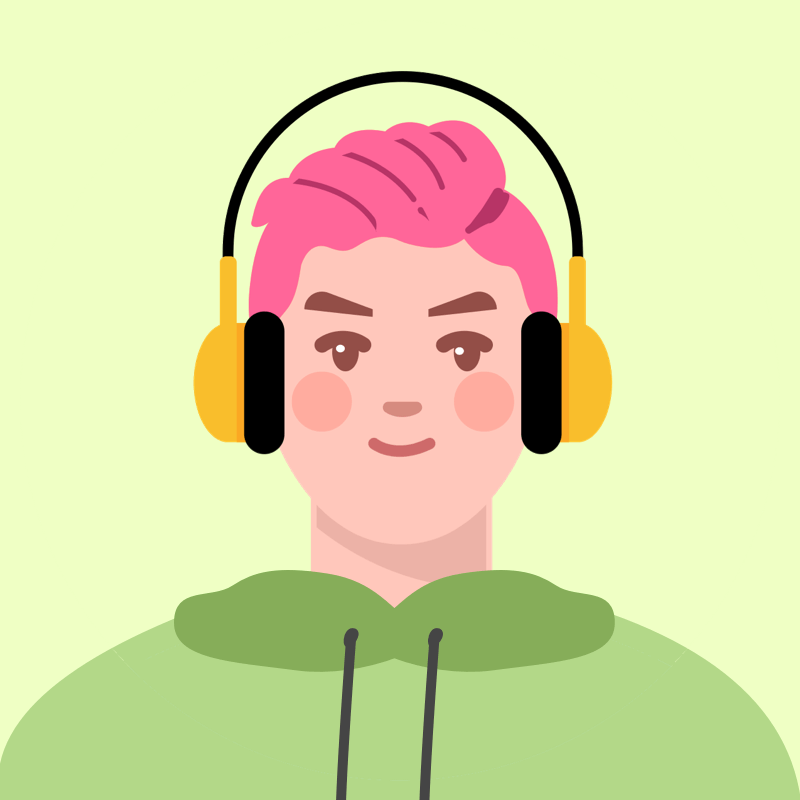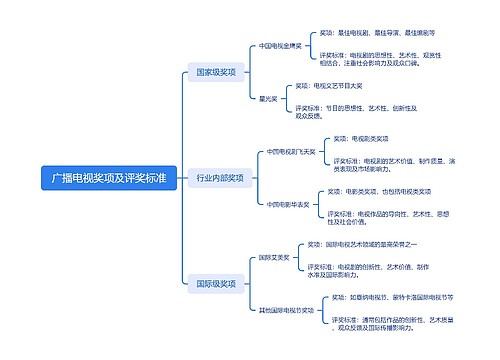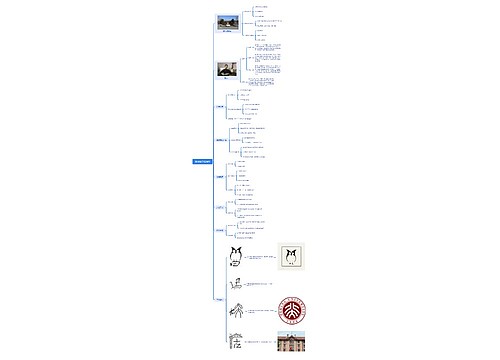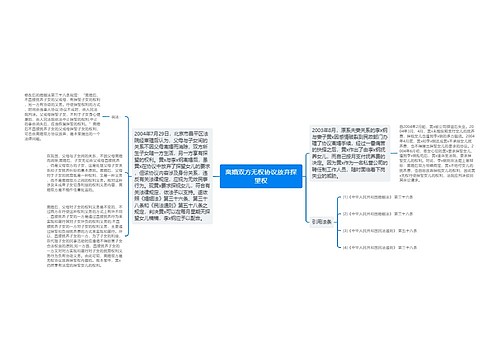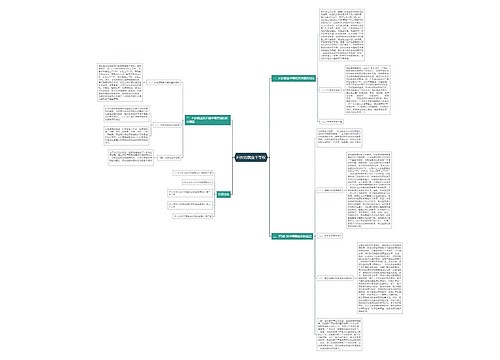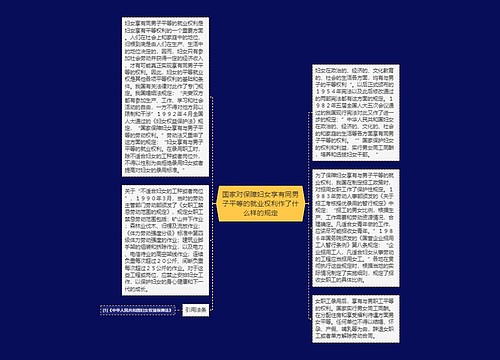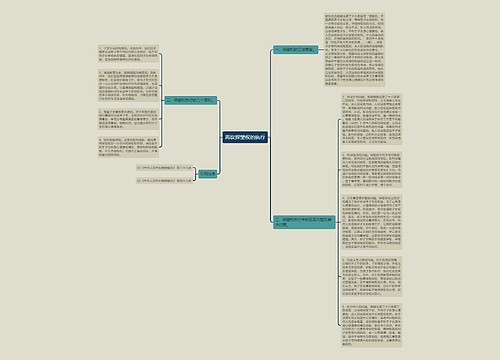杨大文、马忆南:新中国婚姻家庭法学的发展及我们的思考思维导图
深拥意中人
2023-03-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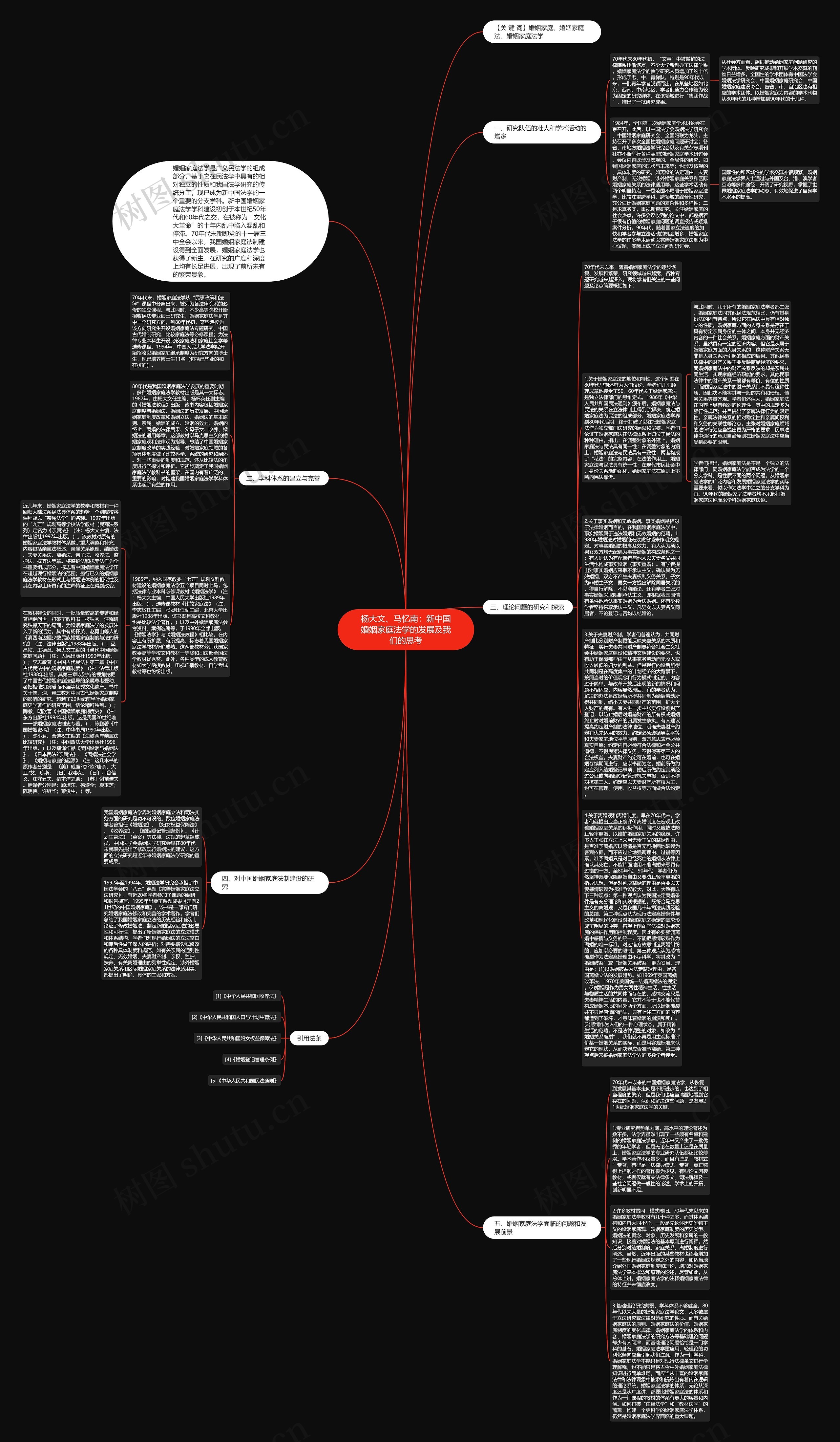
庭法
学
发展
家
婚
文
马忆南
新
妇幼权益
妇女儿童权益论文
【内容提要】70年代末以来,我国从事婚姻家庭法学研究的队伍不断壮大,学术活动增多,学科体系得到建立和完善,在诸多学术领域获得研究成果的同时,对中国婚姻家庭法制建设的研究亦功不可没。21世纪的中国婚姻家庭法学,应改变重应用、轻理论的功利化倾向,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加强学术上的开拓与创新,争取在广度和深度上更上一层楼。
树图思维导图提供《杨大文、马忆南:新中国婚姻家庭法学的发展及我们的思考》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杨大文、马忆南:新中国婚姻家庭法学的发展及我们的思考》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8105924db7ce2eaea57a7b51a34bb66b
思维导图大纲
相关思维导图模版
杨大文、马忆南:新中国婚姻家庭法学的发展及我们的思考思维导图模板大纲
【关 键 词】婚姻家庭、婚姻家庭法、婚姻家庭法学
婚姻家庭法学是广义民法学的组成部分,基于它在民法学中具有的相对独立的性质和我国法学研究的传统分工,现已成为新中国法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新中国婚姻家庭法学学科建设初创于本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之交,在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中陷入混乱和停滞。70年代末期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婚姻家庭法制建设得到全面发展,婚姻家庭法学也获得了新生,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均有长足进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一、研究队伍的壮大和学术活动的增多
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革”中被撤销的法律院系逐渐恢复,不少大学新创办了法律学系。婚姻家庭法学的教学研究人员增加了约十倍,形成了老、中、青梯队。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一批青年学者脱颖而出。在某些地区如北京、西南、中南地区,学者们通力合作结为较为固定的研究群体,在该领域进行“集团作战”,推出了一批研究成果。
从社会方面看,组织推动婚姻家庭问题研究的学术团体、反映研究成果和开展学术交流的刊物日益增多。全国性的学术团体有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中国婚姻家庭建设协会。各省、市、自治区也有相应的学术团体。以婚姻家庭为内容的学术刊物从80年代的几种增加到90年代的十几种。
1984年,全国第一次婚姻家庭学术讨论会在京召开。此后,以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全国妇联为龙头,主持召开了多次全国性婚姻家庭问题研讨会;各省、市地方婚姻法学研究会以及有关杂志期刊社亦不断举行各种类型的婚姻家庭学术研讨会。会议内容既涉及宏观的、全局性的研究,如我国婚姻家庭的现状与未来等;也涉及微观的、具体制度的研究,如离婚的法定理由、夫妻财产制、无效婚姻、涉外婚姻家庭关系和区际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适用等。这些学术活动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范围不局限于婚姻家庭法学,比较注重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性研究,充分估计婚姻家庭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二是求真务实,重视调查研究,关注婚姻家庭的社会热点。许多会议收到的论文中,都包括若干很有价值的婚姻家庭问题的调查报告或疑难案件分析。90年代,随着国家立法速度的加快和学者参与立法活动的机会增多,婚姻家庭法学的许多学术活动以完善婚姻家庭法制为中心议题,实际上成了立法问题研讨会。
国际性的和区域性的学术交流亦很频繁,婚姻家庭法学界人士通过与外国及台、港、澳学者互访等多种途径,开阔了研究视野,掌握了世界婚姻家庭法学的动态,有效地促进了自身学术水平的提高。
二、学科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70年代末,婚姻家庭法学从“民事政策和法律”课程中分离出来,被列为各法律院系的必修的独立课程。与此同时,不少高等院校开始招收民法专业硕士研究生,婚姻家庭法学是其中一个研究方向。到80年代初,某些院校为该方向研究生开设婚姻家庭法专题研究、中国古代婚制研究、比较家庭法等必修课程;为法律专业本科生开设比较家庭法和家庭社会学等选修课程。1994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开始招收以婚姻家庭继承制度为研究方向的博士生,现已培养博士生11名(包括已毕业的和在校的)。
80年代是我国婚姻家庭法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多种婚姻家庭法学教材出版是其一大标志。1982年,由杨大文任主编、杨杯英任副主编的《婚姻法教程》出版,该书内容包括婚姻家庭制度与婚姻法、婚姻法的历史发展、中国婚姻家庭制度改革和婚姻立法、婚姻法的基本原则、亲属、婚姻的成立、婚姻的效力、婚姻的终止、离婚的法律后果、父母子女、收养、婚姻法的适用等章。这部教材以马克思主义的婚姻家庭观和法律观为指导,总结了中国婚姻家庭制度改革的实践经验,对婚姻家庭领域的各项具体制度做了比较科学、系统的研究和阐述。对一些重要的制度和规范,还从比较法的角度进行了探讨和评析。它初步奠定了我国婚姻家庭法学教科书的框架,在国内有着广泛的、重要的影响,对构建我国婚姻家庭法学学科体系也起了有益的作用。
1985年,纳入国家教委“七五”规划文科教材建设的婚姻家庭法学五个项目同时上马,包括法律专业本科必修课教材《婚姻法学》(注:杨大文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选修课教材《比较家庭法》(注:李志敏任主编,张贤钰任副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该书既是高校文科教材,也是比较法学著作。)以及中外婚姻家庭法参考资料、案例选编等,于1990年全部出版。《婚姻法学》与《婚姻法教程》相比较,在内容上有所扩展,有所提高,标志着我国婚姻家庭法学教材渐趋成熟。这两部教材分别获国家教委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一等奖和司法部全国法学教材优秀奖。此外,各种类型的成人教育教材如大学函授教材、电视广播教材、自学考试教材等也纷纷出版。
近几年来,婚姻家庭法学的教学和教材有一种回归大陆法系民法典体系的趋势,个别院校将课程冠以“亲属法学”的名称。1997年出版的“九五”规划高等学校法学教材(民商法系列)定名为《亲属法》(注:杨大文主编,法律出版社1997年出版。)。该教材对原有的婚姻家庭法学教材体系做了重大调整和补充,内容包括亲属法概述、亲属关系原理、结婚法、夫妻关系法、离婚法、亲子法、收养法、监护法、抚养法等章。将监护法和抚养法作为全书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中国婚姻家庭法学正在超越现行婚姻法的范围;盛行已久的婚姻家庭法学教材在形式上与婚姻法体例的相似性及其在内容上所具有的注释特征正在得到改变。
在教材建设的同时,一批质量较高的专著和译著相继问世,打破了教科书一枝独秀、注释研究独撑天下的局面,为婚姻家庭法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其中有杨怀英、赵勇山等人的《滇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婚姻家庭制度与法的研究》(注:法律出版社1988年出版。);巫昌祯、王德意、杨大文主编的《当代中国婚姻家庭问题》(注: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李志敏著《中国古代民法》第三章《中国古代民法中的婚姻家庭制度》(注:法律出版社1988年出版。其第三章以独特的视角挖掘了中国古代婚姻家庭法倡导的亲属尊老爱幼、老妇相敬如宾爱而不淫等优秀文化遗产。书中关于儒、道、释三教对中国古代婚姻家庭制度的影响的研究,超越了20世纪前半叶婚姻家庭史学著作的研究范围,结论精辟独到。);陶毅、明欣著《中国婚姻家庭制度史》(注:东方出版社1994年出版。这是我国20世纪唯一一部婚姻家庭法制史专著。);陈鹏著《中国婚姻史稿》(注:中华书局1990年出版。);陈小君、曹诗权主编的《海峡两岸亲属法比较研究》(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以及翻译作品《美国婚姻与婚姻法》、《日本民法?亲属法》、《离婚法社会学》、《婚姻与家庭的起源》(注:这几本书的原作者分别是:〔美〕威廉?杰?欧?唐奈、大卫?艾、琼斯;〔日〕我妻荣;〔日〕利谷信义、江守五夫、稻本洋之助;〔苏〕谢苗诺夫。翻译者分别是:顾培东、杨遂全;夏玉芝;陈明侠、许继华;蔡俊生。)等。
三、理论问题的研究和探索
70年代末以来,随着婚姻家庭法学的逐步恢复、发展和繁荣,研究领域越来越宽,各种专题研究越来越深入。现将学者们关注的一些问题及论点简要概括如下:
1.关于婚姻家庭法的地位和特性。这个问题在80年代早期还鲜为人们议论,学者们几乎顺理成章地接受了50、60年代关于婚姻家庭法是独立法律部门的思维定式。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颁布后,婚姻家庭法与民法的关系在立法体制上得到了解决,确定婚姻家庭法为民法的组成部分。婚姻家庭法学界到80年代后期,终于打破了以往把婚姻家庭法作为独立部门法研究的局限和偏狭。学者们论证了婚姻家庭法在法律体系上归位于民法的种种理由,指出:在调整对象的外延上,婚姻家庭法与民法具有同一性;在调整对象的内涵上,婚姻家庭法与民法具有一致性,两者构成了“私法”的完整内容;在法的作用上,婚姻家庭法与民法具有统一性;在现代市民社会中,身份关系渐趋弱化,婚姻家庭法在原则上不断向民法靠近。
与此同时,几乎所有的婚姻家庭法学者都主张,婚姻家庭法同其他民法规范相比,仍有其身份法的固有特点,所以它在民法中具有相对独立的性质。婚姻家庭方面的人身关系是存在于具有特定亲属身份的主体之间、本身并无经济内容的一种社会关系。婚姻家庭方面的财产关系,虽然具有一定的经济内容,但它是从属于婚姻家庭方面的人身关系的,这种财产关系无非是人身关系所引起的相应的后果。其他民事法律中的财产关系主要反映商品经济的要求,而婚姻家庭法中的财产关系反映的却是亲属共同生活、实现家庭经济职能的要求。其他民事法律中的财产关系一般都有等价、有偿的性质,而婚姻家庭法中的财产关系则不具有这种性质,因此决不能将其与一般的共有和债权、债务关系等量齐观。学者们还认为,婚姻家庭法在内容上具有强烈的伦理性,其中的规定多为强行性规范;并且提出了亲属法律行为的限定性,亲属法律关系的相对稳定性和亲属间权利和义务的关联性等论点。主张对婚姻家庭领域的法律行为应当提出更为严格的要求;民事法律中通行的意思自治原则在婚姻家庭法中应当受到必要的限制。
学者们指出,婚姻家庭法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同婚姻家庭法学能否成为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从婚姻家庭法学的广泛内容和发展婚姻家庭法学的实际需要来看,似以作为法学中独立的分支学科为宜。90年代的婚姻家庭法学者均不采部门婚姻家庭法说而采学科婚姻家庭法说。
2.关于事实婚姻和无效婚姻。事实婚姻是相对于法律婚姻而言的。在我国婚姻家庭法学中,事实婚姻属于违法婚姻和无效婚姻的范畴。1980年婚姻法对婚姻的无效或撤销未作明文规定。对事实婚姻的概念及效力,有人认为须以男女双方均无配偶为事实婚姻的构成条件之一;有人则认为有配偶者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也构成事实婚姻(事实重婚)。有学者提出对事实婚姻应采取不承认主义,确认其为无效婚姻,双方不产生夫妻权利义务关系,子女为非婚生子女,男女一方提出解除同居关系的,得自行解除,不以离婚论。还有学者主张对事实婚姻采取限制承认主义,即根据我国国情有条件地承认事实婚姻为合法婚姻。还有少数学者坚持采取承认主义,凡男女以夫妻名义同居者,不论登记与否均以结婚论。
3.关于夫妻财产制。学者们普遍认为,共同财产制比分别财产制更能反映夫妻关系的本质和特征,实行夫妻共同财产制更符合社会主义社会中婚姻家庭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也有助于保障那些由于从事家务劳动而无收入或收入较低的妇女的利益。但是现行的婚后所得共同制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大背景下,按照当时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制定的,内容过于简单,与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的情况和问题不相适应,内容显然滞后。有的学者认为,解决的办法是改婚后所得共同制为婚后劳动所得共同制,缩小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扩大个人财产的拥有。有人进一步主张实行婚前财产登记,以防止婚后对婚前财产的所有权或婚姻终止时对婚前财产的归属发生争执。有人建议提高约定财产制的法律地位,明确夫妻财产约定有优先适用的效力。约定必须遵循男女平等和夫妻家庭地位平等原则,双方意思表示必须真实自愿;约定内容必须符合法律和社会公共道德,不得规避法律义务,不得侵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夫妻财产约定可在婚前,也可在婚姻存续期间进行,应以书面为之。婚前所做约定应列入结婚登记事项,婚后所做约定则须经过公证或向婚姻登记管理机关申报,否则不得对抗第三人。约定应以夫妻财产所有权为主,也可在管理、使用、收益权等方面做合法约定。
4.关于离婚观和离婚制度。早在70年代末,学者们就提出应当正确评价离婚制度在宏观上改善婚姻家庭关系的积极作用,同时又应依法防止轻率离婚,以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许多人主张在立法上采用无责主义的离婚理由,是否准予离婚应以感情是否无可挽回地破裂为客观依据,而不应过分地强调理由、过错等因素。准予离婚只是对已经死亡的婚姻从法律上确认其死亡,不能片面地用不准离婚来惩罚有过错的一方。至80年代、90年代,学者们仍然坚持既要保障离婚自由又要防止轻率离婚的指导思想,但是对判决离婚的理由是否要以夫妻感情破裂为标准争议较大。对此,大致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法定离婚条件是有充分理论和实践根据的,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离婚观,又是我国几十年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第二种观点认为现行法定离婚条件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对婚姻家庭之稳定的需求形成了明显的冲突,客观上削弱了法律对婚姻家庭的保护作用和控制程度。因此有必要强调离婚中感情与义务的统一,不能把感情破裂作为离婚的唯一标准。对过错方故意制造离婚纠纷的,应加以必要的限制。第三种观点认为感情破裂作为法定离婚理由不尽科学,将其改为“婚姻破裂”或“婚姻关系破裂”更为妥当。理由是:(1)以婚姻破裂为法定离婚理由,是各国离婚立法的发展趋势。如1969年英国离婚改革法、1970年美国统一结婚离婚法的规定。(2)婚姻是作为男女两性精神生活、性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共同体而存在的,感情交流只是夫妻精神生活的内容,它并不等于也不能代替构成婚姻本质的另外两个方面。所以婚姻破裂并不只是感情的消失,只有上述三方面的内容都遭到了破坏,才意味着婚姻的崩溃和死亡。(3)感情作为人们的一种心理状态,属于精神生活的范畴,不是法律调整的对象,如改为“婚姻关系破裂”,我们就不再是用主观标准评价某一婚姻关系的实际,而是用客观标准来认定它的现状,从而决定应否准予离婚。第三种观点后来被婚姻家庭法学界的多数学者接受。
四、对中国婚姻家庭法制建设的研究
我国婚姻家庭法学界对婚姻家庭立法和司法实务方面的研究是功不可没的。数位婚姻家庭法学者曾担任《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收养法》、《婚姻登记管理条例》、《计划生育法》(草案)等法律、法规的起草组成员。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早在80年代末就率先提出了修改现行婚姻法的建议,这方面的立法研究是近年来婚姻家庭法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1992年至1994年,婚姻法学研究会承担了中国法学会的“八五”课题《完善婚姻家庭法立法研究》,有近20名学者参加了课题的调研和报告撰写。1995年出版了课题成果《走向21世纪的中国婚姻家庭》,该书是一部专门研究婚姻家庭法修改和完善的学术著作。学者们总结了我国婚姻家庭立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论证了修改婚姻法、制定新婚姻家庭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新婚姻家庭法的立法模式和体系结构。学者们对现行婚姻法的立法空白和滞后性做了深入的评析;对需要增设或修改的各种具体制度和规范,如有关亲属的通则性规定、无效婚姻、夫妻财产制、亲权、监护、扶养、有关离婚理由的列举性规定、涉外婚姻家庭关系和区际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适用等,都提出了明确、具体的主张和方案。
五、婚姻家庭法学面临的问题和发展前景
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婚姻家庭法学,从恢复到发展其基本走向是不断进步的,也达到了相当程度的繁荣,但是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它存在的问题,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是发展21世纪婚姻家庭法学的关键。
1.专业研究者势单力薄,高水平的理论著述为数不多。法学界虽然出现了一些颇有名望和建树的婚姻家庭法学家,近年来又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年轻学者,但是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婚姻家庭法学的专业研究队伍都还比较薄弱。学术著作不仅量少,而且有些是“教材式”专著,有些是“法律导读式”专著,真正称得上担纲之作的著作极为少见。有些论文因袭教材,或者仅就有关法律条文、司法解释及一些社会问题做一般性的论述,学术上的开拓、创新明显不足。
2.许多教材雷同,模式陈旧。70年代末以来的婚姻家庭法学教材有几十种之多,而其体系结构和内容大同小异。一般是先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婚姻家庭观、婚姻家庭制度的历史类型、婚姻法的概念、对象、历史发展和亲属的一般知识,接着对婚姻法的基本原则进行阐释,然后分别对结婚制度、家庭关系、离婚制度进行阐述。当然,近年出版的某些教材也逐渐增加了一些现行婚姻法规定之外的内容,如适当地介绍外国婚姻家庭制度和理论,增加对婚姻家庭法学基本概念和原理的论述。尽管如此,从总体上讲,婚姻家庭法学的注释婚姻家庭法律的特征并未彻底改变。
3.基础理论研究薄弱,学科体系不够健全。80年代以来大量的婚姻家庭法学论文,大多数属于立法研究或法律对策研究的性质。而有关婚姻家庭法的原则、婚姻家庭法的价值、婚姻家庭制度的变化规律、婚姻家庭法学的体系和内容、婚姻家庭法学的研究方法等基础理论问题却少有人问津,而基础理论问题恰恰是一门学科的基石。婚姻家庭法学重应用、轻理论的功利化倾向应当引起我们注意。作为一门学科,婚姻家庭法学不能只是对现行法律条文进行学理解释,也不能只是将古今中外婚姻家庭法律知识进行简单堆砌,而应当从丰富的婚姻家庭法律和法律现象中抽象和提炼出有着内在逻辑的理论系统。婚姻家庭法学的体系,无论从深度还是从广度讲,都要比婚姻家庭法的体系和作为一门课程的教材的体系有更大的容量和内涵。如何打破“注释法学”和“教材法学”的藩篱,构建一个更科学的婚姻家庭法学体系,仍然是婚姻家庭法学界面临的重大课题。
引用法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4]《婚姻登记管理条例》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查看更多
相似思维导图模版
首页
我的文件
我的团队
个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