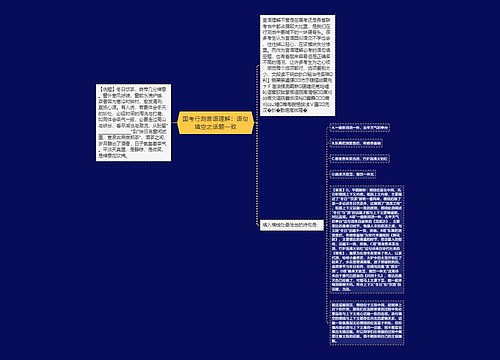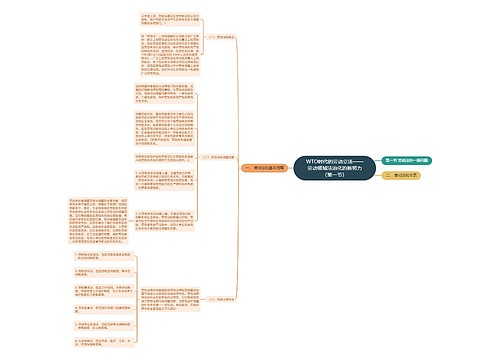论我国《劳动法》的立法目的思维导图
青烟
2023-03-04

目的
立法
劳动关系
《劳动法》
保护
劳动法
理论研究
劳动立法
「内容提要」我国劳动法把保护者的合法权益,调整劳动关系,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为立法目的。本文论述其产生的社会基础,指出该目的在立法过程中人们的认识和接受历程。文章力图从多个角度说明劳动者为何为“弱者”,强调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作者结合劳动法律规范阐述了劳动法立法目的的内容。
树图思维导图提供《论我国《劳动法》的立法目的》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论我国《劳动法》的立法目的》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81d97230d2eeee63b79545e92f80ee2c
思维导图大纲
相关思维导图模版
论我国《劳动法》的立法目的思维导图模板大纲
「关 键 词」劳动法、立法目的、劳动者、劳动关系
任何法律都有其立法目的。正是有了立法目的,人们才会为制定这项立法而开展工作。在立法目的指引下,制定出针对特定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告诉社会成员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可以怎么样行为,不得怎么样行为,以及应当或者必须怎么样行为。我国《劳动法》的立法目的,贯穿于整个劳动法律规范体系之中;各项具体的劳动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必须为其立法目的服务。认真研究和领会我国《劳动法》的立法目的和精神,才能在《劳动法》的贯彻实施中准确掌握和运用。
一、确立我国《劳动法》立法目的的社会基础
我国《劳动法》的立法目的如同大多数立法一样,是规定在“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中的。我国《劳动法》第1条规定:“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调整劳动关系,建立和维护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制度,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根据这条规定,我国《劳动法》的立法目的包括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确立、维护和发展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三个方面。
之所以说《劳动法》把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作为立法目的才能实现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真正的公平和平等,是由劳动者的“弱者”地位和法律维持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方式决定的。
在现代社会,劳动者在法律地位上与用人单位平等,雇工与雇主同样都具有平等的权利既是普遍的共识,也是各国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劳动者是国家的主人,其法律地位和权利得到的保障是毋庸置疑的。但法律地位上的平等与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的平等并不是可以直接画等号的。比如在婚姻关系中夫妻双方都是平等的,但现实的婚姻关系却要偏重对妇女合法权益的保护。这种情况在劳动关系中尤其突出,因为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弱者地位是十分突出的。
对于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弱者地位,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首先我们可以追根溯源,看看劳动法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劳动法得以面世的理由。法律是人的产品,如同人的其他产品一样是为人的需要而产生,为人的需要而存在,为满足人的需要而效力的。如果没有人的需要,任何法律都不会产生;当人有了某种法律需要后,某项法律便会产生;当人的这种需要发生变化或者消失后,法律便会修改或者废除。由人的这种需要决定,因这种需要应运而生的法律便注定了它特有的“目的”。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法律几乎与人类社会的形成同时产生,并为人类社会提供服务。但劳动法是个例外,尽管劳动是与人类共始终的,但劳动法并没有与人类共始发。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随着工人阶级的成长和壮大,工人们不堪忍受机器生产下大大增加了的劳动强度,不堪忍受工时长、工资低等种种恶劣的劳动条件,不断和资本家展开斗争,从自发的分散的破坏机器,到成为有组织的自觉的运动并组织工会,开展更为有效地斗争。启蒙思想家的进步学说也演生出主张劳动和职业自由,强迫劳动者从事雇佣劳动,过度延长工作时间和压低工资数额,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和非正义的。资本家迫于对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而不得不做出适当让步,资产阶级政府也意识到如果允许资本家不受限制地肆意蹂躏工人,或者以合同自由为据放任不管,甚至以法律规范助纣为虐,必然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也必将付出昂贵的社会代价。因此,皮尔勋爵于1802 年提出学徒健康与道德法案,获得国会通过。这就是目前公认的最早的劳动法,实际上是第一部保护童工的劳动立法。该法规定:纺织厂不能用9岁以下的学徒;童工每天工作不得超过12小时,而且限于清晨6时至晚间9时,禁止做夜工。经皮尔等人的继续努力,此法案1819年得到修正,规定纺织业不分对象均禁止雇佣 9岁以下儿童,16岁以下儿童仅能工作12小时。1833年的《工厂法》进一步规定,13岁以下儿童每天工作不超过9小时,每周48小时。1847年修正工厂法规定,女工及18岁以下的童工每天工作不得超过10小时。
从劳动法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第一部标志性劳动法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劳动法面世的理由和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处于“弱者”地位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它是以劳动关系一方当事人,即作为弱者的劳动者为保护对象的。如果劳动者不需要劳动法的专门保护,劳动法就不会出现在人类社会的生活中;如果劳动法不以劳动者为专门的保护对象,并以此作为自己的根本目的,劳动法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和必要,或者说这样的劳动法就不能再称之为劳动法了。这或许也就是我国劳动者在呼唤《劳动法》尽早出台所说:“我们劳动者亟待劳动法的保护”的原始依据吧。
劳动者的“弱者”地位随着历史的进程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劳动者的地位已是历史上的劳动者不可想象的,但今天劳动者相对于用人单位的“弱者”地位仍然是可以感知的。
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资源大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现象尤为突出。温家宝总理2003年3月18日会见中外记者时就坦诚地表明:“中国的劳动力有7亿4千万,而欧美所有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只有4亿3千万。中国每年新增劳动力1000万;下岗和失业人口大约1400万;进城的农民工一般保持在1亿2千万。中国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注:“温家宝总理等会见中外记者,答问全文”中国人大新闻, www.npcnews.com.cn,2003 年3月19日。)巨大的劳动力基数意味着即使是较低比率的失业也产生了庞大的失业后备军。如果说“失业” 对于社会和政府是“压力”的话,对于失业的劳动者本身,其中的滋味就不仅仅是“压力”所能领略的了。美国一个州的劳动法协会的定论为:犯罪通常是失业者的最后选择。失业不仅使失业者本人及其家庭生活由于收入下降而质量下降,劳动者的劳动技能因为停止工作而退化或过时,而且还会使失业者及其家庭成员在精神上蒙受伤害,自信心与成就感因挫折而减退,与社会的沟通由于离开工作单位而疏远。就连家庭的稳定性也面临严峻的考验,失业或下岗者中离婚率偏高,其中又以男性失业或下岗为甚便是例证。直白地说:失业影响的是失业者的生存、失业者家庭成员的生存和失业者家庭本身的生存。由于有了失业保险等救济制度,这里的“生存”与“活着”是略有区别的,但其程度也是不易承受的(注:“逾4万人争3600个职位‘获聘好过中大彩’”:香港最大雇主赛马会连续两天为3600个职位举办招聘会,共吸引了逾4万人通宵排队求职,此情此景仿佛时光倒流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最艰难时期。一名昨天成功获得面试机会的中七男生向《明报》即时新闻说,他尝试找过六七份工都失败,现在希望在马会觅得兼职电话接听员的职位。他形容,如果获聘,“还好过中六合彩(大彩)”。仅首日有38000人排队3公里为争取一个职位,人龙由湾仔排到中环,成为香港20年来罕有的“壮观”求职场面,也凸显了香港失业的困境。(联合早报[新加坡],2003年5月 19日))。
可见,劳动者的“弱者”地位再次被“注定”。
进而言之,在已经形成的劳动关系中,即劳动者已经找到工作,实现就业后,劳动者仍然是“弱者”。我们知道,劳动关系的特征之一就是它的依附性,包括雇工对雇主的依附和雇工对雇用组织的依附性。劳动者服从雇主及其雇用单位的管理、指挥和监督是一项基本的劳动义务,这项义务还构成了劳动法、劳动合同和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内容。在日常工作劳动者必须将自己置之于用人单位的管理、指挥和监督下。当发生劳动争议时,劳动者或由于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管理方式,或由于其他劳动者对于雇主的顾虑,往往难以得到对自己有利的证据。还有由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一次争讼,在失去现有工作后更难重新找到工作,尤其当这次争讼在媒体曝光后。而这一切,对于雇主或者用人单位都不在话下,不仅会容易找到新的劳动者,即使是诉讼费、律师费等开支也是在生产成本中列支,不是由个人承担。前些年江苏的一个案例也能证明这方面的情形。一家长期亏损的国有企业在四人承包经营后效益大增,成为该市的纳税大户。该厂一名一贯表现优秀的女工因一天没来上班被全厂通报批评,女工的丈夫为此去找厂长理论,双方发生冲突。厂长于当天下午发出公告,开除该名女工。女工不服,向区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争议仲裁申请。区劳动仲裁委员会审理后认定厂方开除女工的做法于法无据,裁决撤销厂方的决定。四名作为厂长和副厂长的承包人对仲裁裁决不服,在向法院起诉的同时,集体辞职,致该厂停产,并通告全厂职工凡愿每天去市政府请愿要求恢复厂长职务,开除该名女工者发给高于工资的报酬。这个案件的最后结果现在已不重要,但它向我们清楚地说明了在劳动争议案件中,作为双方当事人所做的和所能做到的差异是何其明显?
劳动者的“弱者”地位已不需再多证明。问题在于面对实际地位不平等的双方当事人,法律应当怎么办?由法律维持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方式决定,劳动法应当担负起维护作为“弱者”一方的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任务。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社会成员在社会中的生存能力由于先天或后天的原因是有强弱之分的,但人类社会与动物世界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不允许“弱肉强食”这一 “丛林规则”成为社会规范,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中必须奉行平等和公正的原则。
二、我国《劳动法》立法目的的内容
(一)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是我国《劳动法》最基本的目标之一。我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劳动者是公有制经济的生产资料的主人。这种社会制度的性质决定了劳动者在企业中的地位和享有充分的民主管理等权利。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建立起劳动者当家作主的社会制度,中国共产党无论在为新中国成立而斗争的过程中。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经济建设中,始终都将这一由社会性质决定的最高目的,贯穿于所有的决策和工作实践之中。
对此,我国《宪法》第十二条至四十五条作了全面而系统的规定,《劳动法》将此作为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立法目的的最高效力的法律依据。《劳动法》把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作为首要任务,就是充分体现宪法有关规定的精神,把劳动者享有的合法权益明晰化、具体化,使宪法赋予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以真正实现。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是指劳动者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劳动方面享有的各种权利和利益。《劳动法》把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作为首要目的,也是由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决定的。在社会主义国家,法律所体现的是人民的意志,是以维护广大人民利益为其根本目的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劳动者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生活的主体,《劳动法》首先要体现保护劳动者的各种需要和利益。同时,劳动者的利益需要是劳动者从事生产劳动的内在动因和动力。当劳动者的这种利益需要得到满足和保护时,劳动者便更有劳动的创造性。《劳动法》正是以法律手段来满足、支持和保护劳动者不断得到这些物质利益的需要。总之,如果不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作为《劳动法》的基本立法目的,《劳动法》本身也会失去其制定的意义。
另一方面,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是实现稳定劳动关系、正常劳动秩序、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前提与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和谐和稳定的劳动关系,以及正常的劳动秩序便不可能存在。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长期不被重视和遭受侵害,必然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劳动者合法权益受到保护的程度,又是反映一个国家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因此,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是我国《劳动法》的最基本的立法目的。
(二)确立、维护和发展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
我国《劳动法》的立法目的,不仅在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而且还同时确立、维护和发展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
无论从人类劳动法产生、发展的历史考察。还是从现实和社会生产方面考察,只要有众多人在一起劳动,即进行社会劳动,就必然要求有一定的劳动规则,以实现正常的劳动秩序。正常的劳动秩序,只能建立在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的基础之上。没有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就没有稳定和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因此,劳动法从它在人类社会诞生以来,一直肩负着正常劳动秩序的重大使命。
尽管我国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主人,并享有最广泛的民主管理权利,但是,人类现阶段正处于市场经济的历史阶段决定了社会各群体之间仍然存在着各自的利益的差别,特别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差别。因利益关系决定的各种差别,无时不在威胁着正常的劳动秩序。另一方面,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促进了我国非公有制的多种经济形式得到了迅速发展,如外国资本经济、私营经济等。在这类非公有制经济中,用工一方与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更加明显和突出。因此,将确立、维护和发展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作为我国《劳动法》的立法目的,是劳动法的基本功能和我国社会经济的必然要求和结果。
确立、维护和发展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三者之间是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赖和联系的辩证统一体。
确立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其实质是要求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时,必须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基础上,充分考虑双方各自的利益要求,依法形成一种良好的、健康的劳动关系,不隐含发生冲突的各种人为因素。这一立法目的,在我国《劳动法》中,主要通过第二章“就业促进”和第三章“劳动合同”法律制度保证实现。根据就业促进立法,建立起劳动者之间平等就业的社会就业机制,使劳动者在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时,不因民族、性别、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在就业方面有所差别。通过劳动合同法律制度,建立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确立劳动关系的原则,保障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意志的合理实现,为确立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构建了和谐的人际环境。
发展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是我国《劳动法》确立、维护、发展稳定和谐劳动关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制度立法目的中一个重要目的层次。这一目的不仅将稳定和谐劳动关系置于发展变化之中,而使其更切合实际和便于实现。同时,还对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最大限度地激发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及高涨的劳动热情,使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不断地提高其存在的质量。这一立法目的在《劳动法》中主要表现为:通过规定劳动者享有民主管理的权利,树立和增强劳动者的主人翁责任感,使劳动者同用人单位之间在根本利益基本一致的基础上进行协调的劳动。通过劳动竞赛、合理化建议和奖励制度,激发劳动者的创造性和劳动热情,使劳动者在心情舒畅和精神愉快的情景下实现劳动过程。通过职业培训制度,促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劳动关系的进一步深化。通过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企业对职工职业培训计划的实施,和劳动技能的提高,可以使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延伸到劳动关系的存续期间之外,即劳动合同期限外,当劳动关系依法终止时,其职业培训使有利于促进双方当事人继续确立新的劳动关系。通过建立安全卫生和劳动保护制度,社会保险与福利制度,以及劳动争议的处理制度,不断提高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的质量,并使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不断赋予崭新的内容。
三、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组织和促进经济发展,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职能之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相互促进,互相统一是我国长期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可以说,所有的有关市场经济的立法,都直接或间接地在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我国《劳动法》将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为一项重要的立法目的,不仅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而且通过立法确认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之间的辩证的关系,即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在《劳动法》中具体体现出来。
劳动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而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又是人们进行生产劳动,不断满足自身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重要条件。《劳动法》通过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调整劳动关系,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促进社会进步与促进经济发展,是一个国家一定历史时期内的两项最主要的任务。因此,我国《劳动法》也将促进社会进步作为其重要目的之一。根据这一目的要求我国《劳动法》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考虑社会进步,在选择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各项具体措施时,必须将是否影响或危害社会进步这一因素作为主要依据,并给予充分考虑。在确立的各项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机制实施后影响或与社会进步不一致时,必须有相应的补救措施,以消除追求经济发展目的所采取措施的不足和不完善。
对此,我国《劳动法》在其法律规范的具体内容中,均作了相应的规定,具体表现在:以促进社会进步为目标,确立和贯彻了平等原则。我国《劳动法》不仅确立了这一原则,而且将这一原则贯穿于《劳动法》的各项具体法律规范之中。如保障劳动者就业权的平等行使,保证职业选择权的平等性,保证取得劳动报酬的平等性;通过劳动安全卫生与劳动保护,职业培训,社会保险,劳动争议的处理等统一的规则,保障平等原则在各方面的贯彻实行。
以促进社会进步为目的,建立职业培训制度。我国《劳动法》不仅在总则中将提高职业技能,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作为劳动者的基本义务,将发展职业教育作为国家的责任,并且通过第八章职业培训专章对国家、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个人在职业培训中的地位、作用、职责义务作了专门规定。通过规定逐步提高劳动安全卫生、劳动保护条件和水平以及提高劳动保险待遇等规定,促进社会进步。对此,我国《劳动法》都作了专章规定,对劳动安全卫生规章和标准:劳动保护设施和劳动保护用品。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的特殊的劳动保护;多层次的广泛的社会保险制度和社会保险水平等均作了详细而具体的规定。
应当特别指出,《劳动法》的三个方面的立法目的,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体,三项具体的立法目的,构成了我国《劳动法》立法目的的科学体系。在这个目的体系之中,最高层次的目的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一目的,不仅是《劳动法》的一个最高的目的层次,而且也是我国市场经济立法的一个总目标。将这一目标作为《劳动法》的最高目的,不仅确立了《劳动法》在整个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起到了《劳动法》同相关的市场经济的其它立法相协调和衔接的作用。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以及确立、维护和发展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两个方面的立法目的,一方面反映了《劳动法》的本质和作用,直接地指导和制约着具体的劳动法律规范,另一方面又服务或作用于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高层次的立法目的。
黎建飞
引用法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第一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第三条
查看更多
904名中国成年人第三磨牙相关知识、态度、行为和病史的横断面调查思维导图
 U633687664
U633687664树图思维导图提供《904名中国成年人第三磨牙相关知识、态度、行为和病史的横断面调查》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904名中国成年人第三磨牙相关知识、态度、行为和病史的横断面调查》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10b9a8a2dd2fb4593f8130ef16c320fc

9.战斗的基督教思维导图
 U582679646
U582679646树图思维导图提供《9.战斗的基督教》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9.战斗的基督教》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33d168acd0cd9f767f809c7a5df86e3a

相似思维导图模版
首页
我的文件
我的团队
个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