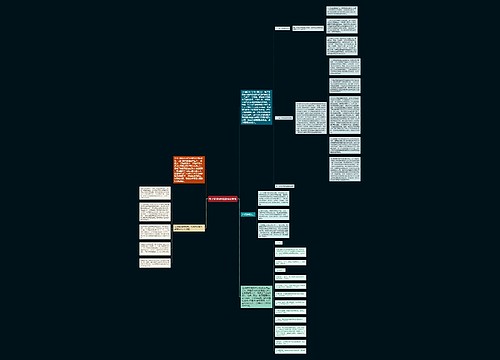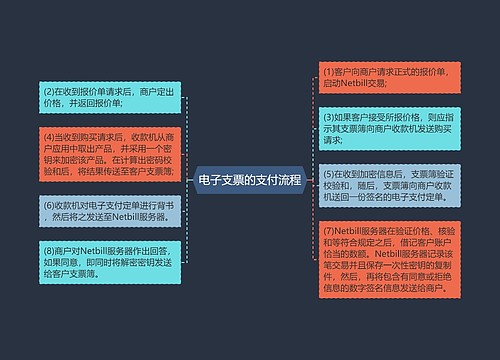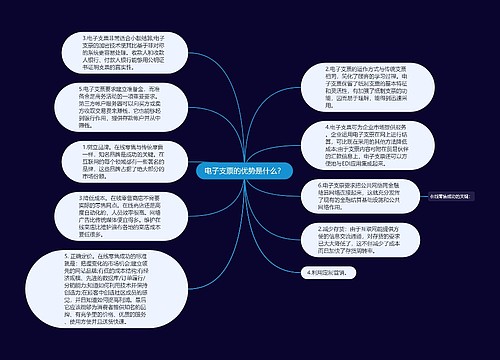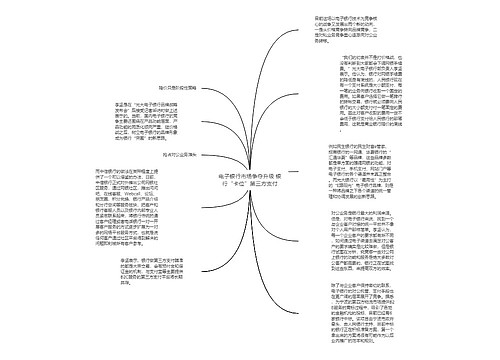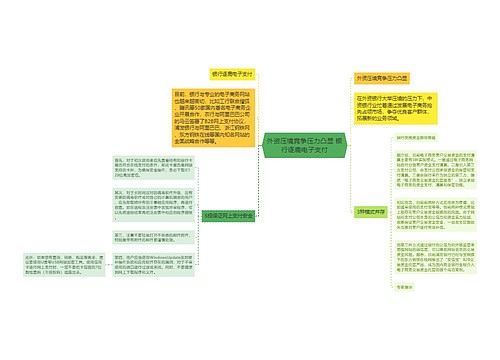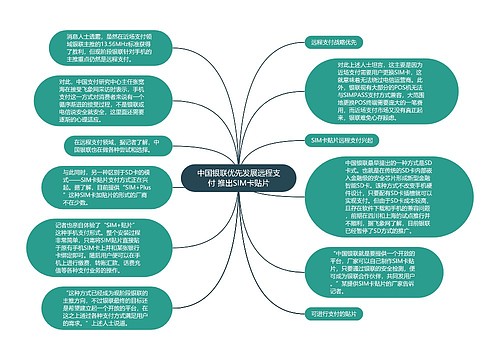这些支付手段,一般都是有形的,它们是电子货币得以移转的载体。换言之,没有这些载体,是无法实现电子货币移转的。进而可以说,行为人进行经济型、工具型网络犯罪,要依赖这些载体。但它们不是犯罪的对象。因为它们并不直接反映作为犯罪客体的财产关系所受到的侵犯。如行为人窃取他人智能卡到他取现或进行使用之间,有时间上的间隔,在此期间,原持卡人可以挂失从而避免财产受损;或者行为人并没有利用智能卡,权利人的财产就没有受到损失。所以,决定是否对行为人追究刑事责任不是看他是否取得了电子货币的载体,而是他取不取用电子货币的现实可能性,以及他对于电子货币所体现的财产权施加危害的大小。
另外,盗取或者骗取他人网络服务。网络服务要在网络中计费,最终涉及的依然是以数字符号表示的财产关系,所以其犯罪对象也不妨看做是电子货币。
依照传统的刑法理论界分诈骗罪和盗窃罪,似乎问题不大;但是在对盗窃信用卡后使用,以及盗窃空白发票、支票以及其他空白有价凭证然后使用的行为的定性上,也曾经出现过不同看法。新刑法颁布后所作的一些规定以及有关司法解释澄清了其中的一些问题,对于盗窃与诈骗的区别规定得更为明确。如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盗窃罪)的规定定罪处罚。只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原本简单的问题在网络金融领域变得复杂了。
信用卡是最早的电子货币载体,今天,体现电子货币的载体还包括其他的电子钱夹、电子票据和智慧卡,所以,犯罪的手段更是复杂、多样。如在日本,到处都有全国联网、各银行联网的现金自动取款机?ATM?,ATM和信用卡的普及程度非常高,针对ATM卡的犯罪也相当猖獗,从盗窃他人的ATM卡然后破译密码,接着提取现金,发展到伪造主ATM卡,再发展到通过网络联接到银行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直接窃取账户资金的“线上犯罪”。
网络诈骗和盗窃犯罪区分的难点在于虚拟环节的欺诈性与现实环节的盗窃性竞合的场合。虚拟环节是在网络中发生的,而现实环节是在现实社会中发生的。
行为人为了取得或盗用他人的电子货币,在虚拟空间可以采取的方式有两类:一是破坏信息系统的正常运行,借机达到目的;二是冒充其他的权利人,骗取“系统管理者”的信任,从而获得或使用其他权利人的电子货币。用第一种方式达到目的的可能性在网络领域几乎是零,所以第二种方式是常见的。如此一来,肯定要使用欺骗性手段。为了使欺骗更有成效,尽快得到权利人的密码、签名等真实信息,无疑是行为人所追求的。有些行为人采取技术方式,在网络中破译权利人密码,套取其相关信息;也有的采取传统意义的盗窃方法获得这些关键信息。后一种情形就发生了盗窃行为和诈骗行为竞合的现象。
对此,立足于我国刑法的规定,结合传统的刑法理论,并充分考虑电子货币的特点,区分某种行为是属于盗窃罪还是诈骗罪,必须考虑发生在现实环节的行为性质。因为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虚拟空间发生的行为绝大部分具有诈骗的性质,但是,如果将网络经济型犯罪一律以诈骗罪论处,显然与法律的规定不符;另外,从法理上讲,盗窃罪相对于诈骗罪,属于重罪,当出现两种罪竞合时,要作为牵连犯处理,应定为盗窃罪。进一步说,在现实环节发生的行为如果是诈骗,继之所为的虚拟环节的行为就构成诈骗罪;在现实环节发生的行为是盗窃,继之而为的虚拟环节的行为就构成了盗窃罪。
综上,笔者认为,网络诈骗和盗窃犯罪的界分具体可概括如下:
以下行为构成盗窃罪:1.对于使用未设定密码的智能卡,或者多次使用限额设定密码的智能卡,且达到较大数额的;2.对于一年之内连续三次使用智能卡,应当认为符合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多次盗窃”;3.盗用他人公共信息网络上网账号、密码上网,造成他人电信资费损失数额较大的行为;4.对于使用盗窃的电子钱夹,如信用卡等的行为。
以下行为构成诈骗罪:1.以虚假、冒用的身份证件办理入网手续并使用移动电话,造成电信资费损失数额较大的;2.骗取他人的各种支付手段的账号、密码,然后利用这些账号密码在网络中套取电子货币的;3.在网上采取技术方式,破译权利人密码,套取其相关信息,继而套取电子货币的;4.骗取智能卡的密码,继而使用的;5.盗窃智能卡的密码,从而使用的。

 U582679646
U582679646
 U882673919
U882673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