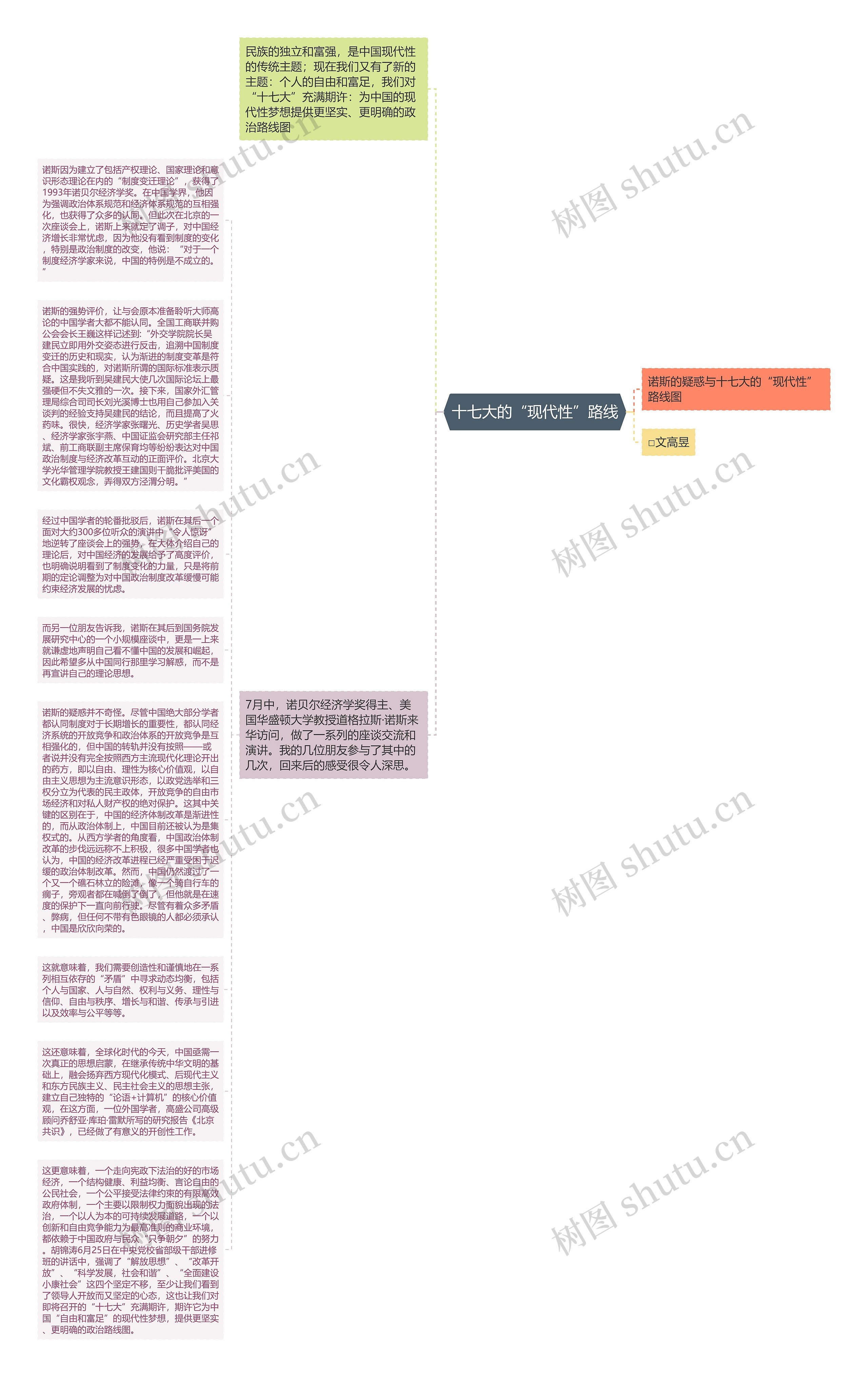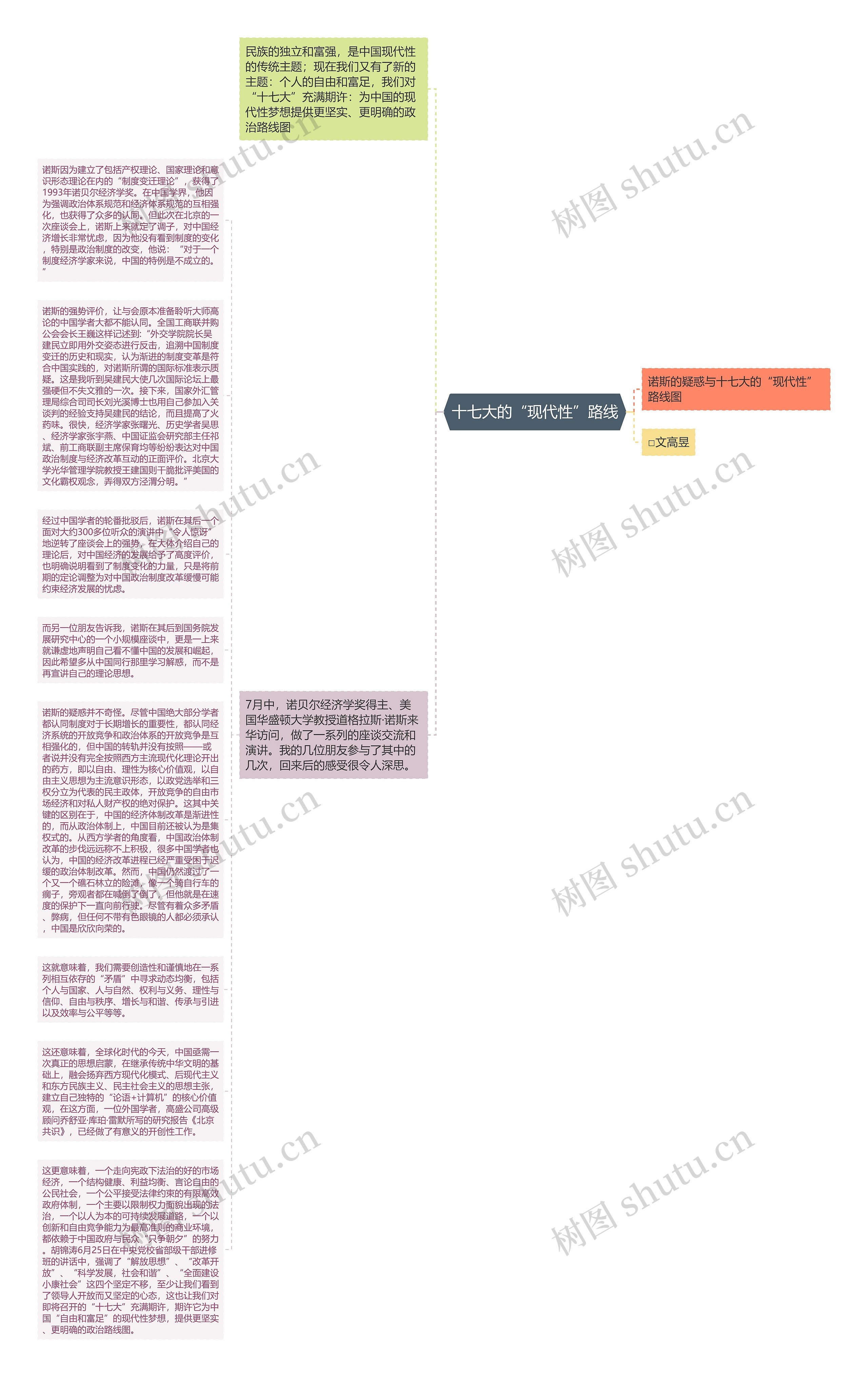诺斯因为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获得了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中国学界,他因为强调政治体系规范和经济体系规范的互相强化,也获得了众多的认同。但此次在北京的一次座谈会上,诺斯上来就定了调子,对中国经济增长非常忧虑,因为他没有看到制度的变化,特别是政治制度的改变,他说:“对于一个制度经济学家来说,中国的特例是不成立的。”
诺斯的强势评价,让与会原本准备聆听大师高论的中国学者大都不能认同。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会长王巍这样记述到:“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立即用外交姿态进行反击,追溯中国制度变迁的历史和现实,认为渐进的制度变革是符合中国实践的,对诺斯所谓的国际标准表示质疑。这是我听到吴建民大使几次国际论坛上最强硬但不失文雅的一次。接下来,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司长刘光溪博士也用自己参加入关谈判的经验支持吴建民的结论,而且提高了火药味。很快,经济学家张曙光、历史学者吴思、经济学家张宇燕、中国证监会研究部主任祁斌、前工商联副主席保育均等纷纷表达对中国政治制度与经济改革互动的正面评价。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王建国则干脆批评美国的文化霸权观念,弄得双方泾渭分明。”
经过中国学者的轮番批驳后,诺斯在其后一个面对大约300多位听众的演讲中“令人惊讶”地逆转了座谈会上的强势,在大体介绍自己的理论后,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给予了高度评价,也明确说明看到了制度变化的力量,只是将前期的定论调整为对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缓慢可能约束经济发展的忧虑。
而另一位朋友告诉我,诺斯在其后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个小规模座谈中,更是一上来就谦虚地声明自己看不懂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因此希望多从中国同行那里学习解惑,而不是再宣讲自己的理论思想。
诺斯的疑惑并不奇怪。尽管中国绝大部分学者都认同制度对于长期增长的重要性,都认同经济系统的开放竞争和政治体系的开放竞争是互相强化的,但中国的转轨并没有按照——或者说并没有完全按照西方主流现代化理论开出的药方,即以自由、理性为核心价值观,以自由主义思想为主流意识形态,以政党选举和三权分立为代表的民主政体,开放竞争的自由市场经济和对私人财产权的绝对保护。这其中关键的区别在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渐进性的,而从政治体制上,中国目前还被认为是集权式的。从西方学者的角度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远远称不上积极,很多中国学者也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已经严重受困于迟缓的政治体制改革。然而,中国仍然渡过了一个又一个礁石林立的险滩,像一个骑自行车的瘸子,旁观者都在喊倒了倒了,但他就是在速度的保护下一直向前行驶。尽管有着众多矛盾、弊病,但任何不带有色眼镜的人都必须承认,中国是欣欣向荣的。
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创造性和谨慎地在一系列相互依存的“矛盾”中寻求动态均衡,包括个人与国家、人与自然、权利与义务、理性与信仰、自由与秩序、增长与和谐、传承与引进以及效率与公平等等。
这还意味着,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中国亟需一次真正的思想启蒙,在继承传统中华文明的基础上,融会扬弃西方现代化模式、后现代主义和东方民族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主张,建立自己独特的“论语+计算机”的核心价值观,在这方面,一位外国学者,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所写的研究报告《北京共识》,已经做了有意义的开创性工作。
这更意味着,一个走向宪政下法治的好的市场经济,一个结构健康、利益均衡、言论自由的公民社会,一个公平接受法律约束的有限高效政府体制,一个主要以限制权力面貌出现的法治,一个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一个以创新和自由竞争能力为最高准则的商业环境,都依赖于中国政府与民众“只争朝夕”的努力。胡锦涛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讲话中,强调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四个坚定不移,至少让我们看到了领导人开放而又坚定的心态,这也让我们对即将召开的“十七大”充满期许,期许它为中国“自由和富足”的现代性梦想,提供更坚实、更明确的政治路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