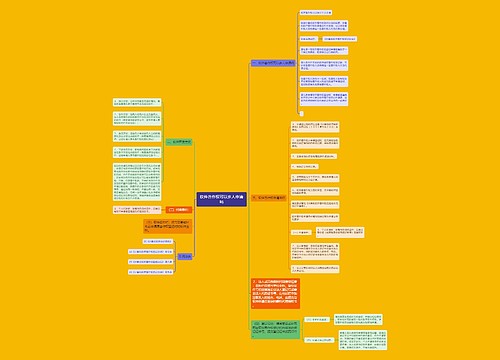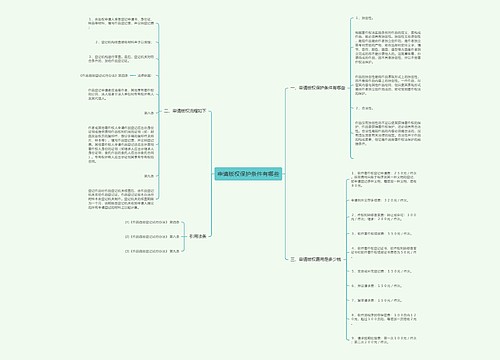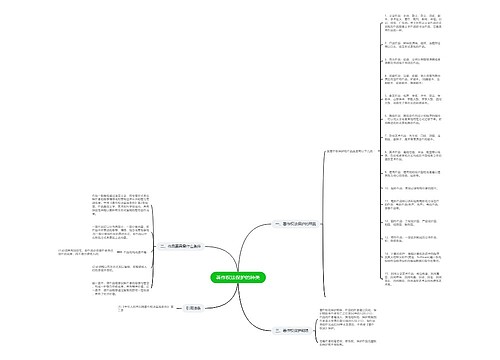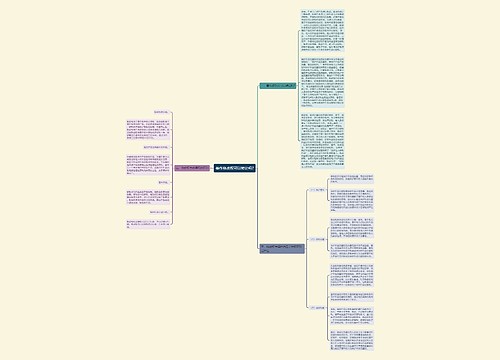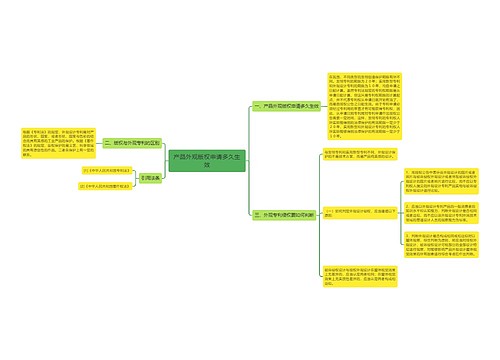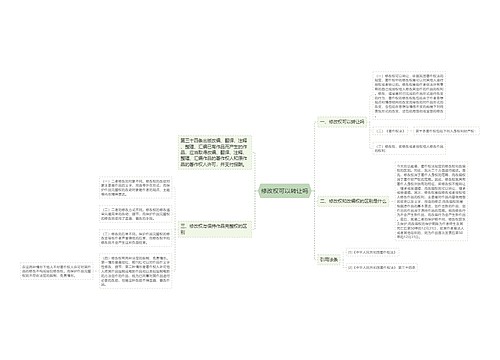表演者权的客体是表演活动。表演活动则是指表演者通过自己对作品的理解和阐释,以声音、动作、表情等等将作品的内容传达出来或者借助一定的工具如乐器、道具等等将作品的内容传达出来。
表演者的表演活动,只有在录音技术发明和广泛运用之后,才成了受保护的客体。在录音技术发明和运用之前,社会公众要想观看或聆听某一作品的表演,只能亲临表演现场。随着表演活动的结束,表演者的表演也只是或多或少地留存在观看者的记忆之中。如果观看者还想再次观看或聆听有关的表演,就必须再次亲临表演现场。而在录音技术发明和运用之后,却有可能将表演活动中的声音部分录制下来,让社会公众不必亲临表演现场就可以听到、看到有关的表演。当然,在运用电影技术将表演活动拍摄下来的时候,还可以形成电影作品或录像制品,让观众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和听到有关的表演。这样,对于表演活动的保护,对于表演者权的保护就成了法律必须面对的问题。
说表演活动只有在录音以后才成为受保护的对象,并不意味着表演者权的客体是录音制品。录音制品是录制者权的保护客体,而非表演者权的客体。表演者权的客体仍然是表演活动,是录制在录音制品中的表演活动。这样,作为一件录音制品,其中就至少包括了三个受保护的对象,即被表演的作品、表演者的表演活动、录音制作者的录制。与此相应,一件录音制品中也至少含有了三个权利,即作者的权利、表演者的权利和录音制作者的权利。
表演者权的客体是表演活动,但不是被表演的作品或“节目”。例如,莎士比亚的戏剧是作品,虽然从来没有受到过著作权法或版权法的保护,但可以由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的表演者进行表演,并且就其表演活动享有表演者权。又如,中国的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中国的话剧《雷雨》《茶馆》,中国的音乐《梁祝》《二泉映月》等等,曾经有过许多个“表演版本”和“表演”,表演者对于每一个“表演版本”或每一次“表演活动”都享有表演者权。这种状况甚至发生在同一个表演者对同一个作品的数次表演上。例如,杨丽萍曾经多次表演《孔雀舞》,她就自己每一次的表演活动都享有权利,绝非仅仅对自己的第一次表演享有权利,而对随后的表演活动就不享有权利。如果将表演者权的客体定义为被表演的作品,就有可能发生表演者仅在作品受保护期间就其表演活动享有权利,而在作品保护期届满以后就对其表演活动不享有权利的误解。甚至在某些从来没有受到过著作权法或版权法保护之作品的情况下,如莎士比亚的作品、曹雪芹的作品,得出表演这些作品不享有表演者权的荒谬结论。如果将表演权的客体定义为“节目”,就可能发生让表演者仅仅对第一次的表演活动享有权利,而否认表演者对后来的表演活动享有权利的误解。例如,在《红色娘子军》、《二泉映月》等作品的情况下,得出错误的结论说,表演者仅对第一次的表演活动享有表演者权,对以后的表演不享有权利。
严格说来,表演者权的客体是表演者的每一次表演活动,而不论这种表演活动是对于同一作品的表演,还是对于不同作品的表演,也不论这种表演活动是表演专有领域中的作品还是公有领域中的作品。

 U633687664
U633687664
 U582679646
U582679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