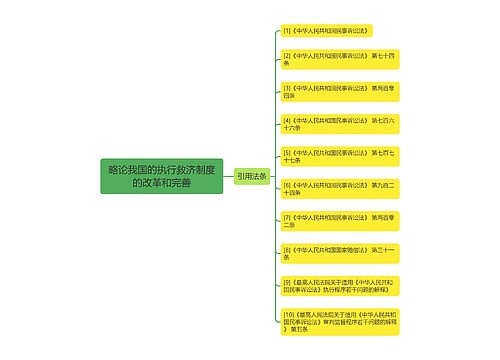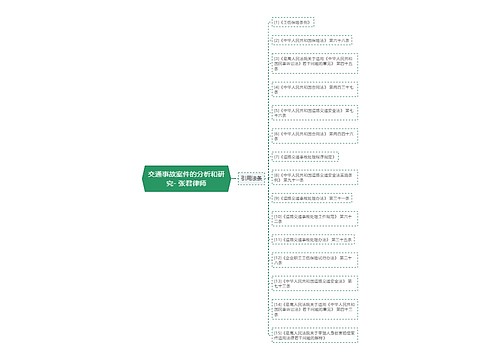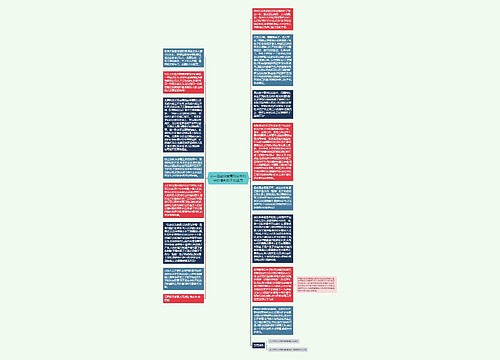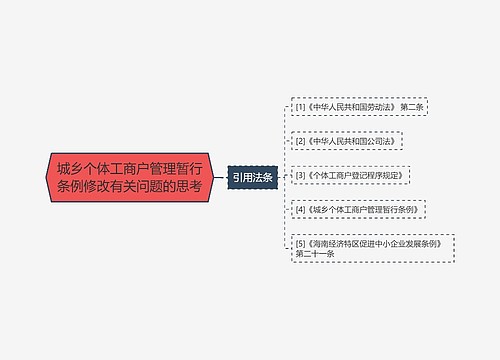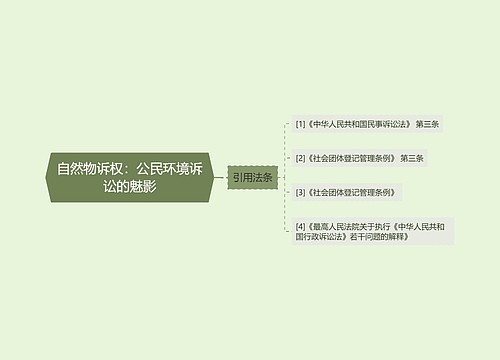先决问题与中间裁判(下)思维导图
烟花柳巷
2023-02-23

裁判
中间
问题
判决
诉讼
事项
先决
确认
请求
程序
合伙
合伙论文
内容提要: 目前我国对于先决事项的司法判定在形式、程序、效力、救济途径等方面的空白或缺陷已严重困扰司法实践,特别是随着诉讼模式改革的日渐深化,当事人辩论权的控制力与司法效率的强大压力从两个相向的方向上对裁判权形成挤压。通过解析德国和法国等大陆法系国家中间裁判制度,将其中间裁判的适用对象分解为实体性先决事项、程序性先决事项和攻击防御事项,进而在我国民事裁判体系—判决、裁定和决定—的整体框架中,讨论上述三类事项的决定形式。最后重点讨论了实体性先决事项的中间裁判制度,及其与我国现有基本理论和现行制度的协调问题。
树图思维导图提供《先决问题与中间裁判(下)》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先决问题与中间裁判(下)》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77bfcef1203849286ad0a720c743928e
思维导图大纲
相关思维导图模版
先决问题与中间裁判(下)思维导图模板大纲
三、建构:我国实体性先决问题的中间判决
以上讨论表明,我国程序性先决事项的中间裁判可以通过扩大裁定的适用而获得解决,本文暂不展开讨论。建构中间裁判制度的主要意义和障碍基本上集中在实体性先决事项的中间判决问题上。
(一) 空白与缺陷:我国实体性先决问题的现行判定方式
我国对于给付之诉或形成之诉中的实体性先决问题的判定,是作为终局判决的理由进行的司法确认,其性质并非“裁判”,而是作为给付之诉理由进行的法律“认定”。这种情况与法国判决书中的“决定性理由”很相似。以这种非裁判方式确认实体性先决事项存在多方面的问题,不妨以普遍而又典型的合同纠纷为例来详细分析。例如,原告在主诉中请求继续履行合同或/和追究被告违约责任,而被告却提出合同未成立或无效抗辩,从而导致双方就给付之诉的原因法律关系发生争议,亦即就创设主诉的合同是否成立、有效或可撤销性存在争议。目前的做法是,对此先决性问题迟至作出最终判决时一并确认。这种在超职权主义模式下合乎我国逻辑并且基本奏效的司法确认方式,随着整个诉讼模式以处分权主义为基本理念逐步改造,可能产生并将加剧至少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当事人主张和攻击防御方法的不确定性。合同是否成立或有效所引起的法律责任迥然不同,甚至方向相反。以原告为例,如果合同被判定成立、有效,则可在后程序中依据合同和有关法律,主张并证明有关合同义务的约定(合同解释)、双方履行合同的过程、对方违反合同的责任(违约金及实际损失赔偿)等;如果合同被判定不成立或无效,则在后程序中不能依据合同约定,而只能依据有关法律主张导致合同无效的过错及相应赔偿责任。在法庭未就合同效力问题作出明确判定之前,双方当事人都无法针对主诉请求选定有利于本方的立场和与之相应的事实主张、证明对象和法律辩论主张。
第三,原告提出逻辑一致的利己主张的机会丧失。除非预先荒谬地提出两套相互冲突的诉讼请求和理由,比如原告在提出合同有效并据此请求继续履行及承担违约责任的同时,主张合同无效并据此请求承担无效过错责任,否则一旦最终判决对于合同效力的认定与本方的主张相反,原告就丧失了基于先决问题的判定结果而提出之逻辑一致的利己主张的机会。
第四,诉讼程序的拖延和浪费。如果最终判决对于确认之诉的裁判否定了合同的效力,则围绕给付之诉中合同履行和违约赔偿进行的全部诉讼都成为浪费和无效,当然也导致整个诉讼的拖延。
进而言之,当可以就达到可裁判的程度的请求权原因作出先行裁判,以利于诉讼程序的减负和加速时,建立先决问题的先行解决制度可以避免程序浪费和诉讼拖延,这也是建立我国中间判决制度的主要目的。这一问题在合同纠纷中不是最突出的,却是各类纠纷中最为普遍的,比如在侵权损害赔偿请求、不当得利请求、消灭时效等争议中都会经常产生—如果最终判定不构成侵权责任或不当得利,或者判定请求权已超过诉讼时效,那么围绕给付范围和数额等进行的审理都没有意义。避免程序浪费和诉讼拖延,既然是建构和适用先决问题裁判制度的主要目的,当然在中间裁判的适用条件及救济途径等制度构造和司法裁量中,这一目的能否实现而不是适得其反,是考量中间裁判制度设计的合理性的重要尺度。换言之,在制度设计上,必须平衡中间判决在节省程序、减少浪费方面的正面效应与可能被滥用而导致的诉讼拖延和程序浪费的负面效应,而在程序运行上,这类中间判决应为非必要的中间判决或称裁量性中间判决,即是否作出中间判决应交给法官根据上述功能标准来裁量决定。后面将特别指出,讨论中间裁判制度应当将中间裁判与中间上诉区分开来—中间裁判并不一定能提起中间上诉。
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在对主诉作出裁判之前,必须首先对争议中的原因法律关系或原因行为进行司法确认,以固定后程序的审判对象。如果说中间裁判第一个方面的功能由于正负效应并存而使之成为非必要的中间裁判事项,那么,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却已经向实践提出了刻不容缓的现实挑战,以至于相关制度不得不作出权宜性回应。特别是在举证失权制度实施之后,这一问题更加突出。为缓解这一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证据规定》第35条中写道:“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34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从宗旨和功能上看,《证据规定》第35条规定是针对变更诉讼请求及提交相关证据的期限作出的,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我国在没有答辩失权制度的背景下实施举证失权制度所导致的诉讼标的及相应攻击防御手段无从确定的严重缺陷。然而,作为权宜之计,以司法认定和释明而非裁判的方式对实体性先决事项作出司法判定,其最致命的缺陷是其效力的不确定性和救济途径的缺失,不仅对于实践问题的解决存在着多方面的局限性,而且在制度的整体协调性和理论逻辑上导致紊乱,引发其他问题。
(二) 障碍与超越:中国特色的中间判决制度的基本构想
建立中间裁判制度要考虑的核心问题是:对于争议事项的中间确认,应当符合怎样的条件、经过怎样的程序、具备怎样的形式乃至救济途径,才能具有正当性和以此为基础的法律效力;而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司法政策对于公正的追求与成本的控制之间的平衡支点究竟在什么位置。我国关于裁判效力及诉(的合并或吸收)的理论缺乏自己独立、完整的体系,因而,试图在一个与德国或法国差异很大的裁判制度框架内,借用类似于德国或法国的裁判理论来解释和修补漏洞,是难以奏效的。因此本文以完善我国裁判制度体系为目标,吸收德国和法国中间判决乃至整个裁判制度的基本原理,在对我国裁判文书的结构和理论进行符合我国个性的改造的基础上,尝试将我国中间裁判制度建构在这个自成体系的裁判制度框架之内。在这个过程中,以下几个理论和实践的障碍必须超越。
1.确认之诉与给付之诉之间的关系
先决事项的相对独立性在国内民事诉讼法中不受承认,通说认为,确认之诉已为给付之诉所吸收,故不能单独就确认之诉作出裁判。这是建构我国中间裁判制度的主要理论障碍。
从目的和功能上看,确认之诉与给付之诉本是两个独立的诉,将二者合并审理与其他类型的诉的合并无二致:一是避免就同一事项作出相互矛盾的裁判;二是为了降低诉讼成本和提高诉讼效率。因此,当两诉的合并审理和裁判恰恰产生与上述预期功能相反的效果时,即使不考虑其他因素,也应考虑以单独裁判替代合并裁判。而且从制度原理上看,当关于原因法律关系或法律行为的争议已形成,不能为给付之诉或形成之诉所吸收的确认之诉时,仅以“认定”(而非“裁判”)方式在给付之诉的裁判理由(而非在判决主文)中给予回应,不符合裁判对象与诉讼标的相一致的原理。[1]
在理论层面上,确认之诉之所以能够被给付之诉(或形成之诉)吸收或包含,亦即原告之所以可以在提出给付之诉时不必单独提出确认之诉,是基于一个隐含前提或假定,即双方对于确认之诉没有争议。然而,在以下两种情形中,确认之诉与给付之诉同时存在争议:一是起诉之前即已显现出双方对原因法律关系存在争议的案件中,且原告同时提出确认之诉和给付之诉两个明确独立的诉讼请求,此时,除非被告对于这个隐含的前提或者说原告明确提出的确认之诉不予回应,因而可视为原告主张(确认之诉)的承认,否则就该确认之诉的争议必须给予司法裁判;二是起诉之后由于被告对原因法律关系的存在与否、合法性、适当性等等提出抗辩(异议或质疑)。这两种情形均打破了上述隐含前提或假定,昭然若揭地表明双方就此问题存在争议,因而法庭需要首先对确认之诉作出明确的判定。质言之,当实体性先决事项与请求事项均存在争议时,确认之诉与给付之诉之间就不再是吸收,而类似于诉的合并。
2.处分权对于先决事项成为中间判决裁判对象的意义
既然先决事项争议构成相对独立于主诉的确认之诉,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确认之诉是否需要单独提出诉的声明,才能成为裁判对象?换言之,如果原告起诉时未就实体性先决问题提出单独的诉讼请求,而是由于被告抗辩才产生的先决事项争议,那么法庭能否就此事项直接作出裁判?直接裁判是否有悖于处分权主义和诉讼标的限定裁判对象的理论?
笔者认为,确认之诉无须单独提起,只要在诉讼中形成争议即可成为裁判对象;但非必要的中间裁判须经当事人一方动议,由法官裁量决定。理由在于:确认之诉只具有“相对”独立性,亦即相对于本诉而言,实体性先决事项本身并非独立的诉讼标的,它的判决以先决事项的争议为起点,但并不以其本身的解决而成为本案争议的终点。无论这一“争议”由原告起诉时提交法庭,抑或由被告抗辩时提交,法庭即对该事项享有裁判权。当确认之诉的裁判成为给付之诉审理和裁判的必要前提时,法官凭借审判权的内在权力即可直接对先决事项作出裁判,无须另行或单独提起确认之诉,也无须当事人任何一方动议其就此作出裁判,因为不就此作出裁判,后面的实体审理就无法进行(此时可参考强制的预备合并理论)。但当确认之诉的裁判只是基于节约程序或/和加速审判进程等程序因素考虑时,法官应尊重当事人对于程序利益的自我考量和选择(处分),并以维护双方当事人利益及公共司法资源的平衡作为法官裁量决定是否同意作出中间裁判的考量标准。即便在非必要的中间裁判情形下,也无须另行专门提起确认之诉,只须任何一方口头动议并记人庭审笔录即可—当然也不拒绝书面申请。
在我国,先决事项争议无须单独提起即可成为相对独立的(中间)裁判对象,还有另一层理由。我国实际上通行的理论与实践是,原告、被告乃至法庭共同“动态”地形成诉讼标的的。主流理论认为,诉讼标的由诉的声明加原因事实构成。实践中,审判对象并非单独以起诉作为终结点的,原告的诉的声明加原因事实也不是审判对象的唯一依据,原因事实更是在被告提出抗辩之后,甚至双方经过几轮证明和辩论之后,才能确定。最常见的一种表征就是立案时的案由与结案时的案由不同,例如原告起诉时主张是借贷关系要求被告偿还借款,被告抗辩则主张是合伙关系故而风险共担,法院并不会因为借款关系不成立而简单地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甚至可能超越借贷关系与合伙关系之争,认定为某种投资关系等等。由于我国也没有事实问题一法律问题的分野—况且法律关系的性质问题属于法律问题,因此,即使表面看来判决主文通常是直接针对起诉请求(给付之诉)作出的支持或驳回的判定,但被作为主诉裁判之理由的先决事项并非裁判对象,直到裁判作出之前都处于不确定状态。要求在诉讼过程中就先决事项单独提起确认之诉作为中间裁判的前提,既不符合制度逻辑,也不能体现诉讼声明对于审判对象的固化或处分权对于审判权的制约,更不符合诉讼经济原理,徒增程序的繁复和诉讼成本。
3.实体性先决事项的判定在裁判结构中的角色
接下来的相关问题是,如果先决事项在最后判决中一并作出判定,其角色应当是作为裁判理由,还是裁判(即判决主文)?如果作为裁判理由,是否与中间判决将先决事项作为裁判对象逻辑一致?此时这一事项的司法判定具有怎样的法律效力?
然而,如果原告在起诉时在给付请求之外单独提出确认之诉,比如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并请求判令赔偿损失,是否应当在判决主文中单独就合同效力问题给予回应?目前我国的司法实践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比如法院可能支持了合同无效的主张,而不支持请求赔偿的主张,但判决主文只写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而将确认合同无效的司法判定写人判决理由。由于我国赋予包括裁判理由在内的整个“生效判决”以先决事实的效力,这种实践在既判力方面的严重缺陷被掩盖了[2],但仍然存在以下几个问题无法解决:
其一,根据处分权主义和诉权保障原理,司法判决(主文)应针对当事人的每一项诉的声明给予直接回应。对于当事人而言,将先决事项争议作为一项单独的诉讼请求提请司法裁判,就是将确认之诉与给付之诉作为两个相互独立的诉提请合并审理,此时给付之诉不能吸收确认之诉,因为对于两个诉的司法回应对于当事人可能具有不同的法律意义,而将确认之诉的司法判定作为给付之诉的裁判理由给予回应不能实现当事人的诉讼目的(理由如“其二”所述)。
其二,生效裁判的法律效力,除事实效力和证明效力之外,最重要的是权利效力,亦即该裁判直接对当事人的法律状况产生具有法律确定力的影响。权利效力与证明效力的区别在于:前者附属于判决本身,后者附属于判决理由部分;前者涉及判决所确认的权利的状态,后者涉及推导出判决的事实。比如,宣告不动产买卖无效或股权转让无效的判决,可以直接成为原权利人籍此实现权利的根据;但如果将这些内容作为判决理由,则无法直接实现这一目的。
其三,从技术上说,判决主文是对全部诉讼请求的回应,将对于确认之诉的请求放在判决理由中回应,而将给付之诉放在判决主文中给予回应,可能出现裁判理由与裁判主文的法律效果自相矛盾的现象,仍以合同无效和请求赔偿两项请求为例,如果将合同无效的确认作为判决理由而予以支持,而将赔偿请求作为判决主文内容予以驳回,则会出现两个问题:一是认定合同无效实际上并非驳回赔偿请求的理由,因为驳回赔偿请求与认定合同无效之间并无因果关系;第二,按照通常的文书制作规范,判决主文可能会简单地写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那么,原告的诉讼请求是两项,这样等于判决主文将合同无效和赔偿损失两项请求一并驳回了,而判决理由中却实际上是支持了合并无效的主张。这种自相矛盾,对于确定先决事项的司法判定的法律效力,无论是事实效力、证明效力或权利效力,都是非常不利的。
其四,不在判决主文中就先决事项给予回应,意味着双方当事人都丧失了就此事项单独提起上诉(或再审)的救济机会。理由如上。
由此可见,确认之诉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或应当被给付之诉吸收,就先决事项的司法判定的角色也因具体情形而不同:(1)如果当事人未将确认之诉作为独立的诉讼请求提出,先决事项争议系因被告抗辩而产生,则就此事项作出的先行判决为中间判决,在最后判决中就此事项的司法判定应作为裁判理由,而不是裁判对象。(2)如果当事人将确认之诉作为独立的诉讼请求与给付之诉同案提出,则应就确认之诉单独作出终局判决,此时该争议事项就不单是给付之诉的“先决事项”,而是独立的诉讼标的。如果在诉讼过程中就此请求先行判决,则该判决为部分判决(在性质上属于终局判决),具有实质既判力,并包括本案给付判决在内的其他后判决有拘束力;如果在本案终结时与给付之诉一并作出最后判决,则应在判决主文中给予单项裁判,而不能作为裁判理由。
在讨论中间判决的效力与救济途径时,我们必须再次强调,是否应当就先决事项作出中间判决,与是否允许就中间判决提起中间上诉,二者所追求的目标和价值考量标准并不完全相同。中间裁判的意义在于使发生争议的先决问题获得当事人辩论、公开审理和明确判定的机会,因为只有就这些先决间题作出中间裁判,这些事项才能成为既判事项,对当事人和法官有拘束力,并且符合逻辑地成为上诉审查对象。以中间裁判形式替代目前以决定或“司法认定+法官释明”的方式,目的是保障先决事项司法判定的规范性、确定性和拘束力(形式既判力),其效果和意义在于增加对当事人的辩论权和程序保障权,但更在于通过增加程序的约束力而加速和节约整个诉讼程序。即使基于诉讼效率和防止滥用的考虑而应当减少中间上诉,中间裁判也具有形式既判力;但中间裁判事项则可以通过与终局裁判一并上诉,而成为上诉程序中的审判对象。
中间判决的上诉作为一种救济途径,其在增加程序保障方面的意义自不必论,但在先决事项司法判定的确定性和程序的节约方面,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先决事项判决通过中间上诉而尽早获得终审法院的确定,可能避免针对诉讼标的进行的后程序的浪费—在先决事项受到否定性司法判定时尤其如此,比如作为违约赔偿请求之前提的合同被判定无效,作为侵权赔偿请求之基础的侵权责任被判定不成立,作为主张请求权之基础的诉讼时效被判定已经消灭,等等。另一方面,中间上诉将导致一审诉讼程序的中止或停顿,因而可能导致诉讼延迟和成本增加。正如我们在考虑任何民事诉讼制度时始终应当铭记的,上诉权同样是由双方当事人共享的权利,一方的程序权利(特别是救济权)增加可能意味着对方程序利益的损害。如果对中间裁判事项不加区别,笼统地讨论中间上诉权,其适用范围要么失之过窄,造成不必要的后程序浪费;要么失之过宽,为滥用抗辩权和中间上诉权拖延诉讼提供契机。
因此,尽管中间判决的适用范围较宽,但中间上诉必须限定在非常狭小范围之内。总体原则是,当中间判决可能导致后程序终结(如诉讼时效消灭则全案就此终结,侵权责任不成立则数额程序无须继续审理),或者导致以此为基础的实体权利丧失裁判机会,或者以此为基础的诉讼标的可能变更时,则可提起中间上诉。其他中间判决不允许上诉,但对后程序有形式既判力。就确认之诉单独作为一项诉讼请求与给付请求同案提起诉讼的,其裁判在性质上属于终局判决,适用终局判决的上诉规则。先行作出部分判决的,可单独上诉;最后一并作出全部判决的,可以就整体案件提起上诉(如果对全部判决不满),也可以单独就此事项提起上诉(如果仅对此事项不满)。这一原则与我国允许上诉的裁定仅适用于诉的合法性裁判可能导致诉讼在本院终结的情形(无论是驳回起诉的终局裁定,还是驳回管辖权异议的中间裁定)保持了合理的一致性。
注释:
[1]关于诉讼标的的形成,我国主流理论认为,诉讼标的由原告诉的声明和原因事实构成,并且原告的诉的声明与被告对于诉的抗辩相结合,动态地形成诉讼标的和裁判对象。司法实践目前正是如此奉行的,比如立案登记的案由(诉的声明)与判决书上的案由(裁判对象)不同是司空见惯且未受合理质疑的现象。
[2]有学者提出,德国适用中间判决是因为其裁判理由不具有既判力,而我国司法解释已经规定,“……具有先决效力”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因此不濡要中间判决。(北京大学法学院·傅郁林)
出处:《中国法学》2008年第6期
引用法条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三十五条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三十四条
查看更多
9.战斗的基督教思维导图
 U582679646
U582679646树图思维导图提供《9.战斗的基督教》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9.战斗的基督教》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33d168acd0cd9f767f809c7a5df86e3a

第六章 群体传播与组织传播_副本思维导图
 U882673919
U882673919树图思维导图提供《第六章 群体传播与组织传播_副本》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第六章 群体传播与组织传播_副本》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1672f555831e7d9a3bb2cf2fb792cb49

相似思维导图模版
首页
我的文件
我的团队
个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