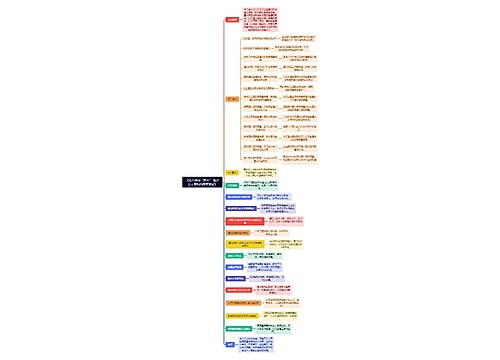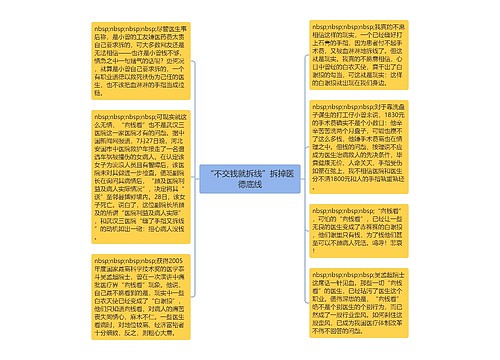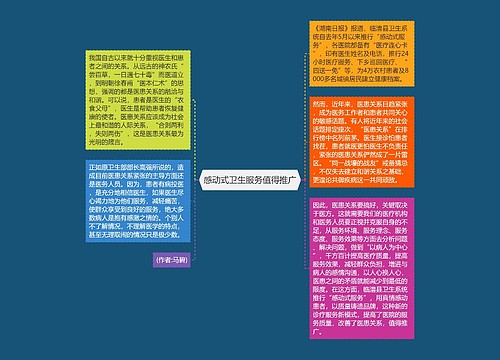这一病案管理制度,不仅开中国现代病案管理制度之先河,在当时的世界上也属于领先地位。据协和医院院史载:上世纪30年代,王显星曾向医院领导提出赴美国进修考察的报告,当时的院长,美国医学家胡恒德(S.Houghton)说:“不是你到美国学习,而是美国要到协和学习。”
这些详尽的病历档案,每一册都记录了医务人员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经过,为医学研究提供了资料和数据,在医生们遇到疑难病例需要帮助时,只要将病例交给病案室,工作人员就会从上百万份病案中提出相关的病例。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的夫人患病,很多专家都无法确诊,最后请到了协和医院的著名内科医师张孝骞。张孝骞在没给病人做任何辅助检查的情况下,仅通过详细询问其病史与查阅相关病历,就准确地诊断出马夫人的病症。此事轰动了当时的医学界。
近年来,国际医学界越来越普遍地认为,人一生的健康状况,与最初在子宫内的发育状况密切相关,它甚至关系到一个人中老年可能会得的各种疾病。
基于这种认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发起一项名为“宫内发育与老年病关系”的计划——在全世界范围内,对1921年至1941年出生的人,进行出生期和老年期身体状况的对比统计研究。
有关专家到中国考察后发现,只有协和医院保存有从1921年到1941年在这里出生的婴儿病案。从2003年起,这项研究的中国部分,便开始在协和医院进行。
协和医院病案室主任刘爱民说,在协和保存完好的240多万份病案中,已经找到了符合条件的2000多位老人。他们中,有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还有吴文藻和谢冰心的女儿吴青。
翻开发黄的案卷,那上面有婴儿出生时留下的花瓣似的小脚印,还有他们的接生医师林巧稚,用娟秀的英文书写的出生证明和签名。
医学科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让医学生们尽早与疾病短兵相接,把书本还原为应用,使理论转化为认识和经验,这是医学生们登堂入室,进入医学殿堂的唯一正确路径。
重视病案是协和医院的传统,它是医学院学生临床入门的基本功,也是医生考评的依据。
协和医院的病案书写,很大一部分是由刚从协和医科大学毕业的见习医师完成。见习医师刚进病房,要做的是采写病史,自己动手为病人做常规化验检查,在各种检查结果的基础上做出初步的判断,写出完整的“大病案”,然后交给导师。
“病历写得好,就一定会成为好医师,病历写得不好的,很少能成为出色的医师。”每一个在协和医科大学就读的学生们,都从各自的导师那里听过这句话。
这些见习医师们,每人都有一位指定的导师。在他们采写完病历之后,导师会和学生一道对病人进行复查,核对化验的结果和各种体征。
由于缺乏医疗实践经验,临床思维能力也还在逐渐形成过程中,见习医师常常在资料搜集与病情分析方面存在不足,甚至对病案书写的基本要求、格式都有着不理解之处。这就需要导师们对其严格要求。
这些学生更认真地观察与记录,结果,林巧稚依旧不满意。
于是,这些学生找来“Good”的作业,对照之下发现,那位同学的病案记录上,只比他们多写了一句话:“产妇的额头上冒出了豆粒大的汗珠。”
这样丝毫不留情面的严格和认真,现北京协和医院血液内科的张安教授也曾经历过。张安是我国著名内科专家钟惠澜的学生。当年,他的第一份病历被钟惠澜用红笔改得面目全非,“只剩下名字的三个字是自己的”。
导师还会就病人所患疾病可能的种种病因和问题,向学生提问。因此,见习医师们在向导师提交病历之前,都要跑图书馆和病案室,查阅相关病例的资料和各种书籍文献,对自己分管病人的疾病做最充分的了解,避免在导师们严苛的追问下理屈词穷。
一个协和医大的学生,在她毕业多年以后曾深情地写下这样的文字:“……我依旧记得病案室里的书桌和高背靠椅,协和许多教授(在那)有着自己的固定座位,他们的星期天常常在那儿度过。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房间,那些熟悉的身影一动不动地镶在窗框里,像是一幅幅逆光的剪影……”
老协和成为两类人最多的医院——达官贵人和走投无路的穷人
现代西方医学理念认为,疾病大多与患者心理的、情感的和社会的因素有关,任何一家医院,如果不能提供社会服务,只是设备精良、具有一定的医疗水准,还不能被称为第一流的医院。
在这样一种理念下,协和医院从建院初始,便设立了“社会服务部”。这是一个特殊的医疗机构,它的职责是为确有困难的患者提供经济、心理、愈后的服务、同时也可以为医生提供治疗前的社会调查和治疗后的追踪随访结果。
老协和的医生们,时常会遇到因生活贫困而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的病人,这时,医生就会去找“社会服务部”的工作人员,把病人介绍给他们。
随后,工作人员对患者进行社会调查与家庭访问,写出对患者生活状况的书面报告。社会服务部再根据报告,商量决定对病人的资助方式:减免或分期偿付医疗费用、或给予衣物、路费与营养资助,甚至还提供殡葬救济。
这些衣领上绣着“SOS”(“社会服务”的英文缩写)的白大褂,多是刚从全国各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的学生。他们所做的调查报告,都附在病人的病历后面,是医生的重要参考材料,而他们对出院病人进行的随访调查,既让病人及时得到指导,防止疾病复发,又为医生的科研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这些调查报告作为病案的一部分,和病案装订在一起。几十年过去,病案室里还依旧完整地保留着这些原始记录。在这些发黄的纸上,依旧可以清晰地辨认出这样的字迹:“……大夫优待,按八五折计算……”“……大夫免收费用……”
根据董炳琨的研究,上世纪30年代,是协和医院的社会服务部职能最完善的时代。正是由于有了社会服务部,老协和才成为两类人最多的医院——一类是达官贵人,一类是走投无路的穷人,“他们的工作,不仅仅有作为病案保存的价值。对穷苦人的帮助,也体现了医生这个职业的社会关怀和理性。”董炳琨说。
协和医院的社会服务部撤销于1952年。同年,中国所有的大学,全部取消了社会学系,原因是当时有人认为: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社会问题。
一位无名医生的铭文: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从1939年起,董炳琨就在八路军120师医疗队工作,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这个行医60多年的老医生,对北京协和医院院史有系统、深入的研究,曾主编、撰写过数部医院管理专著。
在董炳琨对医患关系的多年研究中,他发现,许多医疗纠纷的发生,不是技术原因,而是源于“医方的服务态度、语言沟通和责任心方面”的问题。
而医院与医生漠视病案,正是当下医患关系紧张的一个缩影。“别说病案了,现在的年轻医生,连处方上的字都敢写得七扭八歪。”董炳琨不住地摇头。
多年以前,董炳琨曾在老协和图书馆的一本英文原版书上读到过:英国的撒拉纳克湖畔,镌刻着一位无名医生的铭文:
在董炳琨看来,这来自遥远地方的湖畔铭文,正如同老协和所保存的那240万份病案一样,深刻地阐释出医生这个职业的人道使命,折射出人性的温暖。
“希望协和的这次病案展览,能够让年轻医生,和那些即将进入医学这个神圣殿堂的学生们明白,如今的我们,究竟丢失了什么。”董炳琨叹息道。

 禹
禹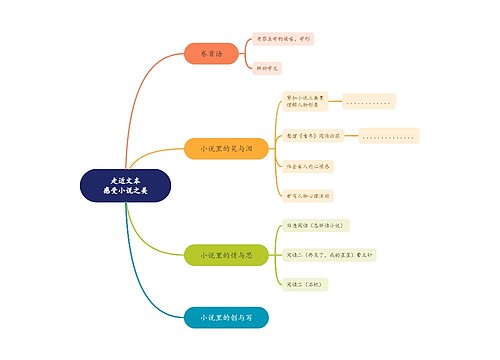
 U275361216
U27536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