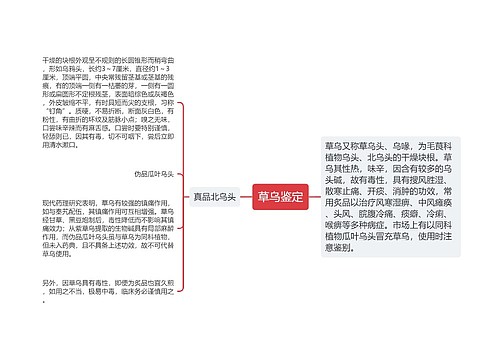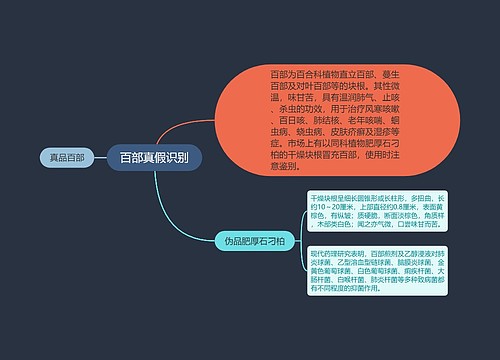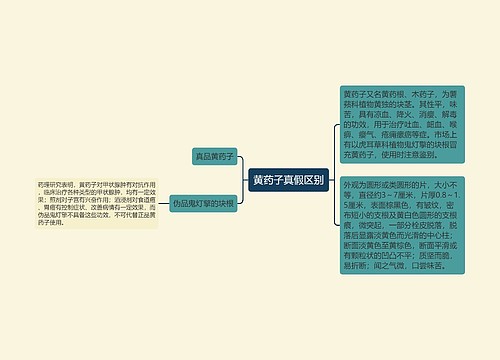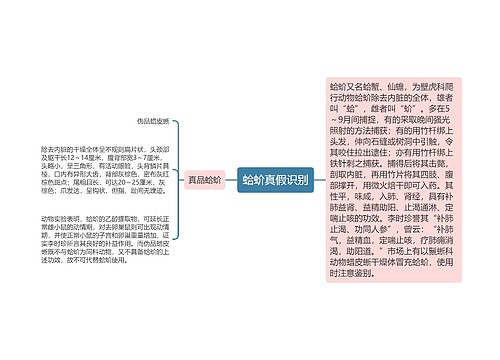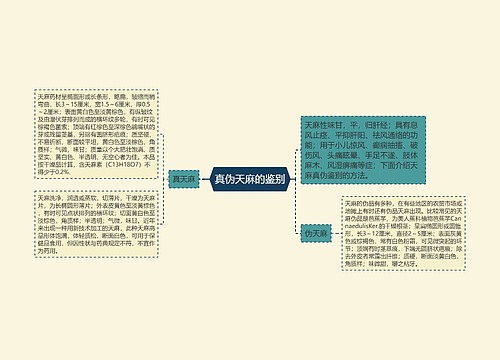办公桌上,一摞用档案袋装着的患者病历、一堆有些发黄的医学书籍,提示着此屋的主人与医学有着某种联系。见有人来,一个年轻、帅气的小伙子忙从电脑前站起,他就是记者要采访的对象——马军,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法官。
马军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审结了七十多起医疗纠纷案件。说起自己审过的医疗纠纷案件,马军丝毫没有欣喜之色,反而有些伤感。他给记者讲了一个让他许久不能忘记的案子:
一位中年母亲,由于孩子在医院去世与医院闹了整整8年,能找的部门都找过了,但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颁布后,她起诉到海淀法院。而经过一年多的医疗事故鉴定后,得出的结论却是不属于医疗事故。后来,马军把这个案子给调解了,得到医院一定经济补偿的母亲当时就要给他跪下。
说到这儿,马军的眼睛已经有些湿润:“说实话,在审理这类案件时我会悲伤和难过。那种感觉是不可名状的,因为法官也可能成为患者的一员。”
马军告诉记者:“从2001年到现在,北京市各级人民法院受理医疗纠纷案件以每年30%的速度递增,海淀区法院有一年的增幅甚至达到了100%。”
医疗纠纷案件存在定性困难、诉讼时间长、医患双方矛盾激化等诸多问题,审判人员在处理这类案件中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是什么呢?记者把问题提给了马军。
据记者了解,3年前国务院颁布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对医疗事故鉴定在程序上做了重大修改,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来《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中卫生部门“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的游戏规则。
“条例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实践中,也显现出一些天生的不足。”马军说:“根据条例的规定,医疗事故鉴定由医学会组织。”他拿起一本书,一下子翻到要找的那页指给记者看:“再看看医学会的章程,一个重要的规定是‘为会员和医学科技工作者服务’。”马军说,患者经常拿这条作为不服医疗事故鉴定的依据。
上海市律师协会医药卫生法律研究组组长唐建立律师,多年从事医疗纠纷法律服务,他把医疗事故鉴定的改革比作“终于打开了暗箱,但是一些问题依然存在”,“首先就是鉴定主体问题,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只不过是从‘老子给儿子鉴定’变成了‘兄弟给兄弟鉴定’”。
“其次,医疗事故鉴定程序也有问题。”唐建立告诉记者,问题表现在4个方面。其一,当事人提交材料后,无法知道对方提交了什么材料。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患者,更无法确定医方是否提交了充分、真实的材料,而且不知道医学会是否将全部材料交与鉴定人员。其二,实际操作中,医学会工作人员并不对缺乏医学知识的患者进行指导,抽签中出现的均是代码,在短短的几分钟内,患者在不知具体专家姓名、特长等情况下仓促抽签,易使这一过程流于形式。其三,鉴定是在一种封闭状态下进行的,这有悖于鉴定所要求的公开、客观原则。其四,鉴定后,对专家的原始意见及合议书,当事人无从查询,处于权利的真空状态。
“第三,是对医学会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唐建立说,我国医疗事故鉴定人员没有淘汰机制,并且由于鉴定人员都是临床执业医师,这种无监督的权力容易产生不合理的鉴定结论。由于法官不是医学专家,对医疗纠纷案多采信医疗事故鉴定结论,而对鉴定结论的审查却缺乏相关的措施,于是在实践中出现了许多“唯鉴定论”的司法判决,这无疑从另一方面削弱了对医学会的监督力度。
此外,马军告诉记者,条例没有规定应该由鉴定组里哪位专家出庭质证,造成了没有鉴定专家愿意出庭质证的现状,从而违反了证据规则。条例还规定专家鉴定组对因果关系、事故等级、责任程度作出鉴定,这些本来是审判过程中认定的事情,却都由鉴定机构作出,等于是由医疗事故鉴定替代了审判权。“在审理医疗纠纷案件时,法官能做的就只是加减乘除,根据条例计算一下赔偿金额了。”话至此时,马军略显激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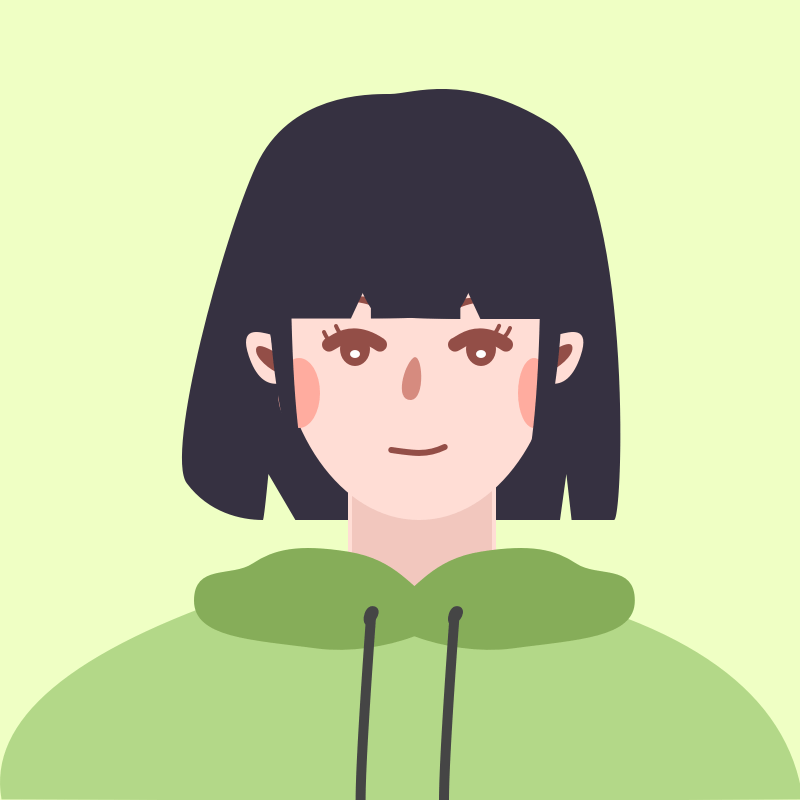 U779509158
U779509158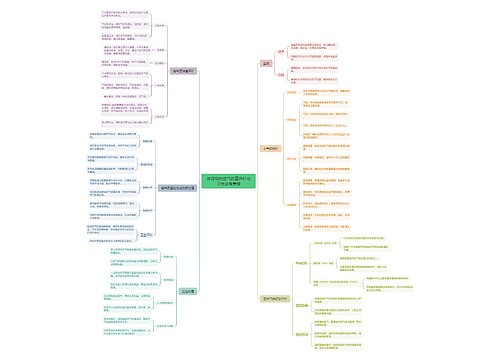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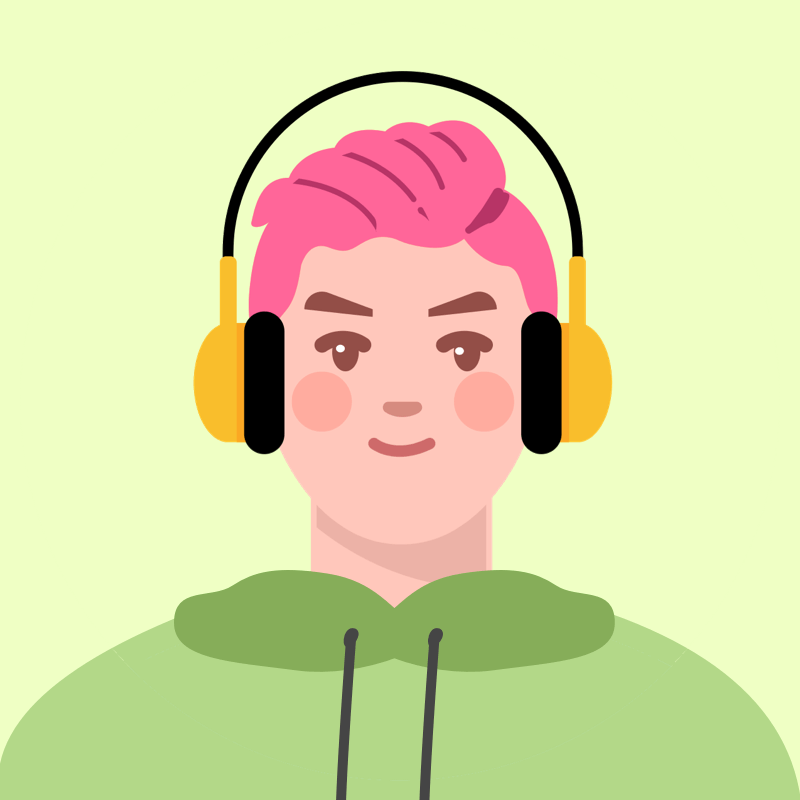 U480806892
U480806892